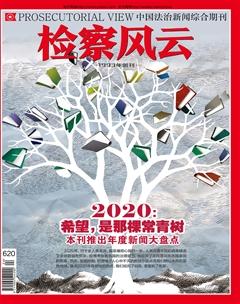姚建龍:新未保法促未檢向綜合檢察拓展
本期客座總編輯

姚建龍: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曾任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上海政法學院黨委常委、副校長,團中央權益部副部長等;榮膺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先進工作者、第十八屆“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第五屆“優秀中青年法學家”、上海市“曙光學者”等稱號。
人民有所呼,修法有所應
《檢察風云》:首先,作為未成年人法領域的專家,您如何評價新出臺的未保法?
姚建龍:改革開放40年來,很少會有一部法律的修訂,會像本次《未成年人保護法》這樣受到如此熱烈的關注。也很少有一部法律的修訂,尚在過程之中就受到高度評價,剛一公布便贊美之聲鵲起。
未成年人保護關系千家萬戶,本次修法拓展公眾參與立法方式,廣泛聽取各界意見和建議,包括未成年人意見。僅修訂草案一審稿在公開征求意見期間就收到4.9萬條修改意見,其中,近半數由未成年人提出。全國人大法工委對于這些意見均進行了認真研究和吸收,對近些年來輿論關注的未成年人保護熱點問題,諸如學生欺凌、性侵、兒童色情、網絡沉迷、課業負擔、兒童安全座椅、高空墜落、意外溺水、未成年人門票減免、兒童友好衛生設施等等,新未保法都增設或者完善了相關條款。可謂“人民有所呼,修法有所應”,是一次人民立法的生動實踐。
修訂后的新未保法構建了新時代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新體制。這一新體制的設計“用心良苦”,既吸收了國際社會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經驗,也充分發揮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同時還兼顧到了我國仍然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國情,充分體現了“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的要求。
《檢察風云》:新未保法的出臺對惡性事件的遏制建立了哪些初步反應機制?
姚建龍:近些年來,南京餓死女童案、畢節垃圾桶悶死留守兒童案等觸犯人倫底線的涉未成年人惡性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只有建立包括監測預防、發現報告、應急處置、評估轉介、幫扶干預、督查追責為一體的未成年人保護綜合反應機制,才能有效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盡管是初步的,但新未保法仍在未成年人保護綜合反應機制的建設上取得了以下重大進步:一是開通全國統一的未成年人保護熱線,及時受理、轉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投訴、舉報(第九十七條)。二是建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單位工作人員在招聘時及入職后定期查詢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記錄以及相應從業禁止制度(第六十二條、第九十八條等)。三是建立發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臨其他危險情形的強制報告制度(第十一條等)。四是要求在公共場所設置走失未成年人安全警報系統(第五十五條第二款)。五是預留檢察機關對負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律責任部門的監督空間。新未保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通過行使檢察權,對涉及未成年人的訴訟活動等依法進行監督。”該條一個“等”字,含義深遠。
新未保法將檢察機關明確為監督機關
《檢察風云》:新未保法賦予了檢察機關怎樣的角色定位??
姚建龍:修訂后的新未保法所確立的未保工作新體制,上下一體、協調有序、責任明確,特別是將檢察機關明確為監督機關,非常具有針對性,有助于保障未保工作新體制的流暢運作,破解“責任稀釋”困境,形成未成年人保護合力。
《檢察風云》:作為曾經在檢察戰線上的檢務專家,您認為新未保法賦予了未成年人檢察怎樣的獨特性?
姚建龍: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二十條第八款規定人民檢察院所行使的職權包括“法律規定的其他職權”。修訂后的新未保法立足檢察機關基本職能,明確人民檢察院在未保工作體制中的監督機關定位,是根據新時代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發展的需要對檢察機關法定職能的細化與深化。目前,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到基層人民檢察院,檢察系統已經建立起相對完善的未檢專門機構體系,未檢職能也從傳統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向綜合檢察發展,有能力履行未保工作新體制中監督機關的職責。修訂后的新未保法的頒布,也意味著未成年人檢察已經在法律上具備了不同于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公益訴訟檢察的獨特性。在我看來,可以也應當視為第五大檢察。
五大體系,打通未成年人保護任督二脈
《檢察風云》:總體而言,新未保法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亮點?
姚建龍:我認為,新未保法有以下幾個亮點。第一,建立協調機制。修訂后的新未保法在細化主要相關國家機關未成年人保護具體職能的基礎上,在總則中明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協調機制,統籌、協調、督促和指導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工作協調機制的建立,標志著未成年人保護正式成為政府的法定職責。
第二,明確牽頭部門。修訂后的新未保法第九條規定,“協調機制具體工作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承擔,省級人民政府也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確定由其他有關部門承擔”。盡管這一條款考慮我國地方的差異留下了省級人民政府可以確立牽頭部門的彈性空間,但確立了“民政牽頭為原則,其他部門牽頭為例外”的法律要求,解決了自1991年以來未保法執法責任主體不明的難題。
第三,賦權協助單位。修訂后的新未保法第十條規定:“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工會、殘疾人聯合會、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青年聯合會、學生聯合會、少年先鋒隊以及其他人民團體、有關社會組織,應當協助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相對原條文,這一規定增加了“應當”的表述,明確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是人民團體和有關社會組織協助政府、司法機關的法定職責,同時也進一步明晰了人民團體和有關社會組織在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新體制中的法定角色為“協助”而非“替代”。
第四,暢通專門力量。未保工作力量的專門化是避免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體制“華而不實”的關鍵。修訂后的新未保法明確要求政府自上而下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專門機構與專門力量:首先,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承擔未成年人保護協調機制具體工作的職能部門應當明確相關內設機構或者專門人員,負責承擔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其次,鄉鎮人民政府和街道辦事處應當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站或者指定專門人員,及時辦理未成年人相關事務。再次,支持、指導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立專人專崗,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修訂后的新未保法還要求國家司法機關“應當確定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門人員,負責辦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辦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員應當經過專門培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
第五,確立監督機關。修訂后的新未保法賦予了檢察機關在未保工作體制中監督機關的地位,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1)對涉及未成年人事項的檢察監督不限于“訴訟活動”。(2)明確將未成年人權益納入公益訴訟范圍。(3)明確了檢察建議這一重要監督途徑,并對被建議單位回復時間與方式提出要求,強化了檢察建議的剛性。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有關單位未盡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護等保護職責的,應當向該單位提出建議。被建議單位應當在一個月內作出書面回復”。盡管該條也同時賦予了公安機關、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建議權,但是由于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以及檢察建議可以公益訴訟為后盾,這種形式的檢察監督更具專門性和獨特性。
采寫:張亮?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