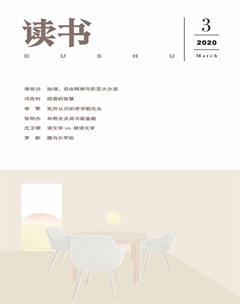博爾赫斯的雨村
楊俊杰
《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篇關于“謎”的小說,它的主要情節是出謎。男主人公身在英國,間諜身份已暴露。但他還有緊急情報要傳遞給德國柏林—轟炸地點是法國城市阿爾伯特(Albert)!他想到了“出謎”——博爾赫斯寫的西班牙語原文正是propusieron elenigma。在追捕者出現前那一刻,他將一位姓“阿爾伯特”的男子(全名Stephen Albert)謀害,然后如愿以償地被捕。他成功地制造出一個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使他的名字與阿爾伯特的名字一起傳播出去。柏林的上級在讀到新聞以后心領神會,識謎、“解謎”(descifradoese enigma)。追捕者遭戲弄,成為“同謀”而不自知。出謎成功!成功的關鍵處在于,男主人公善于(且敢于)“經營”、操縱時間。他計算好了時間,一路上留下許多蹤跡。所以追捕者知道怎樣追,卻總不能追到。于是乎,在整個出謎的情節里,時間儼然是一種可控制(也確實被控制)、可利用(也確實被利用)的東西。
來到阿爾伯特家以后,主人公要做的事情是等待追捕者出現。在躊躇滿志靜候出謎成功的那段時間里,聰明的出謎者卻見識到了(另)一個謎。竟是他曾祖父出的謎,然而他從不知道這個謎的存在—就像追捕他的人不曾意識到他在出謎一樣。難堪的是,聰明如他,竟不能解謎。心領神會地識謎、解謎的,卻是這位阿爾伯特。怎樣的一種吊詭!這大概就是謎中之謎,解謎者告知他謎底是時間—在他曾祖父看來,時間永遠是無限地分岔的,在每一個時間點都朝向無窮多的將來。這無疑是讓人感到敬畏的時間,不啻是時間的迷宮。這般神秘莫測,如何奢談控制!男主人公化身為出謎者,編織一個謎,操縱一段時間,籌劃著成為控制者。但在走向成功的中途,意外出現他不能夠控制的東西。在另一位出謎者面前,同時也在另一位解謎者面前,他感到無能為力。誠然,解謎者阿爾伯特也是如此—解出一個謎,而沒有識出另一個謎。
這樣說起來,《小徑分岔的花園》的“謎”的性質還在于,“情節中的情節”也是出謎。男主人公通過行動出謎,曾祖父寫小說出謎,而且是“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大概可以稱其為“小說中的小說”。主人公棲身于具體時間點,卻能走上各種可能的岔路,然后岔路又生岔路……不難想到,小說將給人以一種異常雜亂的感覺,讀者仿佛走進一座奇異的迷宮。博爾赫斯這里提到《紅樓夢》可不是一時興起,對他來說《紅樓夢》就是一部迷宮般的小說。他把自己的真切感受,寫進《 小徑分岔的花園》里。《小徑分岔的花園》(El Jardi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 ),最初發表在博爾赫斯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同名小說集《小徑分岔的花園》里,作家當時已經對《紅樓夢》形成濃厚興趣。他先是在一九三七年撰文夸贊《紅樓夢》是一部比西方“近三千年的文學”好得多的文學作品,然后還親自動筆把《紅樓夢》兩個選段翻譯成西班牙語(出版于一九四0年)。
自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間,作家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家庭》(ElHogar)雜志撰寫一系列小文章,評介國外文學。后來結集出版,便是Textos Cautivos. Ensayos y Rese?as en El Hogar 1936-1939(Barcelona:Tusquets 1986),即博爾赫斯全集譯本當中的《文稿拾零》(《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下冊,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博爾赫斯這般盛贊《紅樓夢》,當然不是無緣無故。借用艾布拉姆斯(M.H. Abrams)的術語來說,西方文學有著悠久的“鏡”的傳統,在現實的“再現”“摹仿”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就像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后來所梳理的那樣,它始自《荷馬史詩》,至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形成一個高峰。這一點也是博爾赫斯很清楚的,然而他更向往那種帶有強烈幻想風格的文學模式。《紅樓夢》于他而言就是這樣的范例,他欣喜地看到夢幻與現實在書里反復交織,很多時候簡直難以分辨—他稱《紅樓夢》是“幻想文學”,甚至中國“所有的文學”都是“幻想文學”。
《紅樓夢》令博爾赫斯深覺有趣味的內容,是關于賈瑞“正照風月鑒”的描寫,“絕不遜于埃德加·愛倫·坡或弗蘭茨·卡夫卡”。賈瑞因風月寶鑒而送命,事在《紅樓夢》第十二回。博爾赫斯則說是第十章,但這不是他弄錯了章回—他閱讀的不是中文原本,而是翻譯家庫恩(Franz Kuhn)的德譯本。庫恩的德譯本是節譯,最初出版于一九三二年。在德譯本里,它的確屬于第十章。緊接著博爾赫斯又把這一內容翻譯成西班牙語,題以《風月鑒》(elespejo de Viento-y-Luna ),收錄于他和友人們編譯的《幻想文學作品選》(Jorge Luis Borges et al.: Antologia de la Literatura Fantastica , Buenos Aires:Sudaemericana,1940)。博爾赫斯還翻譯了《紅樓夢》的另一選段—《寶玉的無限睡眠》(sue?o infinito de Pao Yu),內容是賈寶玉夢見甄寶玉,同樣也在那本作品選里。《紅樓夢》夢幻描寫頗多,這場夢幻卻顯得有些特別,意味難以捉摸。
選段《風月鑒》還配有一小段按語, 對作者曹雪芹略作介紹。最末一句提及翻譯的底本—Hemos compulsado las versionesde Chi-Chen Wang y del doctor Franz Kuhn,翻譯過來就是“我參考的是王際真的版本、庫恩的版本”。王際真的英譯本最初出版于一九二九年,同樣也是節譯。庫恩在德譯本的后記里,對王際真的英譯提出了激烈批評。王際真英譯本的“序”系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所作,已翻譯成中文。韋利很看重《紅樓夢》的想象,他認為作者的想象力“達到了最偉大的高度”。對他而言,賈寶玉夢見甄寶玉便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例子。王際真的節譯本里并沒有它,韋利便把該內容完整地翻譯出來,置于序的末尾以饗讀者。有理由推斷認為,博爾赫斯翻譯這一選段,應該是受到韋利的啟發。
博爾赫斯與友人們合編的那本作品選很受歡迎,至一九七六年已是第四版。作品選的英譯本出版于一九八八年,又擴大了影響范圍。不過,就《紅樓夢》選段而言,英譯本在忠實方面做得不太好。按語最后那句關于翻譯底本的話,竟不見于英譯本。若單看英譯本,對于博爾赫斯參考哪些底本,將不甚了然。更值得一提的是,英譯本的兩個《紅樓夢》選段,并非博爾赫斯的西班牙語翻譯的英語翻譯。作品選的英譯本是直接從《紅樓夢》的英譯本那里抄來相應段落,代替博爾赫斯的翻譯。或許是由于匆忙,竟把翻譯者的名字說錯。阿瑟·韋利沒有翻譯過《紅樓夢》,翻譯者應該是麥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McHugh)。可以想到的是,作品選的英譯本既然自行選取《紅樓夢》英譯本里的文字,也就不必保留博爾赫斯按語里最后那句話。作品選的英譯本更愿意把真正的《紅樓夢》選段呈現給讀者,而非博爾赫斯翻譯的《紅樓夢》選段—畢竟,博爾赫斯的翻譯是一種“豪杰譯”。
博爾赫斯做出許多刪改增,而且幅度相當大。以篇幅而論,第一個選段《風月鑒》在庫恩的德譯本里大概有兩頁多,博爾赫斯不過是短短三段話而已。第二個選段《寶玉的無限睡眠》,在韋利序言里是兩大段,將近兩頁;博爾赫斯雖也是兩段,內容卻少了許多。不妨來看《風月鑒》第一段話—它以省略號開始,然后是En una?o las dolencias de Kia Yui se agravaron. La imagen de la inaccesiblese?ora Fénix gastaba sus dias; las pesadillas y el insomnio, sus noches……翻譯過來就是“一年之內賈瑞的病加重了。無法得到的鳳女士的模樣折磨著他的白天,夢魘和睡眠(折磨著)他的黑夜”。原文是“黑夜作燒,白日常倦……諸如此癥,不上一年都添全了……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加沉重……”這些省略號表明許多內容已被略去。其中當然有庫恩德譯本的影響,庫恩的翻譯已然是一種豪杰譯,然而博爾赫斯又略去一些,以至于下一段緊接著就講到道人來化齋。
在庫恩的德譯本里,賈瑞是Kia Jui,王熙鳳是Frau Ph?nix。此外,寶玉是Pao Yü,賈雨村是(Kia)Yü Tsun。在王際真的英譯本里,賈瑞是Chia Jui,王熙鳳是Phoenix,寶玉是Pao-Yu,賈雨村是(Chia)Yu-Tsun。粗略地看,名字若是雙字,庫恩與王際真處理起來存在著微妙差別。王際真更愿意在雙字之間加上短橫線,以表示是同屬名字而非姓氏與名字。博爾赫斯翻譯的寶玉是Pao Yu,如此看來更接近于庫恩的翻譯方式—Yü 的德語發音與Yu 的英語發音相同,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說他襲用了庫恩的翻譯。賈瑞的名字Jui 改成Yui,推想起來大概是博爾赫斯知道Jui 的德語發音就是Yui。順帶要說到的是,博爾赫斯翻譯的兩個選段不涉及賈雨村,所以也就沒有出現他的名字。然而如果愿意推想,博爾赫斯翻譯的“雨村”必定是沒有短橫線連接的Yu Tsun(而非Yu-Tsun)。《小徑分岔的花園》男主人公的名字—前面還沒有來得及說—恰好就是Yu Tsun博士!
《紅樓夢》開篇第一段話就提到了賈雨村,誠然還有甄士隱。可惜一九二九年版王際真英譯本沒有把這段話翻譯好,刪掉了賈雨村的名字。一九三二年版庫恩德譯本直接從“姑蘇城”開始,開篇許多話都被刪去。賈雨村的名字的秘密,“假語村言”抑或“假語存焉”與賈雨村之間的聯系,無法由它們而得見。然而,賈雨村的重要性還是顯而易見的。他在第一回登場,然后由他引出榮國府,又由他審案引出薛蟠。王際真英譯本列有一個簡要的人物表,甄士隱排在第一位,賈雨村排在第二位。博爾赫斯如此激賞《紅樓夢》,必定知道這位人物。Yu Tsun 博士的名字與雨村相同,恐怕并非偶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庫恩的德譯本里,賈雨村之為進士,已然就是“博士”!冷子興與賈雨村交談時,曾乖巧地批評他說:“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所謂進士出身,在庫恩那里便是HerrDoktor aller Grade(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 übertr. Franz Kuhn, Leipzig:Insel 1932)。
于是,的確應該像王柏華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宜將男主人公的名字直接翻譯成雨村或雨村博士,而無須讀成“余準”(王柏華:《博爾赫斯書寫的中國故事》,載《文藝爭鳴》二00九年第四期)。王際真的英譯本除了有韋利撰寫的序,也還有王際真本人寫的“導讀”。王際真提到,(賈)雨村的名字意思是“雨天、村莊”(Rain Village),(甄)士隱的名字意思是“隱士、學者”(Hermit Scholar)(Tsao Hsueh-Chin: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trans. Chi-Chen Wang, New York: Doubleday 1929,xvi)。有趣的是,博爾赫斯筆下雨村博士的故事恰與雨有關。英軍擬向德軍發起進攻,進攻時間卻遭推遲。博爾赫斯從后來的戰爭史里讀到,推遲的原因為“滂沱大雨”(las lluvias torrenciales)。他覺得有必要把真相呈現出來,因為真實情形是德軍在得到雨村博士的情報以后轟炸了阿爾伯特,使英軍進攻計劃受阻。換言之,雨村博士的故事幾乎要溶解在“雨”的故事里,幸虧為博爾赫斯所發現(發明)。
小說中提到的那本戰爭史,博爾赫斯給出的書名是西班牙文Historia de la Guerra Europea ,并確切地指出作者是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這是英國享有盛譽的戰爭史家,該書就是名著TheReal War 1914-1918 ,出版于一九三0年(后擴充為History of the WorldWar, 1914-1918 ,出版于一九三四年)。博爾赫斯甚至還給出了具體頁碼—“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242 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 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于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動,后來推遲到二十九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有必要指出的是,西班牙語原文的兩個早期版本,即一九四二年版《小徑分岔的花園》、一九四四年版《虛構集》,都寫著第252頁。后來的版本卻嬗變為第242頁,甚至還有第22 頁、第212頁等——如此嬗變或許正有博爾赫斯的某種意圖在其中(Robert L. Chibka: The Library of Forking Paths, in:Representations ,1996)。
翻看哈特那本戰爭史書, 談論“ 延期” 一事, 的確是在第252 頁(RobertL . Chibka 誤記為第233—234頁)—英語原文是Thebombardment began on June 24th; the attack was intended for June29th, but was later postponed until July 1st, owing to a momentary breakin the weather。博爾赫斯明顯弄錯了時間,應該是六月,卻寫成七月。英軍作戰計劃是,自六月二十四日起開始持續轟炸,總攻時間定在六月二十九號。很顯然,事實是轟炸模式已開啟,總攻推遲至七月一日——正是著名的索姆河會戰正式開始的日子。其他一些細節,博爾赫斯寫得也不完全對。根據哈特所寫,戰線主要是“馬里庫爾- 塞爾”(Maricourt-Serre)。羅林森將軍(Rawlinson)的第四集團軍是進攻主力,所轄十八個師當中有十一個師參戰。英軍還有第三集團軍的兩個師在側翼輔攻,如果加到一起正好是十三個師。炮火支援不是一千四百門,而是一千五百門(Liddel Hart: The Real War 1914-1918 , London: Faber 1930)。
博爾赫斯把a momentary break in the weather 理解為下雨,并發揮為“滂沱大雨”,倒也并非無稽。雨村博士的故事就這樣與雨的故事糾纏在一起。非僅如此,雨村博士的故事還與村的故事形成關聯。他要謀害的那位阿爾伯特,住在阿什格羅夫(Ashgrove)。實際就是一個村子,地處芬頓區(Fenton),隸屬英國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博爾赫斯也的確稱它為村子—西班牙語原文是laaldea de Ashgrove。在雨村博士的故事里,阿爾伯特是“支點”式的人物。倘沒有阿爾伯特,雨村博士的故事將無法展開,更遑論成為一個故事。但應該可以想到,在雨村博士編織(謎)的活動里,阿爾伯特之為支點,抑或阿什格羅夫村作為地點,不過是一種符號性的存在而已。符號對應著怎樣的內涵,抑或阿爾伯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阿爾伯特確實沒能從雨村博士的編織里掙脫,最終還是死在他的槍下。然而,他讓雨村博士見識了(另一個)謎以及它的破解。阿爾伯特不只是符號,阿什格羅夫村同樣也是如此。
概而言之,博爾赫斯從《紅樓夢》那里借來了雨村的名字,又在王際真英譯本的啟發下將雨村的名字拆解成為雨與村。《小徑分岔的花園》可算是《紅樓夢》的一次漫游,博爾赫斯在它的啟發下構造出一個帶有套盒特點的故事。雨的故事的底下是雨村的故事,雨村的故事的底下又有一位住在村子里的阿爾伯特的故事—甚至還可進一步推擴說,阿爾伯特的故事底下還有雨村的曾祖父的故事。雨村的故事掙脫出雨的故事,使雨的故事成其為滑稽的面相。阿爾伯特的故事也掙脫出了雨村的故事,使雨村的故事也顯露出滑稽的面相。雨村的曾祖父的故事是不是也有潛能,要掙脫出阿爾伯特的故事,已然不得而知,然而并非沒有可能。誠然,博爾赫斯在這篇小說里提到的中國人并不只有雨村一人。曾祖父的名字何以是Tsui Pên,駐英國領事的名字何以是Hsi Peng,乃至曾祖父的小說的主人公何以是Fang,或許同樣另有意味,有待進一步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