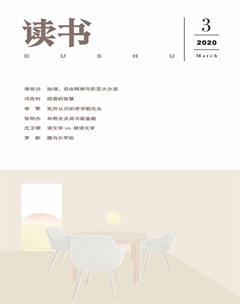林熊光及其書畫鑒藏
張明杰
在近代中日書畫鑒藏史上,林熊光是一位不容忽視的人物,其古代中國書畫收藏不僅數量大、品種多,而且質量尤高。遺憾的是,對林熊光及其書畫鑒藏的考察研究至今仍屬空白,只是由于近年來書畫文物拍賣中,不斷涉及林熊光舊藏品,才開始出現對其人的簡單介紹,但介紹文字又幾乎千篇一律,且間有訛誤。有鑒于此,對林熊光其人,尤其是書畫鑒藏活動做一系統梳理和考察,實屬必要。
林熊光生于一八九七年,字朗庵,室號磊齋、寶宋室等,系臺灣板橋林本源家族成員。林家原籍福建漳州,其先祖早在清乾隆年間移居臺灣,后數代艱苦創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尤其是林國華、林國芳一代,立足臺北枋橋鎮(后板橋鎮),苦心經營,不斷壯大家業,并聚合國華之“本記”與國芳之“源記”而成林本源家族。到了林國華之子林維源、林維讓一代,林家已發展成臺灣屈指可數的富商豪族,而且在劉銘傳督辦臺灣時,維源兄弟因輔佐有功,而得到嘉獎重用。林家在經商以及協助治臺的同時,還大力倡導文化藝術,開辦義學,并延聘儒學或金石書畫家呂世宜、謝琯樵等授學傳藝。臺灣日據時期,林家一度退避廈門。林熊光即出生在舉家返回廈門后的一八九七年三月。
林熊光的祖父即林維讓,父親林爾康英年早逝,母親陳芷芳系前清宣統帝師陳寶琛之妹,育有子女五人。林熊光屬家中老小,上有兄、姐各兩人。長兄林熊征,為盛宣懷之婿,曾擔任漢冶萍公司董事、華南銀行總理等職,還一度為臺灣首富。次兄林熊祥,娶舅父陳寶琛四女為妻,日本留學后返臺經商,且能文善書,尤以書法著稱。大姐林慕安,嫁給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二姐林慕蘭嫁給嚴復之子。在注重門當戶對的林家,林熊光雖娶日本人為妻,但選擇的也是東京士族女子。
林熊光十歲時返回臺灣,十六歲負笈東渡日本,先在皇家學校學習院學習,后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一九二三年畢業。林熊光在學期間,就曾參與創辦大成火災海上保險公司(簡稱“大成火險”),并擔任監察,一九二五年后升任常務董事及董事長,而且,他還以分家所得資產創辦朝日興業公司,并出任社長。不過,他一生的主要事業還是經營大成火險公司。

林熊光舊藏黃庭堅書《王史二氏墓志銘稿》(局部)
林熊光自幼喜讀書,同時傾心于書畫骨董等文物,逐漸磨煉出一雙鑒賞慧眼。早在學生時代,即于書畫鑒藏界嶄露頭角,其收藏的北宋黃庭堅真跡《王史二氏墓志銘稿》,于一九一九年公之于眾(《書苑》第十卷6-10號),令日本鑒藏界大為震驚。
此《王史二氏墓志銘稿》,即黃庭堅為王(長者)、史(詩老)二人起草的墓志銘文稿,后二紙合裝為一卷,是一件遞藏有緒的傳世劇跡,上有晉府寶書以及陳繼儒、項子京、梁清標、羅天池、端方等諸家印記,多達七八十處。后有董其昌、孫承澤、楊守敬、鄭孝胥、羅振玉等人題跋。日本的犬養毅曾獲觀于金陵端方處,并留下“蓋天下第一墨寶”題記,在林熊光入手后,又第二次獲觀并題跋。
關于此墨寶入手經過,林熊光曾在跋文中披露:“大正八年己未五月八日,余以萬五千金,易得此名跡于東都之文求堂主田中氏,歡喜無量。遂以尊山谷室名余齋,以志喜也。”大正八年即一九一九年,在當時一般年輕職員月工資僅四五十元的年代,一萬五千金可不是小數。時年八十四高齡的日本篆刻名家益田香遠特為其操刀刻制“尊山谷室”收藏印。此墨跡清末時為端方所藏,端方死后,其宏富收藏漸散出,常年在北京坐地收購古籍和書畫的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于其遺孀處獲得一批書跡拓本帶回日本,此即其中之一。另有部分書畫為中村不折購去,現藏書道博物館。田中將此名跡帶回后,又特請時居京都的羅振玉題跋。
該墨寶除多次現身于書畫展覽會之外,《書苑》《書道全集》等諸多文獻中也都有收錄或轉載,對書法界影響至深。西川寧在《開眼之師》(《書品》第116號)一文中,回憶恩師田中豐藏講授東洋美術史時,曾屢屢盛贊這件傳世名跡。徐邦達在《古書畫過眼要錄》中對該墨寶也有詳細考證介紹,可資參考。后來林熊光將此墨跡出讓給大阪的收藏家阿部房次郎,后經其嗣子之手,轉歸東京國立博物館,成為該館鎮館墨寶之一。
一九一九年前后,《書苑》雜志還刊載過林熊光所藏明趙左《水墨山水畫冊》(十二開)、王穉登《真跡詩卷》、王虛舟《篆字如南山壽幅》等。前者趙左畫冊后又由西東書房玻璃版影印。
大村西崖編刊的《文人畫選》(丹青社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收錄林熊光藏品四件,分別為王時敏《疊嶂草堂圖》、方士庶《松柏同春圖》、辺壽民《畫冊》和奚岡《山水冊》。從款識知,王時敏《疊嶂草堂圖》(紙本水墨,高四尺五分,闊一尺七寸),作于康熙五年,作者時年七十五,為仿黃大癡法之佳作。方士庶《松柏同春圖》(紙本水墨,高三尺八寸,闊一尺一寸五分)作于乾隆十四年,為仿元代陸廣之作,大村西崖評曰“筆墨溫藉渾厚,蓋現其人之氣韻”(《文人畫選》解說)。
當時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界,東京有大倉喜八郎、根津嘉一郎、菊池惺堂、山本悌二郎等財政界巨頭,京阪地區則有藤井善助、上野理一、黑川幸七等商界大亨,沒想到年紀輕輕的林熊光卻異軍突起,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林熊光留學日本時,正值清王朝覆亡之后,清室、王府等秘藏書畫開始不斷流出。日本國內,出于經濟原因,舊大名家祖傳寶物,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書畫骨董,也陸續入市拍賣。受傳統茶道及鑒賞趣味的影響,日本人對當時入市的中國書畫,仍重宋元,尤其是梁楷、馬夏畫派等院體畫及禪宗畫,售價一直居高不下。相反,明清書畫尚未受到應有重視,價格低廉。而林熊光身在日本,同時又有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渠道,可便捷獲取中日兩地入市或散出的書畫。尤其在一九一九年前后,隨歐洲戰爭的終結,作為生產基地的日本,經濟旋即陷入惡化狀態,美術市場也一度出現了低迷。不過,這對有經濟頭腦的林熊光來說,倒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正是抓住了這一機遇,短期內收藏了大量書畫、鈢印等文物。加之他能把握中國美術史主脈,古代書畫,宋元明清兼而收之,同時旁及鈢印、古硯等。截至一九二三年九月關東大地震時,林熊光收藏的中國書畫等文物已達相當規模。不承想,這次地震使其東京私宅連同所藏寶物,瞬間化為灰燼。另外,其收藏中,另有百余件珍貴書畫,當時曾寄存在田中氏文求堂倉庫,不幸的是,文求堂店鋪及倉庫均毀于震災大火,唯有宋張即之書《李伯嘉墓志銘稿》因臨時借往關西而幸免于難。此墨寶后為藤井善助所得,現藏藤井有鄰館,且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關東大地震后,國華俱樂部曾委托文人畫家相見香雨,對震災中損失的書畫等美術品進行調查,事后出版了《罹災美術品目錄》(一九三三年)。書中雖有文求堂整體罹災及個別重點文物的簡要記述,但只字未提林熊光寄存于該倉庫的書畫。因此,這批書畫幾乎鮮為人知,就這樣瞬間消失了。有鑒于此,震災前日本相關書刊轉載過的林熊光所藏書畫亦不應忽視,從研究角度來講,同樣具有很大價值。
震災后,林熊光在書畫收藏上仍熱情不減,加之有舅父陳寶琛這棵大樹,還有滬上鑒藏大家李拔可、黃靄農等相助,故又陸續獲得不少精品。嘗因得南宋趙伯駒《海天落照圖》、金李平甫《江鄉落照圖》、明李日華《夕照歸鴉圖》及王履《漁村夕照圖》,而將其堂室命名為“四照堂”。后又因喜獲宋徐熙《蟬蝶圖》、米友仁《江上圖》、李公麟《春圖》以及燕文貴《夏山行旅圖》,而易名為“寶宋室”。其一生尤喜用該堂號,并先后請篆刻家小林斗庵、松丸東魚、吳昌碩、曾紹杰等為其制印或題額,其收藏書畫上也多鈐有此印。
美術史學者原田尾山在官方支持下,于一九二八年開始,花費三年時間,對日本所存中國名畫進行初步調查,后在此基礎上編刊了《現日本中國名畫目錄》(一九三八年)。盡管遺漏甚多,但該目錄中仍收有林熊光藏畫六件,分別為夏《瀟湘風雨圖卷》、楊文聰《山水卷》、道濟《紀游圖詠冊》《山水精品冊》(各十二開)、朱耷《書畫合璧卷》及徐揚《御題臨大癡山水卷》。另外,《大東美術》收錄過林熊光收藏的明徐渭《花果魚蟹圖卷》,《國華》雜志還曾以玻璃版影印其所藏元吳鎮《嘉禾八景圖卷》,并刊載瀧精一撰寫的長篇鑒賞論文。這幅畫卷長達二十一尺有余,為吳鎮代表作之一,后被日本指定為重要美術品。

林熊光舊藏吳鎮《嘉禾八景圖》(局部)

林熊光舊藏王翚《仿李營邱江山雪霽圖卷》(局部)
現藏于大阪市立美術館的王翚《仿李營邱江山雪霽圖卷》,也來自林熊光舊藏。《江山雪霽》本是唐代王維的傳承作品,其后諸多山水畫家先后臨摹,本圖則是王翚據北宋李成摹本所做的再臨摹。這幅近八米長的巨幅畫卷,氣勢磅礴,宏偉壯觀,而且從研究角度來講,對探討近年來頗有爭議的王維《江山雪霽圖》也不乏參考價值。
就在林熊光收藏日益精進之時,其主導的保險公司事業卻節外生枝。一九三四年三月,日本北部港口城市函館突發大火,造成兩千余人死亡,兩萬余戶房屋被毀,損失規模僅次于關東大地震。而當時又尚無現行所謂再保險制度,林熊光主導的大成火險公司不得不支付巨額賠償。為籌措資金,更是出于道義,林熊光毅然決定放手所藏書畫等私財。京都美術俱樂部曾有過一次明清書畫專場拍賣,其書畫即來自林熊光之收藏。從當時印制的《寶宋室藏明清書畫便面展觀目錄》可知,各類書畫達二百余件,其中明清名家扇面八十七面、畫冊類三十冊、畫卷類四十卷、畫軸類四十八軸。雖名為明清書畫,但也附帶部分宋元名人作品,如梁楷《寒山拾得圖》、呂東萊《誥敕卷》、李唐《平堤散牧卷》等。二○一五年北京匡時春拍會上以兩千五百萬元落槌的《南宋呂祖謙告身》,恐為當時這件呂東萊《誥敕卷》。
對酷愛收藏的林熊光來說,命運多舛。“二戰”末期,他位于東京麴町的私宅又毀于戰火,苦心收集的書畫、鈢印等藏品多半化為烏有。其在《林朗庵乙酉劫后所用印留影》序中稱:“余歷年請諸友刻藏用印百余顆,乙酉東京寓居受炸毀,殆全部損失。是后求知友所刻及燼余之印,鈐成壹冊,以資記錄。”林熊光一生尤好鈢印,曾得羅振玉、黃賓虹等人藏印,收藏甚豐,而且在篆刻、印譜鑒賞研究方面也造詣頗深,并輯刊《磊齋鈢印選存》等。可以說,在述及近代中日篆刻印譜史時,林熊光也是不可忽視的人物。順便訂正一下,國內拍賣圖錄關于林熊光的簡介中,所謂“瑯庵”之號,與林熊光無關,應為稻垣氏之瑯庵(誤解源于篆刻家稻垣重厚所輯《瑯庵藏印》)。
此次毀于戰火的書畫究竟有多少,現已無法詳知,只能從戰前曾轉載過其藏品的雜志等文獻中略知一二。據筆者調查,三省堂《書菀》雜志自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短短四年多時間,就刊登過其十八件書畫藏品:李世倬《墨筆山水》、李日華《墨筆山水軸》、錢維城《墨筆山水立軸》、祝允明《草書詩卷》、鄭燮《書畫合璧軸》、梅清《山水立軸》、冒襄《畫梅立軸》、陳潮《篆書立軸》、郭詡《畫張子房小景圖軸》、高鳳翰《水墨松泉圖立軸》、伊秉綬《行書七言絕句立軸》、黃慎《人物立軸》、王穉登《草書五言絕句立軸》、藍瑛《淡彩霜桕文禽立軸》、笪重光《書張燕公詩立軸》、陸治《著色牡丹直幅》、羅聘《狗兒園立軸》、程鳴《山水立軸》。這些明清書畫均有一定代表性,堪稱佳作。如清初四大書家之一的笪重光《書張燕公詩》,為高四尺八寸、闊一尺七寸的綾本大軸,書錄唐代張說《游灉湖上寺》詩,有“唐燕公集,為惟德親翁書,笪重光”款識,書法瀟灑,妙趣橫生。
另外,從一九四二年秋冬之交于東京舉辦的趙之謙先生遺作展覽會可知,此次展出的書畫篆刻作品中,也有來自林熊光的七八件藏品,如行楷篆隸書額《讀書便佳》《九書屋》《意可園》《琴心花韻之軒》、書幅《晴窗賞古圖題詠》、畫卷《異魚圖》等,均為趙之謙遺作中的佳品。其中《異魚圖》,現身于西泠印社二0一一年秋拍會,后以一千一百五十萬元成交。
林熊光精于鑒藏,當然與他閱歷豐富,尤其是讀書多、見識廣有關。從其所撰《日本現存唐宋名家墨跡舉知》( 《書菀》六卷一號)一文,便可大體領略。文中列舉了日本所藏唐宋墨跡二十四件,一一加以評介,從主要著錄、遞藏,到名家品評、書體書風等,簡明扼要,點評到位。對他來說,這些赫赫名跡大多都曾寓目,有的還曾經手收藏過。例如,唐褚遂良《蘭亭敘絹本》,林熊光年少時曾于福州親眼所見;唐張旭《草書帖》,關東大地震前,上海金頌清攜此來日本時,林熊光也曾寓目;唐《響拓右軍哀禍、孔侍中二帖》《臨右軍二帖》,也分別在其恩師岡田正之家和博文堂把玩欣賞;宋蘇軾《寒食帖》,北京的顏世清攜來日本,于公使館展出時,林熊光每日均前往觀摩,并于此書卷側幾近“坐臥不能去”,后被菊池惺堂重金購去后,又不免惋惜。除前述宋張即之、黃庭堅所書墓志銘稿之外,宋蘇軾書《李太白詩》、宋《司馬溫公告身》等也都一度為林熊光所藏。
林熊光不僅富收藏,精鑒賞,而且胸懷磊落,對所藏書畫從不私秘,而是以普及共享為己任,故其藏品不少曾無私出借,用以轉載或復制,如遇知音懇求則忍痛割愛。同時,林熊光在臺灣與其堂兄弟一起創辦如水社及大觀書社,大力倡導和推廣書畫藝術,尤其對后學極為關照,張允中走上書畫收藏之路并成為此領域大家,即與林氏的指導和提攜分不開。另外,為彰顯臺灣金石學奠基者呂世宜等人業績,林熊光曾于東京自費重刊呂氏著作《愛吾廬題跋》,編刊《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并撰寫長文《臺灣金石學導師—呂西村先生》。就此而言,其對中國書畫的弘揚與普及不無貢獻。不過,同時也應看到,林熊光的收藏人生,有近半又跟日本占據臺灣,進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時期重合。作為日本殖民臺灣的協助者,這種特殊身份,也使其能在中日交惡的復雜環境下,于中日間尤其是鑒藏界縱橫馳騁。
林熊光收藏書畫終生不輟,直至晚年,還請臺灣篆刻家王壯為刻制“朗庵七十以后所得”藏印,鈐于新收書畫之上。林熊光于一九七一年去世,葬于東京吉祥寺,書法家西川寧為其撰寫碑文。
林氏家族以收藏家著稱者還有林柏壽和林宗毅。前者系林熊光叔父,其“蘭山千館”收藏甚豐,尤以中國古書畫、陶瓷器等知名,其中部分藏品已移交“臺北故宮博物院”。“蘭山千館”之名,源于其藏唐褚遂良臨《黃絹本蘭亭卷》和懷素《小草千字文卷》。而前者《蘭亭卷》,即為“二戰”后經林熊光之手獲得的鎮館之寶。林宗毅為熊光之堂弟,亦是收藏大家,尤以其“定靜堂”所藏明清書畫名世,其藏品后分別捐贈給臺北“故宮博物院”、東京國立博物館、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相關圖錄均已出版。
相比之下,林熊光的收藏則顯得有始無終。其豐富藏品有的毀于震災,有的毀于戰火,從此絕跡人間,殘留下來或后來陸續新收的,最終也未能聚為一體,而是四處星散。也正因為如此,近年國內拍賣市場才不斷有他的舊藏品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