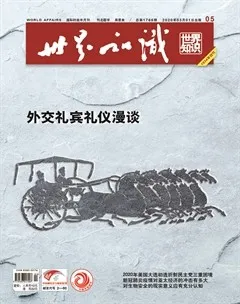對生物安全的現實意義應有充分認知
蘭順正

我軍某導彈旅官兵在高溫條件下開展帶戰術背景的防核生化武器襲擊演練。照片攝于2013年。
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現代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潛在威脅,以及對其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預防和控制措施。根據軍事常識,生物戰爭是指把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媒介(包括細菌、病毒和真菌)和毒素用于軍事用途,對人員進行殺傷、致殘,或對動植物進行破壞。2月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
微生物作戰自古有之
使用微生物對敵作戰的例子在歷史上不乏記載。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微生物進行的戰事,可能是漢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匈奴人最早使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輪臺詔”中有過記載。那之前幾年,匈奴曾將戰馬捆縛著前腿放到長城腳下,對漢軍說:“秦人,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馬。”而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即當時的“詛”或“蠱”,實際就是帶疫馬匹。漢人將病馬引入關后,致人染疾,影響了戰斗力。
公元1515年,500多名西班牙人登上墨西哥的土地后,把攜帶有天花病毒的生活用品送給當地印第安人,短短三年時間,大約200萬~350萬印第安人死于天花。到16世紀末,原來美洲大陸上的兩三千萬居民只剩下100來萬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是當代意義上最早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國家,曾使用鼻疽菌和炭疽熱菌使協約國4500頭軍用騾子受感染,后勤運輸能力受到破壞。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華日軍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1936年日軍又組建“100部隊”,名義上是關東軍抗動物流行病馬匹保護部隊。這兩支部隊主要從事生物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其研發的細菌戰劑主要有鼠疫桿菌、炭疽桿菌、霍亂弧菌、傷寒桿菌、結核桿菌、白喉桿菌、流行性腦膜炎等。
二戰后,生物戰這頭“惡獸”基本被關進了“籠子”,生物武器很少被使用。1972年各國在聯合國框架下締結《禁止發展、生產、儲存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銷毀此種武器公約》,即《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次年生效。然而,隨著科技進步,“籠門”開始松動。如果說20世紀是以原子彈、電腦、登月、因特網、手機等為代表的物理科學大爆炸時代,那么21世紀從某種意義上講便是以解碼人類基因圖譜為開端的生命科學大發展時代。
基因工程剛一問世,一些大國便競相投入經費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genetic weapon,也稱遺傳工程武器或DNA武器)。它運用先進的遺傳工程技術,用類似工程設計的辦法,按人們的需要重組基因,在一些致病細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對抗普通疫苗或藥物的基因,或在一些本來不會致病的微生物體內接入致病基因,從而制造出生物武器。合成生物學的發展可實現人工設計與合成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生物或病毒,能改變非致病微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產生具有顯著抗藥性的致病菌。基因武器有以下特點:
秘密施放,秘密感染,秘密殺傷,讓人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中彈”。即使清楚敵人使用了基因武器,由于只有制造者才知道致病基因的遺傳密碼,他人也很難迅速破譯并進行有效治療,且要查清病毒來源與屬性也需很長時間,事后肇事者也很容易做到文過飾非。
殺傷力大,成本低廉。據測算,如果建造一個核武庫需耗資50億美元,而建造一個基因武器庫僅需5000萬美元,兩者殺傷力旗鼓相當,在有些環境下基因武器的殺傷效果甚至大于核武。英格蘭北部布拉德福德大學馬爾科姆·丹多教授在《生物技術武器與人類》一書中說,只要用多個罐子把100公斤的炭疽芽胞散播在一個大城市,大量市民就會立即感染,無異于“廉價核武器”。
使用方法簡單多樣。只要將病毒放在一只密碼箱中,就有可能躲過海關檢查,戰時可以用人工、飛機、導彈、艦船、氣球或火炮進行散播,使對手在無形的戰場上靜悄悄地喪失戰斗力。
有強烈的心理威懾作用。看不見的敵人最可怕,大多平民對基因、病毒都是一知半解,以訛傳訛,最易引起恐慌,也許在將來一句“病毒來了!”就可能讓老百姓有水不敢喝,有門不敢出,工廠停工,商店關門,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崩潰。
至于能否制造出納米級“導彈”,把特定種群當作目標加以攻擊,由于人類不同種群的遺傳基因確有所不同,所以在理論上有可行性,甚至能被設計成可逆轉型,在完成作戰目的后,向被攻擊方提供“解藥”(疫苗藥物或“致病因子”及攻擊靶點的生物信息資料),從而控制攻擊的后果。
保衛“微邊疆”
基因戰距離現實世界并不遙遠。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俄外交部曾國防部等旗下多家涉外情報機構,對美國的各種生化實驗進行了高強度的調查。根據俄武裝力量三防兵司令伊戈爾·基里洛夫披露的資料,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郊區的理查德·盧加爾社會衛生研究中心是由美國陸軍醫學研究機構成立的生化實驗室。美國病毒學家在這里進行生化武器的研發。201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指出,有人在有目的地采集俄羅斯人的生物樣本資料。此言一出,即遭爆炸性傳播。俄媒隨即報道,美國空軍在一份生物樣本采購招標中將目標鎖定俄羅斯人。有俄專家警告,俄羅斯民眾的生物樣本未來或將被用于制造細菌武器,應監控此類收集活動。美國空軍教育訓練司令部10月31日向俄媒澄清說,美空軍最大醫療部隊、第59醫療部隊的“先進分子監測中心”確實搜集了俄羅斯人的生物樣本,但目的并不是制造細菌生化武器。
生物科技對未來戰爭的影響,將是全面的和深刻的,國內早有人對此給予關注,第三軍醫大學郭繼衛教授在其所著的《制生權戰爭》一書中首創了“制生權”和“微邊疆”概念。他指出,“制權體系在占領陸海空天等作戰空間后,下一步將打造超微空間作戰領域,這一作戰樣式是對科技水平的挑戰,更是對當前人類想象力的挑戰,其戰場將更復雜、更驚險和更神奇”“在制生權時代,戰爭直接在人類體內開始也不足為奇了”。
“微邊疆”概念是指建立本國的生物防御體系,以保衛本國生命的微觀疆界。從狹義理解,“微邊疆”主要是指對中國人的超微生物信息,如基因、蛋白質等種族特征性信息以及人群遺傳資源等進行生物保護的技術性劃界。廣義理解,則應該涵蓋具有國家(地域)特征的全部生命領域資源的超微生物信息研究、使用、開發,捍衛相關權益。生物防御體系的效能體現為保障國家和人民不受生物因素侵犯的能力。生物防御能力是消除或避免生物資源研究、發掘和利用過程中的危害影響以及抵御外來生物因素侵襲的實力,它是在生物領域保障國家安全的軍事潛力、經濟潛力、政治潛力和科學潛力的總和。充分認識基因戰的威脅,守住人倫道德和國家利益紅線,提早做好準備以保衛“微邊疆”,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有著“生死攸關”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