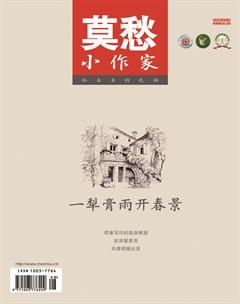爺爺的院子
庭院里的綠肥紅瘦
蘇州人的生活之所以讓人稱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講究情調。這種情調無處不在,比如栽花蒔草。有條件的會在庭院里種下玉蘭、木樨、海棠,圖個“玉堂富貴”;沒條件的,墻角窗臺也少不得幾盆月季、茉莉,或是不占空間又可賞可觀的木香、薔薇、凌霄、金銀花……再不濟也有絲瓜、葡萄、牽牛花之類。走進任何一扇不起眼的大門,庭院里都少不了綠肥紅瘦,俯仰生姿。
爺爺愛花,也善種花,退休后利用前庭后院充分發揮專長和余熱,老有所樂,老有所為。
老宅位于蘇州城東北角,自我記事,老宅的格局是這樣的:門廳下兩級石階,右手廊廡下是一間客房,坐西朝東。左邊是一個方正的大院子,中央種著一棵七八米高的泡桐樹,每年春天一樹繁花,清香不絕,映得滿院紫氣東來的樣子。花事荼蘼新葉初吐,不消月余已濃蔭匝地。
泡桐長得極快,好像正躥個子的莽撞少年,亭亭如蓋的樹冠凌駕于山墻和屋頂,起風的時候總毛手毛腳惹是生非。風雨初歇的清晨,爺爺經常一早撿拾清理被刮落的碎瓦,常常漏雨的二樓成了爺爺奶奶的頭疼事。粗大的根系也不肯安分,把好好的青磚人字紋鋪地拱得高低不平,好像地下有個巨大的八爪魚隨時會破土而出。
穿過山墻的青磚門樓,是客廳前的狹長天井,地上散石鋪成“碎碎平安”的海棠紋,夏日里頗有“日光穿竹翠玲瓏”的意境。爺爺常常躺在客廳落地窗前的竹椅上打瞌睡,腳邊的貓兒伏著青磚乘涼,只記得人面映綠,浮影成趣。東西廂房窗下紛披幾叢常青的書帶草,一眼小小的無圈老井,墻角和地面石縫里的茵茵蒼苔,觀照著歲月靜好的恬淡微涼。
穿過正廳拐過廚房,南面便是后院。院子不算小,長約十米,寬約七八米,這里是爺爺精心打造的花園。西南角上一個高約80厘米、黃石抱土的花臺,孤植一棵瓜子黃楊。枝葉蔥蘢,和院墻齊高,是貓兒們上上下下、進進出出的天然階梯,龍鐘的老干被蹭得油光發亮。黃楊端莊持重,任憑風雨來襲都不曾凌亂,頗有長者之風。其生長緩慢也出了名,還有“黃楊厄閏”一說——閏年就停止生長,因此木質堅硬而名貴,這棵黃楊算得上“宅寶”了。春天時,樹上會結一種黃豆大小、貌似小香爐的青籽,奶奶叫它“三腳蘿卜干”,為什么和蘿卜干搭上邊,我至今沒明白。
東南角上則是一棵筆直修長的棕櫚樹,比泡桐還高,方圓一兩里外就能望見我家的這個地標。棕櫚冬天依然常青,枯敗的老葉倒垂下來,卻不脫落,新老交替中,樹干又向上長了一節。冬天刮西北風的時候,院子里就比別家多了“啪嗒啪嗒”和粗糲的“沙沙”聲。隔幾年,爺爺也會請人搭著梯子爬到樹上,把那些層累堆積的枯葉剝離下來,讓樹長得更快更好。
溪山一灣的寫意
棕櫚樹和南墻的角落里,爺爺用磚和木板搭了個豪華雞舍,頂上覆著瓦片,地上鋪著厚厚的稻草。每天下午我都豎著耳朵,一聽到母雞“咯咯噠”的叫喚,保準第一個鉆進去撿熱乎乎的雞蛋,再獻寶一樣交到爺爺奶奶手里。
東面的花臺里,一樹赤丹山茶、一棵文旦、一株紅石榴傍墻而植。山茶高約2米,株型飽滿,英姿神韻。每年入冬花苞就一星半芽地鉆出,眼見著一點一點地膨大起來,隱隱可以看見紅色的裂紋。及至某個春天的早上,爺爺會把我從睡夢中叫醒“阿囡啊,山茶花開哉,快去看”,我一骨碌爬起奔出去。這株山茶年年如約,不開則已,一開便滿院生輝,獨領風騷。它的孕花期很長,花期也很長,開得盡心竭澤,直到天氣漸熱的五一前后方才紅消香斷。
紅石榴和院中間那棵白石榴,頗有“夫妻相”。每年初夏,紅榴似火,花繁葉密,秋天“子孫滿堂”;白榴卻聲色無動,兀自長得粗壯高大,偶爾懶散地在枝頭頂端開幾朵白花敷衍了事。它的樹蔭卻是我們夏天里的享受,在樹下乘涼、擇菜、洗衣、吃風涼晚飯……東北墻角則壘條石一塊,置放一棵羅漢松盆景,葉叢濃綠,姿態古雅,是爺爺的心水之物,每天早晨細細端詳、輕輕撥弄。一座水石盆景,綠蘚蒼苔,清雅可愛,點綴了小小的亭、臺、橋、釣翁,頗有溪山一灣的寫意。
西墻則是春夏的背景板。暮春時節,鄰家一株“十姐妹”每每成群結隊紅粉出墻,春歸我家。幾十年后看到鄭板橋的一首題詩:“鄰家種修竹,時復過墻來。一片青蔥色,居然為我栽。”眼前霎時便是 “滿架薔薇一院香”的圖景。夏天爺爺必傍墻種些牽牛、蔦蘿、野茉莉等一年生草本植物。每天清晨,帶著露水盛放的牽牛,紅紫紛羅,習習而動,嬌嫩得吹彈欲破,不負“朝顏”之名;鮮紅的蔦蘿,清秀可人,裊裊婷婷,我見猶憐;或黃或紫的野茉莉只把美麗留給黃昏和夜晚,因此蘇州人叫它“夜飯花”。我總是懷疑應該寫作“夜繁華”才對。
還有一串紅、鳳仙花、太陽花偏于一隅自生自滅,盆栽的天竺子、梔子花、茉莉、大麗菊……和我一樣,在這個院子里自由自在。它們都是我童年的小伙伴,也是我季節認知和植物辨識的啟蒙老師。
草木不止一春
我常常早晨醒來就先奔到院子里找爺爺,他一準在那兒,可能戴著紗線手套砌磚翻土,可能拎著大剪刀裁紅剪綠,可能弓著身子清掃落葉殘花,也可能入定一般地怔怔出神。每天晨昏定省完這些寶貝,他才放心地去吃點心、逛園林、喝早茶……
我最愛幫爺爺干的事情一是澆水,二是扦腳泥。炎夏永晝,一整天最盼著日頭偏西,趕緊催爺爺到井臺去吊水,看吊桶撲通幾下盛滿清涼的井水,灌滿那只白鐵皮大噴壺,和爺爺一起抬到后院,然后叫著“我來我來”,再不容爺爺插手。我最喜歡聽它們“嘟嘟”喝水的聲音,樹塘里的泥土有時候會吐個泡泡,我覺得那一定是誰在偷偷打嗝。樹塘澆完了,花臺澆完了,有些花花和盆景我踮起腳也夠不著,爺爺笑瞇瞇地抱起我,我笑嘻嘻地抱著壺,對著它們淋漓盡致地澆,甚至故意搗蛋,拼盡力氣把水往天空揚,咯咯笑著大叫“落雨哉落雨哉”。爺爺從來不惱,反倒夸:“阿囡乖,會做事體哉。”
老房子的墻門間、客廳、廚房、備弄等一般都是青磚鋪地,經年累月的踐踏之后,鞋底的雜泥濕土會在青磚上結成黑黝黝的泥垢,蘇州人稱之為“千腳泥”。那可是極好的花肥,找準泥垢厚實的地方,用一塊薄薄的鐵皮或鏟刀鏟下去,一片烏黑肥亮的油泥就如刨花一般翻卷起來。除了“千腳泥”,爺爺拌到花樹下的寶貝還有雞糞、煤灰、洗魚淘米水等等,它們和陽光雨露、天光地氣一道,滋養著滿園生機。
雖然沒有同齡玩伴,可我在這個自由王國里捉貓、喂雞、撿雞蛋;也坐在門坎上曬太陽,看貓撲蝴蝶、雞啄蚯蚓,或干脆數著地上的西瓜蟲、香煙蟲發呆;撿三腳蘿卜干穿項鏈,幾只蛋殼漂在水盆里也可以玩一下午;還可以騎腳踏車,搖木馬。冬天,奶奶給我用漂亮雞毛做毽子……那個樂園,給了我安全和寧靜的童年;爺爺奶奶給了我生命體驗中最珍貴的慈愛和溫暖。
拆遷時這些花木下落不明,可這么多年來,我還是常常無比清晰地想起它們,疊印著爺爺奶奶的模樣。人生一世,可草木不止一春,唯愿它們歲歲年年,活著就好。
胡亦敏:作家,文宣工作者。
編輯 張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