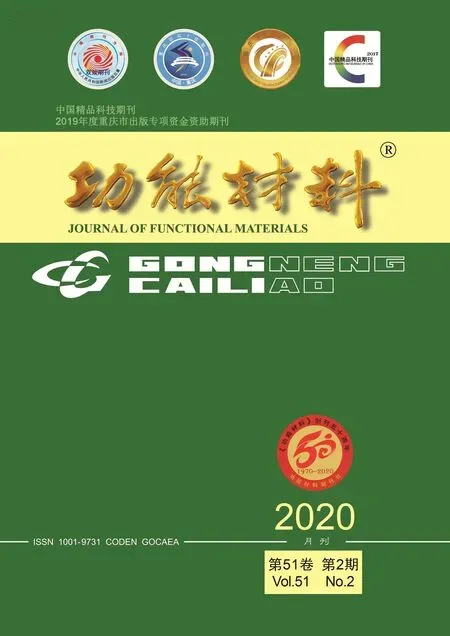第一性原理計算Fe摻雜LiMgP新型稀磁半導體的半金屬鐵磁性
陳 婷,龐 軍,何 紅,杜穎妍,向朝凱,賈 倩,劉 焦,于 越,杜成旭,毋志民
(重慶師范大學 物理與電子工程學院,光電功能材料重慶市重點實驗室,重慶 401331)
0 引 言
在現代信息技術中,對信息的處理和存儲分別利用的是半導體電子的電荷自由度和磁性材料的自旋自由度[1]。若能將電子的電荷特性和自旋特性集于一體,將其應用于信息技術中,將有望開發出集成度更高、運行速率更快、能耗更低的新型電子器件。而自旋電子學(Spintronics) 正是操作半導體中的電子自旋和電荷兩個自由度來進行對信息的加工和處理[2]。半金屬性鐵磁體 (half-metallic ferromagnet)是一個自旋方向的電子能帶具有金屬性而另一個自旋方向的電子能帶具有非金屬性的磁性材料。由于電子結構的這一特性使它們在費米面處的自旋極化率(spin polarization)為100%,被認為是制作下一代電子器件——自旋電子學器件的理想材料[3-5]。在半金屬材料中Heusler合金因為其具有較高的居里溫度(TC)、較大的磁矩、較寬的半金屬能隙[6]和可控的電磁性質而被前人廣泛的研究。
而稀磁半導體恰好能夠同時利用半導體中電子的電荷和自旋屬性,是新一代自旋電子學器件的關鍵材料,但是在II-VI族半導體中,Mn離子的不等價替換只引入了局域磁矩,不同的磁性原子濃度和不同溫度下的磁性行為各異,且摻雜成n型或p型是非常困難的[1]。傳統的III-V族稀磁半導體的磁性離子不等價替代只能形成亞穩態薄膜材料,嚴重限制了材料的固溶度[7],且制備方法直接影響著材料的質量[8]。而Ma?ek等[9]和Jin等[10]通過理論和實驗發現了一類與半Husler合金同為類閃鋅礦結構的I-II-V族新型稀磁半導體Li1±y(Zn1-xMnx)As,它可以實現自旋和電荷注入機制的分離調控,由Mn2+替換Zn2+來注入自旋,而改變體系中Li的含量則能夠調控體系中的載流子濃度。Li(Zn,Mn)As雖然有許多優異的性能,但遺憾的是TC有50 K,遠小于300 K的要求。Sato等人[11]研究了Mn摻LiZnX(X= As, P, N)體系的電子結構,結果發現Li空位不僅能夠提高體系的穩定性和TC,還能誘導Mn離子間的鐵磁交換作用.Deng等[11]發現Li(Zn,Mn)P為軟磁性材料,具有較低的矯頑力,增加體系載流子濃度能夠提高TC,由電荷和自旋分離摻雜的方法能夠合成該體系。Kacimi等人[12]采用第一性原理計算方法發現LiMgP較其他半導體具有更寬的帶隙,有望開發出性能優異的稀磁半導體材料;Sato[13]等人、Venkatesan[14]小組、Lin[15]等人和Potzger[16]等人的研究表明Fe摻雜的ZnO具有穩定的鐵磁性。因此,本文選取LiMgP為基體,采用第一性原理廣義梯度近似計算方法[17],系統的研究了不同Li含量下Fe摻雜LiMgP體系的能帶結構、電子態密度、差分電荷密度和軌道電子數,結果表明Fe單摻具有大的半金屬能隙,是一種性能優異的半金屬鐵磁體,且調節體系Li含量能夠調節載流子濃度,這為Li(Mg,Fe)P在自旋電子學器件方面的應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1 計算模型與方法
1.1 計算模型
計算選用的理想模型是LiMgP反螢石結構[18],屬于F-43m空間群,晶格常數a=b=c=0.6005nm,其中c/a=1.000。LiMgP可由Li,Mg和P反應生長后在高溫(830℃)下結晶析出[18]。根據“間隙插入規則”[20],LiMgP可看作是一個在鄰近P四面體間隙填上Li的二元復合[MgP]-閃鋅礦結構。LiMgP是直接寬禁帶半導體,帶隙值為2.43eV[18]。研究采用24原子(2×1×1)超胞模型,如圖1所示,摻雜時用Fe原子取代LiMgP中最高對稱位置上的Mg原子。為調節體系中的載流子濃度和尋求最穩定結構,分別構建了Li過量和Li不足時,3種不同Li空間占位的超晶胞,對應的結構如圖1(c) 和(d)的ILi1、ILi2、ILi3和VLi1、VLi2、VLi3所示。

圖1 Li1±y(Mg1-xFex)P的超晶胞結構
1.2 計算方法
本文采用第一性原理的方法,在MS的CASTEP[21]量子力學模塊下完成相關計算。電子波函數采用平面波超軟贗勢法[23],利用廣義梯度近似(GGA)中的PBE[22]修正.體系能量和電荷密度的積分計算采用 Monkhorst-Park[24]方案,K-point設置為5×5×5,平面波截斷能(Ecut)為520eV,體系中Li,Mg,P,Fe 各原子參與計算的價電子分別為Li:2s1,Mg:2p63s2,P:3s23p3,Fe:3d64s2,其自洽收斂精度設為2.0×10-6eV/atom。晶胞結構優化后,各項參數均優于收斂標準。對LiMgP基體,采用GGA優化后的帶隙值與實驗值更接近、總能更低,所以采用GGA的計算方法更合理[18]。摻雜體系的穩定性可根據形成能Ef來判斷[25]:
Ef=E[Li1±y(Mg1-xFex)P]-E[LiMgP]-nFeμFe+
nMgμMg±nLiμLi
(1)
其中E表示計算的體系總能,n為改變的原子個數,μ為化學勢,化學勢的取值本與實驗條件相關,這里旨在比較各體系基態的相對穩定性,所以僅在電中性情況下選取Fe,Mg,Li的化學勢為各自穩定結構下的單質能量。通過分析優化后的晶格常數、形成能和總能發現(如表1所示)摻雜體系的穩定性均有所提高,且ILi2和VLi2為最穩定位置,最后選取這兩種結構計算不同Li含量體系的性質。

表1 Li1±y(Mg1-xFex)P的晶格常數、總能和形成能
2 Li1±y(Mg1-xFex)P 的能帶結構
圖2為Li1±y(Mg1-xFex)P體系的能帶結構圖。由圖2(a)(b)可知,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子能帶完全對稱,且導帶底和價帶頂都在布里淵區的G點,故純LiMgP為直接帶隙半導體,帶隙值為1.533eV,明顯低于實驗值Eg=2.43eV[18],這是因為計算方法中的DFT為基態理論,且GGA做的是近似處理,而能隙屬于激發態,但這并不影響對Li1±y(Mg1-xFex)P電子結構及相關性質的分析[18-19]。圖2(c)(d)為Li(Mg0.875Fe0.125)P能帶結構圖。Fe摻入后最顯著的變化是在費米能級附近出現了均勻分布在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中的與Fe相關的10條自旋極化雜質帶,雜質帶寬度為0.726 eV,位于價帶頂上方Ev+0.403 eV處,為受主能級,即在費米能級(EF)下方引入了空穴載流子,表明Fe摻雜LiMgP為p型摻雜。自旋向上的子能帶表現出半導體性質,導帶底由布里淵區的G點轉變為Z點,表明體系由直接帶隙半導體轉變為間接帶隙半導體,且帶隙值增大為2.428 eV;自旋向下的子能帶中雜質帶跨過費米能級,故表現為金屬性質,從而使整個體系表現出了半金屬性質[26]。這種兩個自旋子能帶(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分別呈現出半導體和金屬特性的特殊能帶結構可以產生自旋完全極化的傳導電子,導致其在費米能級附近的自旋極化率(P)可以達到100%,明顯表現為自旋注入,體系表現出半金屬鐵磁性.而半金屬鐵磁體的優劣程度可以用半金屬能隙的大小來進行定量的分析[27],Fe摻雜LiMgP的半金屬能隙為0.500eV(表2),明顯大于Heusler合金中CrLiBi[28]的0.46eV和ZrFeVGa[29]的0.43eV,表明Fe的摻入使體系具有穩定的半金屬性,在自旋電子器件領域具有較大的應用前景[30-32]。

圖2 Li1±y(Mg1-xFex)P自旋極化能帶圖
圖2(e、f)為Li1.125(Mg0.875Fe0.125)P的能帶結構圖。可以看出,由于此時體系中Li含量的增加,導致自旋向上的EF未貫穿在雜質帶中,導帶底由G點處的1.698eV轉變到了Z點處的1.154 eV,價帶頂由G點處的-0.739 eV降低到了-0.968 eV,故帶隙值減小為為2.122 eV;自旋向下的EF貫穿在雜質帶中,體系整體仍為半金屬性,半金屬能隙為0.095 eV,較單摻時明顯減小,半金屬性明顯減弱。雜質帶寬度較單摻時減小為0.348 eV,位于價帶頂上方Ev+0.513eV處,EF向導帶移動。圖2(g、h)為Li0.875(Mg0.875Fe0.125)P能帶結構,與Fe單摻和Li過量明顯不同,Li不足時自旋向上與自旋向下的EF都貫穿于雜質帶中,體系表現為金屬性,導電性增強,雜質帶寬度明顯增大為1.268 eV。

表2 Li1±y(Mg1-xFex)P帶隙、雜質帶寬度和半金屬能隙
3 Li1±y(Mg1-xFex)P的態密度
圖3為Li1±y(Mg1-xFex)P體系的態密度圖。由圖3(a)知純LiMgP體系在費米能級附近的-2.6~0 eV上價帶主要由Li2s、Mg2p和P3p電子構成;-4.3 eV~-2.6 eV之間的下價帶主要由Li2s、Mg3s和P3p電子構成;導帶底主要由Li2s和Mg2p電子構成,其中Li的2s態貢獻最大。由圖3(b)可知Fe摻雜LiMgP后,Li2s在價帶和導帶的態密度峰的峰值都明顯減小,且在費米能級附近新出現的Fe3d態電子與Mg2p態電子的態密度的峰值出現交疊,表明Mg2p和Fe3d發生了p-d雜化作用,這種作用使得Fe3d態電子的t2g能級和eg能級處于劈裂狀態,且部分t2g能級被推向費米能級之上,使其成為半填滿狀態,對費米能級以下的占據態進行積分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體系的凈磁矩為4.02μB,其中Fe原子貢獻最大,為3.48μB,Li、Mg 和P原子的貢獻分別為-0.04μB,0.12μB,0.46μB。

表3 Li1±y(Mg1-xFex)P體系各原子磁矩和總磁矩.
從圖3(c)可以看出,當Li過量時跨過費米能級的子帶在Mg2p和Fe3d之外新增了Li2s,且Mg2p在費米能級附近的態密度峰值增大,而Fe3d在費米能級附近的態密度峰值減小,表明體系發生了sp-d軌道雜化作用,且軌道雜化的程度比單摻Fe的小,軌道劈裂程度減小,t2g能級向費米能級下方移動,體系凈磁矩減小為3.06μB,主要來自于Fe原子貢獻的2.94μB,Li、Mg和P原子的貢獻分別為0μB,-0.10μB,0.22μB。由圖3(d)可知,Li不足時跨過費米能級的自旋向上的子帶主要為p3p和Fe3d,而自旋向下的子帶主要為Fe3d和少量的Mg2p,表明體系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都發生了p-d雜化作用,體系整體上的軌道雜化作用增強,軌道劈裂程度增大,凈磁矩增大為4.64μB, Li,Mg,P和Fe原子的貢獻分別為-0.06μB,0.48μB,0.92μB,3.26μB。圖3(e)(f)為Li1±y(Mg1-xFex)P體系的總態密度圖,從圖可得,Fe摻雜后體系態密度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不對稱,體系具有凈磁矩,這與表3計算結果相符合.
表4為Li1±y(Mg1-xFex)P體系的電子自旋凈磁矩和電子自旋密度的模。2*integrated spin density代表電子自旋密度,即自旋向上電子數與自旋向下電子數的差值,它是以波爾磁子為單位的體系的自旋磁矩,2*integrated |spindensity|代表電子自旋密度的模。當二者不為0且相等時,表示電子自旋磁矩方向一致,體系具有鐵磁性;當前者為0后者不為0時,表明相鄰的電子自旋磁矩方向相反,體系具有反鐵磁性;二者都為0時,體系為順磁性[33]。為了確定摻雜模型的磁性,分別對Li1±y(Mg1-xFex)P體系自旋向上與自旋向下的電子密度進行定值計算。由表4可知,摻雜體系中2*integrated spin density和2*integrated |spindensity|值都不為0,且兩者之間的差值很小,所以在誤差允許范圍內可視為近似相等,因此Li1±y(Mg1-xFex)P(x=0.125;y=0, 0.125)均為鐵磁體,表明Fe的摻入能使LiMgP具有良好磁性。

圖3 Li1±y(Mg1-xFex)P的分波態密度圖。
表4Li1±y(Mg1-xFex)P體系的電子自旋凈磁矩、電子自旋密度的模
Table4The2*integratedspindensity,2*integrated|spindensity|ofLi1±y(Mg1-xFex)P

晶胞Li1±y(Mg1-xFex)P2?integratedspindensity/μB2?integrated|spindensity|/μBLi(Mg0.875Fe0.125)P4.000024.09847Li1.125(Mg0.875Fe0.125)P3.003193.33877Li0.875(Mg0.875Fe0.125)P4.633304.71384
4 Li1±y(Mg1-xFex)P的電荷布局、差分電荷密度和離子電子數
表5為Li1±y(Mg1-xFex)P體心原子與近鄰原子之間的重疊電荷布局和鍵長的大小。LiMgP中的Li-P鍵和Mg-P鍵的重疊電荷布局全為正值,化學鍵表現為極化的共價鍵[34]。當Fe摻入后,Li-P鍵的重疊電荷布局變為-0.05,由共價鍵變為離子鍵。Mg-P鍵的重疊電荷布局增大為0.18,Fe與P原子間的電子發生了強烈的相互作用,使得Fe-P的重疊電荷布局為0.60,表明形成了強于Mg-P鍵的Fe-P共價鍵。在Li過量情況下,Li-P鍵電荷布局為0,表明Li、P之間不成鍵。Fe-P鍵的重疊電荷布局有所減小,由圖3(c)可知,這是因為在Li過量體系中Fe3d在費米能級處的態密度值較單摻Fe時有所減小,且Fe3d軌道和其他原子軌道之間發生了相互作用,使得Fe-P鍵的相互作用有所減弱。此時Li-P鍵,和Fe-P鍵的鍵長都有所減小,而Mg-P鍵的鍵長有所增大,但整體上鍵長減小,與體系晶格常數減小相對應。Li不足時,Fe-P鍵的重疊電荷布局最大,從圖3(d)可知Fe3d態自旋向下電子在費米能級處的態密度值較單摻Fe時減小,但是此時在費米能級處新增了自旋向上的Fe3d態電子,且P3p在費米能級處的態密度值明顯增大,所以此時Fe3d軌道和P3p軌道之間的相互作用增強,使得Fe-P鍵的重疊電荷布局反而增大,增大為0.78,且鍵長最小,相互作用最強,使Li空位呈現金屬性。
表5Li1±y(Mg1-xFex)P的鍵長、重疊電荷布局
Table5ThebondlengthsandoverlappingchargedistributionofLi1±y(Mg1-xFex)P

晶胞Li1±y(Mg1-xFex)P化學鍵重疊電荷布局鍵長/nmLiMgPLi-P0.030.26176Mg-P0.140.26093Li(Mg0.875Fe0.125)PLi-P-0.050.25315Mg-P0.180.26358Fe-P0.600.25993Li1.125(Mg0.875Fe0.125)PLi-P00.25310Mg-P0.210.26426Fe-P0.560.25153Li0.875(Mg0.875Fe0.125)PLi-P-0.020.24852Mg-P0.130.26958Fe-P0.780.22430
圖4為4個體系晶面為(1, 1, 2)的差分電荷密度圖,白色區域表示得電子,黑色色區域表示失電子。由圖4(a)可知,P原子的第二層軌道被極化,電子發生內向移動,在圖中表現為P原子中間存在一部分較小的白色區域[35]。P原子表現為得電子,雖然Mg的電負性強于Li,但由于Mg的電子多于Li的電子,因此體系靠近Mg位置的P原子的電子云卻更密集,主要是Mg與P之間形成極化共價鍵且共用電子向P偏移所致。由圖3(a)分波態密度圖可知,共價鍵主要由Mg的2p態與P的3p態構成。從圖4(b)可以看出,Fe與P之間為共價鍵,由于Fe的電負性強于Mg的電負性,故 Fe的摻入使共用電子偏移P原子的程度有所減弱,雜化作用增強,P原子周圍的電荷分布仍存在方向上的極化分布,結合表5與圖3(b)可知,主要是Mg的2p態電子、P的3p態電子、Li的2s態與Fe的3d態之間形成了極化共價鍵。圖4(c)表明在Li過量情況下,較單摻Fe時,Fe原子和靠近它最近的P原子之間的電子云密集程度有所增強,且共用電子偏移程度有所減小,結合態密度圖3(c)可知,因為此時Mg的2p態和Li的2s態電子在費米能級附近的值增大,Fe的3d軌道的部分電子在和P原子軌道發生相互作用的同時也要和Mg的2p軌道和Li的2s軌道發生相互作用,這使得Fe原子和P原子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弱,重疊電荷布局的值最小。圖4(d)表明Li不足時,Fe原子和靠近它最近的P原子之間的電子云最密集,且共用電子偏移程度最小,結合態密度圖3(c)可知,Fe的3d態電子雖然在費米能級處的值有所減小,但是新增了自旋向上的一部分P的3p態電子在費米能級處的值明顯增大,此時Fe的3d軌道和P的3p軌道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強,重疊電荷布局的值達到最大,體系的磁性也最強,與單摻Fe相比,P原子的電子云存在部分缺失,這是由于Li原子的缺失使得P原子沒有得到Li原子提供的電子所引起的,故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e與P電子云最密集的原因。

表6 Li1±y(Mg1-xFex)P體系中體心離子附近各離子的參數

圖4 Li1±y(Mg1-xFex)P差分電荷密度圖
表6為Li1±y(Mg1-xFex)P體心離子附近各離子的電參數。Li*表示的是體系中填隙處的Li離子,ns、np、nd和nt.分別表示的是s、p、d軌道上的電子數和總電子數,總電子數等于各個軌道上的電子數之和,charge表示的是離子的電荷數。由表6可知,本征LiMgP中Li離子在s軌道上的電子數和總電子數皆為2.08,電荷值為0.92,此時Mg離子nt的值為7.55,電荷數為0.45,P離子nt的值為6.37,電荷數為-1.37。Fe摻入后,Li離子的ns即nt減少為2.01,也就是Li離子軌道電子數又失去了0.07,所以Li離子電荷數增大為0.99。Mg離子的ns減小0.03,np減小0.02,故nt減小為0.05,Mg離子的電荷數增大為0.5。P離子的nt減少為6.24,主要是源于np減小了0.12,因此P離子也失去更多電子使得電荷數增大為-1.24,這與差分電荷密度圖4(b)中P原子失去了更多電子的結果相符合。Li、Mg和P離子電子數減少是因為Fe摻雜之后,3種離子在原有相互作用的基礎上,會有一部分電子和新增加的Fe離子之間發生軌道雜化作用,這種相互作用使得3種離子軌道上失去更多的電子,所帶的電荷數增大,軌道電子數和總電子數減少可體現在態密度圖3(b)中Li2態、Mg2s態、Mg2p態、P3s態和P3p態的態密度值都減小。Fe離子的nt為8.33,比其他離子nt都大的原因是因為Fe元素是過渡元素,所以具有的電子數最多,其中s、p、d軌道貢獻的電子數分別為0.62、1.11、6.60。
Li過量時,Li離子的ns即nt減少為2.07,所以Li離子電荷數增大為0.93。Li*離子的ns為2.39,所帶的電荷數為0.61,其軌道電子數大于Li離子的電子數是因為Li*離子是在原有體系的基礎上填隙進去的,所以它和其他離子之間的相互作用相比其他位置的Li離子相對較弱。Mg離子和P離子的軌道電子數都有所減小,所以Mg和P離子之間的軌道雜化作用增強,重疊電荷布局增大,在費米能級處態密度值增大;Fe離子的軌道電子數增大,故Fe離子和其他離子之間的軌道相互作用減弱,重疊電荷布局的值減小。Li不足與單摻Fe相比,Li、Mg和P離子的s和p的電子數和總電子數都明顯減少,離子所帶的電荷數明顯增大,Fe離子的電子數僅增大0.03,這表明在Li不足時參與軌道雜化作用的電子數最多,軌道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強,導致Fe-P重疊電荷布局最大,體系中軌道電子數減少體現在態密度圖3(d)中Li原子、Mg原子和P原子的Li2態、Mg2s態、Mg2p態、P3s態和P3p態的態密度減為最小.
5 結論
采用平面波超軟贋勢和廣義梯度近似的第一性原理計算方法,對Fe摻雜LiMgP,Li過量和Li不足的超晶胞結構進行幾何結構優化,計算并分析了系的電子結構、半金屬性、態密度、電荷重疊布局及體系中心離子附近的電參數。結果表明,Fe的摻入能使Li1±y(Mg1-xFex)P具有較好的磁性,調節摻雜體系中Li的化學計量數可以實現體系電性和磁性的分離調控,且Fe單摻時具有大的半金屬能隙0.500 eV,半金屬鐵磁性穩定,在自旋電子學器件領域中有較大的應用前景。Fe的摻入使得Fe3d態與Mg2p態發生p-d軌道雜化,產生4.02μB的凈磁矩,主要源于Fe元素貢獻的3.48μB,體系中軌道電子數減小,離子所帶電荷數增大。Li過量時,體系中填隙位Li原子的引入使得軌道雜化作用減弱,凈磁矩減小為2.72μB,僅僅表現為微弱的半金屬性,帶隙值減小為2.122 eV,此時體系中化學鍵鍵長減小,晶格常數減小,形成能最低,結構最穩定。Li不足時,雜質帶寬度增大為1.268 eV,體系中軌道上的電子數明顯減小,Fe3d軌道與P3p軌道雜化作用增強,凈磁矩達到最大值4.64μB,表現為金屬鐵磁性,Fe-P鍵重疊電荷布局達到最大值0.78,鍵長達到最小值,Fe和P原子之間的電子云分布最密集且共用電子對偏移程度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