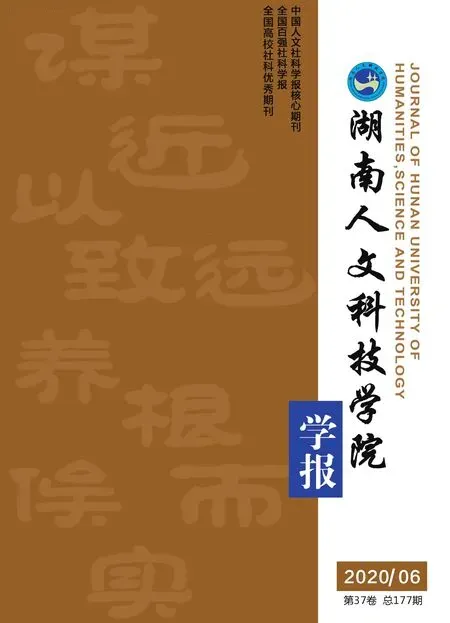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的分類與基本特征
彭健民,梁越輝
(1.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研究生教育教學部,湖南 婁底417000; 2.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湖南 婁底417000)
武陵山片區內民族眾多、農村人口占比大,于片區內的大小山系中或雜居、或聚居,形成許多各具特色的村落,創造出很多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體育項目。在長期歷史演變中,村落承載了這些體育項目的創造、傳承與變革,使其融入村民的日常起居、歲時節氣、婚喪習俗、宗教祭祀之中,是維持村落人際關系的重要紐帶,已超出了體育的范疇而成為其生活文化甚至是生存文化的一部分;時至今日,保留傳統體育內涵又融合現代體育特征的村落體育仍然是村民生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的代表依然是村落(族群)文化的表現符號、對外交流的文化名片、村落社會經濟發展的助推劑、村民團結的凝聚劑,有著極其重要的現代價值和社會功效,極具研究價值。本文以文獻資料、田野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在查閱大量相關文獻的同時,深入片區村落及村民的生活之中,廣泛調研村落體育尤其是村落節慶體育活動,旨在探究片區內村落體育的基本分布與分類,分析其結構狀態與基本特征,以期為武陵山片區區域文化發展提供助力,為進一步研究片區村落體育的現代價值與社會功效打下重要基礎。
一、片區村落體育
武陵山片區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和貧困地區于一體,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數民族聚集多、貧困人口分布廣的連片特困地區,是重要的跨省經濟協作區[1],是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的首個試點片區。
(一)片區村落體育文化
武陵山片區內多民族人口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形態,于山腰、水旁、林中形成自然村落(村莊),以民族為主體、以村落為單元產生并傳承了豐富多彩的包含體育文化在內的民族文化,并通過村落這一載體來表達和呈現。同時,由于“大雜居”和民族遷徙的存在,不同地域、民族、村落之間又相互交融,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文化(民俗、民風)的融合。因此,武陵山片區所在地域是歷史上多民族遷徙走廊和“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的典型地區,境內有9個世居少數民族,同屬西南蚩尤文化一脈,共奉“梅山教”和巫文化。片區東部(雪峰山區)雖非少數民族地區,但是古梅山地區所在地,是瑤族、苗族的祖源地之一[3],也是“梅山教”的起源區和核心地[4],還是承載中原文化與西南少數民族文化交集交融功能的“武陵民族走廊”,區內傳承至今的梅山文化自然也成為研究武陵山片區鄉土文化和瑤族、苗族村落文化的重要史料。
因片區內的生存環境比較惡劣和相對封閉,境內主要世居少數民簇(苗族、土家族等)大都有語言而無文字,由此產生了以“崇尚武勇”和“崇(信)巫尚鬼”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2]14-15。體育形態的內容是其核心內容,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以身體符號為主體,配合相應的儀式、工(道)具、服式和語言等,表達民族、村落和村民的物質與精神訴求,構建了極具特色和文化內涵的村落民俗體育和節慶體育;二是健體強魄、保家衛村(族)、表現村落(族群)實力的尚武活動。片區村落體育具有典型的民間、民俗和民族性,其以具體項目為載體,與村民的日常起居、歲時節氣、婚喪習俗、宗教祭祀息息相關,是維持村落人際關系的重要紐帶,已超出了體育范疇而成為人們生活文化甚至是生存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來,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不斷認識,村落體育的變遷呈現內在神巫色彩逐漸減退、外在健身娛樂功能逐漸增強的特點。同時,受現代體育的沖擊與融合,村落體育的變遷正處于加速期,民族(間)體育的現代化改造與現代體育的鄉村化融合齊頭并進,呈現出現代體育文化融入鄉村、本土化發展的當代村落體育文化格局。
(二)片區村落體育項目
武陵山片區內“大雜居、小聚居”所形成的村落(族群)是產生和發展村落體育的主體,并以項目的形式傳承,從而擁有了豐富的民族、民俗和民間體育項目。根據各研究文獻、各地政府網站和實地調研的不完全統計,這些體育項目主要包括:春游、地方武術(梅山武功、苗族武術、土家族武術、瑤拳、湯瓶拳、板凳拳)、摔跤、茅古斯、儺戲、九子鞭、舞蹈(擺手舞、跳喪舞、銅鈴舞、跳馬舞、花鼓子、蘆笙舞、銅鼓跳舞、板凳舞、花鼓舞、跳得舞、接龍舞、木鼓舞、爬花桿舞)[2]129-181、圍鼓、舞龍(草龍、火龍、板凳龍、潑水龍)、舞獅(獅子、高臺獅子)、舞龍燈、花燈(唱花燈、高花燈、板板龍燈)、龍舟(賽龍舟、獨木龍舟競渡)、斗家畜家禽(斗水牯牛、斗山羊、斗牛、斗豬、斗雀、斗雞)、玩牛、抬故事、拔河、踩高蹺、登高、蕩秋千、踩雞蛋、打長鼓、打陀螺、打鉚球、打梭兒、打匕棒、打彈弓、打篾雞蛋、射弩、射箭、摔跤、跳花棍、搶花炮、拔腰、跘跤、木球、踢毽子、花式跳繩、爬桿、趕老牛、順風扯旗、中幡、摜牛、方棋、跳格、踏腳、彈腿、較腳勁、耍麒麟、潑泥賜福、跳花盆、糠包、拋繡球、叉草球、抵杠、德砂呱、雜耍、擊鼓、搶鴨子、扭扁擔、拉鼓、穿花衣裙賽跑、穿針賽、斗角、搭撐腰、石擔、肉連響、跳紅燈、打飛棒、牙力、跳桌、打粉槍、游泳、踩獨木、切水、打木球、抵肩、跳偉登、跳大把、頂斗、三雄奪魁、拔蘿ト、跳高腳馬、春谷子等、哆毽、滾爛泥、耍春牛、打湯碟、跳高、蛇龍、趕猜、甩糖包等上百種[5-8]。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片區內勞動人民所創造的體育項目遠不止上面所列舉的這些,還有更多的體育項目或埋沒于歷史長河中、或由于調查所限沒有被統計進來。
民族、民俗、民間體育項目是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的主體。隨著村民生活用具的逐漸現代與豐富,以及農村學校和鄉鎮政府體育設施配置的提高及相關人員的體育示范與引領,現代體育逐漸融入村落體育,出現了具備現代特征的體育活動,如各種球類運動(如籃球和乒乓球)、跳山羊、單(雙)杠、跳皮筋、滾鐵環等。交通的高速發展(以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為標志),也使片區村落融入現代社會生活的進程大大加快,現代體育快速地融入了村落體育中,如籃球和廣場舞等現代項目已成為村落體育的主要項目和節慶的保留項目(如春節的籃球賽)。除此之外,村落的部分時尚項目(如“微型馬拉松”)亦與城市沒有差別。
二、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的分類
武陵山片區不同的聚居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發展,產生了目的、內涵、形態、方式各異的村落體育,且項目繁多、千姿百態。因此,對其分類實有必要,依其功能表達和價值指向可分為宗教祭祀、民俗節慶、防衛御敵、強身健體、娛樂身心5類體育項目,如表1所示。

表1 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項目分類統計表
(一)宗教祭祀類
宗教祭祀類項目的產生和傳承與族群(村落)的宗教活動有關,其原本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并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內容逐漸豐富、規模不斷擴大、規則不斷完善,通常是歌舞樂一體,反映和傳承族群(村落)的生產生活文化。雖然這類項目在現代已基本剝離了其宗教色彩而成為表演甚至娛樂項目,但在偏遠地區仍承擔著民間宗教活動功能。
(二)民俗節慶類
民俗節慶類項目往往脫胎于宗教祭祀類項目,是民眾在民俗節慶期間的群體歡慶表現與愉悅表達。現在,現代體育逐漸融入部分地區,在不同的節日里充當主著要角色,比如春節的村落籃球賽。
(三)防衛御敵類和強身健體類
防衛御敵類和強身健體類項目應該是片區內出現最早并傳承至今的體育項目形式,兩類項目在古代并存于一體,以技擊(武術)為核心逐漸發散和發展。這些體育項目緣于古代山區爭斗頻繁,民風彪悍,習武、練拳、操械能起到改善生存狀況、防衛御敵的作用,這從片區內習武成風,各地“武術之鄉”有著超然地位可得到證實。熱兵器時代來臨后,習武防身的作用大大降低,民間習武熱情大幅減弱,兩類項目才開始逐漸分離、各自成型。受現代體育的沖擊,許多傳統項目不斷被邊緣化和弱化,甚至走向衰亡,這對保護村落體育的多樣性極其不利。
(四)娛樂身心類
娛樂身心類項目多以小型、簡單、即興的方式存在,往往存在于田間地頭,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而改變,調劑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情趣。改革開放以來,村落“空心化”、田間生產方式的改變、人民休閑娛樂方式的多樣化與“電子化”,導致“田間地頭”項目基本已只存于人們的記憶之中。
片區村落體育除按功能分類外,還可以按其他方式進行分類。按項目所用道具劃分可分為舞圖騰類、斗家畜家禽類、舞生產器械類、打擊樂器類、體操武術類等;按項目開展的方式可以劃分為競技類、表演類、休閑娛樂類、益智類等;按項目參與人數可以劃分為多人(群體)類、雙人類、單人類;按體育項目的受重視程度可以劃分為特殊保護類(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一般性質類(特殊保護類以外的項目)。
三、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的分布
武陵山片區人口總計1 200多萬人,約占全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1/8[2]5,片區各地主要民族分布見表2。

表2 武陵山片區各地主要民族分布情況統計表
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由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眾多民族所創造。因宗教信仰、生活環境、生產條件和文化傳承方式的不同,各民族所創造發明和傳承的體育項目各有不同、各具特色或各有側重(見表3),但其無一例外都是各民族(村落)文化核心組成部分,尤其是片區內多個少數民族有語言、無文字,村落體育或村落體育為構成成份的族群活動(主要是宗教祭祀和節慶慶典活動)承擔了族群(村落)文化傳承功能,是維系族群(村落)象征的符號,甚至是村落實力的表現(如村落的習武傳統)。

表3 武陵山片區部分民族村落體育分布情況

續表
與此同時,武陵山片區各民族長期“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形態決定了片區民族融合和文化開放程度高,內外交流不存在語言文化障礙的特點,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文化為特色的多民族地域性文化[1]。作為這種地域性文化核心組成部分的村落體育,一方面和民族聚居地具有分布統一性,并隨著族群(村落)的歷史變遷和社會發展而形成各具表現形式的反映民族特征的體育項目群,另一方面則不斷沖突與融合,繼而形成既具武陵地域文化特色又具時代特征的村落體育體系。各民族在村落體育的舉辦形式、活動內容以及參與主體等方面可能會有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因文化的脈絡維系,其村落體育的功能價值、文化內涵和精神訴求等都大同小異,與時代同步。這種“融合”現象在當代更為突出,一是民族體育項目的聚集和跨民族參與,如各級民族運動會;二是現代體育項目的“村落化”,如在片區各地鄉鎮以村落為主體如火如荼進行的“春節籃球賽”及“廣場舞賽”。
四、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的基本特征
武陵山片區內各民族以大雜居、小聚居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形成各式各樣的村落,或依山而建、或伴水而成,在自然的生產生活中產生了形式多樣又具有區域文化特性且獨自傳承的村落體育,表現出獨特的自身特點。
(一)村落體育的地理適應性與地域差異性
武陵山片區地域遼闊,東西縱橫和南北跨度都比較大,呈現出西高東低、北高南低的地形特點,集合了山區和丘陵地區的地理特征且水系豐富。因此,境內居民所創造和傳承的村落體育有著與片區地理相一致的特征:一方面,村落體育具有地理適應性特征,表現在受片區地理影響呈現集中與小型的形態特征、受村落人群聚居影響呈現統一與集體的組織特征、受生產生活影響呈現簡潔與實用的動作構成特征;另一方面,村落體育具有地域差異性特征,這一方面的特征恰好是由地理適應性特征所決定的,片區內越往西北,山地越多,村落體育呈現出山地體育的特性,形成諸如爬花桿、過刀山、蕩秋千、摔跤、斗家畜家禽等山地體育項目,越往東南,盆地越多且水系流域更廣,村落體育則呈現盆地體育和水域體育的特性,形成諸如舞龍舞獅、拔河、龍舟等盆地體育項目和水域體育項目。
(二)村落體育的民族多樣性與項目融合性
武陵山片區生活著30多個民族,各有各的文化傳統與傳承,由此衍生出許多獨具特色的村落體育活動,帶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和人群特征,比如土家族的擺手舞、仡佬族的打篾雞蛋、亻革家族的跳蘆笙、水族的耍水龍、瑤族的瑤拳等。這些村落體育活動是族群生產生活的文化沉淀與符號表現,體現本民族的價值取向,其中又以反映民族核心文化內涵的宗教祭祀體育和節日慶典體育最具本民族的文化符號特征,是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主要構成部分,由此展現了片區村落體育的民族多樣性。
武陵山片區形成了以“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為主要形式的民間信仰,是融合“儒道釋”于一體的“宗教文化”[2]5-16。各民族文化由此實現了交往和交融,村落體育也自然互相影響和融合,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各民族開展相同的體育項目,如龍舟競賽和舞龍舞獅(漢、苗、土家族等)、斗牛(苗族、侗族、水族等)、射箭射駑(布依、亻革家、侗、瑤族等),因為各民族的傳承不同,這些共同的項目還是會存在一些內在文化和外在形態方面的不同,以呈現各自民族的特質;另一方面是一個民族獨有的村落體育項目在傳承過程中,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因素來改造自身以適應發展需要,比如各民族傳統武術在不同民族文化尤其是“儒道釋”文化的融合中,逐漸趨于現代武術,再如經返鄉大學生的演示和推廣,盛行高校近20年的競技龍獅內容逐漸取代鄉村傳統龍獅內容。現代體育項目和傳統體育項目的融合性則顯得更加突出,一是傳統村落體育項目的現代化改造,如各地龍舟項目已趨同為“龍舟競速”;二是現代體育“村落化”,如日漸興盛的“村落籃球賽”和“村落廣場舞”。
(三)村落體育的民族、民俗與民間性
武陵山片區由原有的濮人、巴人、越人、三苗與南下西進的楚人不斷融合,成為多民族雜居區[2]17-69,現有包含9個世居民族在內的30多個民族居住其中。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各民族均產生了服務于本民族、體現其民族價值、具備民族特征的民族體育,這些民族體育傳承于族群聚居的村落,是典型的村落體育。各民族文化在歷史傳承與發展中,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俗習慣,造就了片區內“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民俗格局。由民眾創造和使用、具有儀式(模式)性和集體性,且維系傳統的村落體育項目是反映這種民俗格局的主要表現成份,如擺手舞、茅古斯、“團龍”[9]、苗族鼓舞、龍舟等便是各族群(村落)的典型民俗體育。村落歷來是社會組織的底層結構,居住其中的民眾亦是社會階層的底層,由其創造和傳承的村落體育自然屬于民間體育。
與其他地方不同,武陵山片區絕大部分時期是處在地方(族群)自治或官方(朝庭)的松散管理之下,村落體育的民族性、民俗性和民間性更加明顯。但在當代,由于民族融合加劇,生活方式受到現代化影響,片區村落體育的這種特性有所弱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四)村落體育的“武勇”特性
自然地理環境和村落聚居的人居環境,鑄造了武陵山片區獨具特色的山地丘陵文化,其核心是“崇(信)巫尚鬼”的族群維系文化、“農耕漁獵”的生存文化、“擴張防御”的斗爭文化。因此,境內各民族“祖先崇拜”的對象基本是“勇猛”的先人,勇敢精神是各民族文化的內核和貫穿史詩、歌謠、傳說、故事的主線[2]15。軍事斗爭貫穿民族歷史發展進程,成就了該地域的尚武文化,血性與“蠻”性是其文化特質。
在這種尚武文化的培育下,武陵山片區村落體育自然表現出內“勇”外“武”的文化特性。內“勇”表現為族群利益優先、一致對外,有膽有識、進退有據,吃得苦、“霸得蠻”、舍得命。在具體項目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如賽龍舟、舞龍獅、茅古斯等集體項目的儀式(規矩、利益)、內容(歌頌英雄、贊美勇敢)和動作(團結、協同);二是如“團龍”(斗龍比武)、斗家禽家獸等爭斗(競技)項目的勇猛(精神、意志)、求勝(力量、速度、技巧);三是過刀山等危險項目的極限(膽識、血性)、挑戰(技巧、精神)。外“武”則表現為村落(族群)習武成風、成員以習武為榮,武術是村落和村落成員的實力象征及文化名片。
(五)村落體育的健體性與娛樂性
村落體育是勞動人民群眾同自然、同社會做斗爭的產物,因此,原始村落體育帶有濃厚的宗教性、家族性和健體性。隨著社會進步,科技昌明,粘附在村落體育上的宗教、家族等屬性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健體性和娛樂性的逐漸增強。
健體性是體育的本質屬性,貫穿于村落體育的發展全程,但在不同發展時期,其目標指向是不同的。當村落是一個個獨立存在的社會單元時,對內自給自足、對外需擴張與防御,此時的村落體育更多的是作為軍事體育存在,呈現出集體組織性和斗爭專門性,因是以“武”為主、以“力”為質,人們往往采用簡單、直接、對抗的方式進行訓練,傳統梅山武術常采用80多斤的石鎖進行練習就是明顯的例證。這種時代背景下,村落體育的健體性服務于集體而非個體,目的是提升村落集體的斗爭實力而非村民的體質健康。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片區內的村落衍變成基本的社會治理單元,村落間的交流變得日益頻繁和和平,村落的“軍事”功能基本喪失,村落體育傳承與發展的維系之“筋”由斗爭逐漸轉為“娛樂”,其健體性轉而服務于個體而非集體,活動的方式也逐漸向多樣、多變與非對抗的方向轉變,強調健體和娛樂的雙重屬性以及個體的身心愉悅,最能說明這種轉變的就是片區內各傳統武術(如梅山武術)的衰敗和部分現代體育項目(如籃球賽)在村落間的快速興盛。
村落體育發展到一定程度,體育項目也逐漸豐富并分類發展,娛樂性自然而然地成為其內在屬性。追根溯源,村落體育的娛樂性應起源于片區內各族群的祖先神靈崇拜,遵循“娛神(鬼)”繼而“娛人”直至“娛己”的發展脈絡。現在,片區內村落體育的娛樂性正呈現“娛人”與“娛已”并行不悖、各自發展的態勢:有著傳統文化內涵、能夠“娛人”的項目逐漸成為鄉村經濟的助推劑;貼近生活、能夠“娛已”的項目成為村民的“新寵”;既不能“娛人”又不能“娛已”的項目逐漸消失。
五、結語
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武陵山片區創造和傳承的村落體育項目如過江之鯽,數不勝數。但從項目的功能來說,村落體育項目無外乎宗教祭祀、民俗節慶、防衛御敵、強身健體、娛樂身心5類。隨著時代的進步,宗教祭祀類項目逐漸向民俗節慶類轉變,防衛御敵則向強身健體類和娛樂身心類轉變,5類項目逐漸變為3類項目;片區村落體育因歷史變遷逐漸形成地理適應性與地域差異性,民族多樣性與項目融合性,民族、民俗與民間性,“武勇”特性和健體性與娛樂性5個方面的基本特征,但這些特征與時代緊密關聯,并根據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傳承、創新和發展片區村落體育,應遵循其發展的內在規律表現其與時代合拍的基本特征,才能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