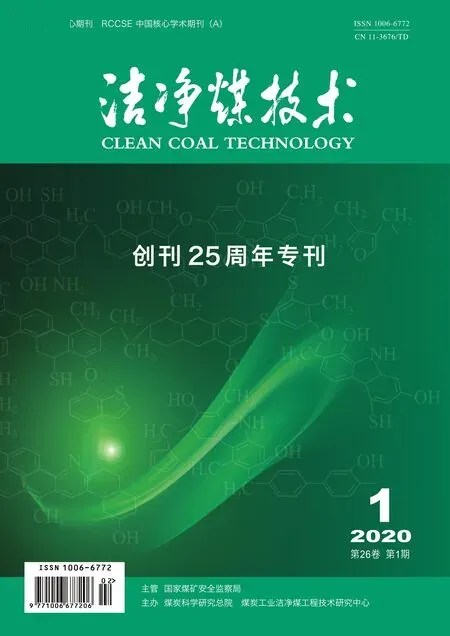300 MW循環流化床鍋爐大比例摻燒煤泥試驗研究
張 平,陳陸劍,江 華,張 縵,徐 巍,劉 實,楊海瑞,呂俊復
(1. 國投盤江發電有限公司,貴州 盤州 553000;2. 清華大學 能源與動力工程系 電力系統及發電設備控制和仿真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4)
0 引 言
我國是煤炭消耗大國,2017年我國的一次能源消耗量中煤炭占比超過60%[1]。煤炭資源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儲量有限,不僅要加強高品質煤的利用,對低品質煤(煤泥、矸石等)的利用也不容忽視。煤泥是煤炭分選過程中的主要副產品,產量巨大,煤泥具有顆粒細、水分大、灰分高、黏度大、持水性強、內聚力大、難以運輸等特點,在堆積狀態下形態不穩定,極易造成環境污染[2]。目前處理煤泥大多采用摻燒方式,循環流化床(CFB)鍋爐具有燃燒溫度低、負荷調節范圍廣、燃燒效率高、污染物控制效果好等優點,廣泛應用于低品質燃料利用領域,比較適合燃用煤泥,因此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循環流化床是一種能夠形成流態化的裝置,主要由帶布風板的提升管、分離器以及回送分離物料的回料裝置組成。提升管內的固體物料流化狀態與物料性質和流化風速有關,可以是鼓泡床、湍動床、快速床以及氣力輸送[3]。
邵偉等[4]在一臺440 t/h的CFB鍋爐中進行試驗,發現摻燒煤泥比例增加可使床溫降低,提高脫硫效率,CFB鍋爐仍可正常運行,當煤泥摻燒比例為50%~60%時,鍋爐效率達到峰值。劉彥鵬等[5]在一臺300 MW亞臨界參數CFB鍋爐中進行摻燒試驗,當煤泥摻燒量達到40 m3/h(約30%給煤量)時,床溫下降約30 ℃,飛灰含碳量變化不明顯,底渣含碳量升高,鍋爐效率下降。劉吉堂等[6]研究發現,在大比例摻燒煤泥的情況下,煤泥在爐內的凝聚結團特性是影響CFB鍋爐穩定、高效燃燒的關鍵,在設計與改造現有鍋爐時,應考慮爐內受熱面吸熱份額的變化以及煙氣量和煙氣溫度的變化。前人研究大多是小鍋爐摻燒,摻燒比例也較低,實際運行中不是僅燃用矸石與煤泥的混煤,對于300 MW的CFB鍋爐大比例摻燒煤泥的情況研究很少。
貴州盤北電廠是貴州省首個30萬千瓦CFB機組資源綜合利用發電項目,以盤江礦區煤泥及煤矸石為主要燃料,綜合熱值小于9.63 MJ/kg。投產以來,盤北電廠與清華大學合作開展了煤泥、煤矸石大比例摻燒及機組適應性創新研究,實現了將煤泥、煤矸石等低熱值燃料變廢為寶。自2013年7月投產以來累計利用煤泥、煤矸石1 000多萬噸,其中,2018年累計利用煤泥200多萬噸、煤矸石50多萬噸。近幾年來,盤北電廠的煤泥摻燒比例穩步提高,目前可達84%,中低負荷下摻燒比例最多可達100%,在全國同類型機組中屬領先水平。
本文主要針對不同煤泥矸石摻燒比例下的CFB系統物料平衡進行模型計算,研究不同摻燒比例對爐內物料平均粒徑、物料濃度分布、顆粒停留時間的影響,從而確定大比例摻燒煤泥條件下的流態優化條件,通過流態重構提高煤泥在爐內停留時間和燃盡率。根據盤北電廠實際運行情況,分析了燃用的煤泥比例對鍋爐床溫、底渣與飛灰含碳量、排煙溫度等參數的影響,并根據得到的結果給電廠的優化運行提供建議。
1 電廠概況
盤北電廠運行的循環流化床鍋爐由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設計制造(型號SG-1036/17.5-M4507),鍋爐的設計參數見表1。該鍋爐為亞臨界參數、帶中間再熱、單汽包自然循環、島式布置、全鋼架支吊結合的循環流化床鍋爐。鍋爐爐膛高40.1 m、寬29.4 m、深8.9 m,錐段高10.0 m。鍋爐采用水冷式旋風分離器進行氣固分離,運轉層標高為 12.6 m。目前CFB鍋爐摻燒煤泥的方式大多采用頂部給料和中部給料[6],經對比分析,考慮到大比例摻混煤泥的實際需要,采用頂部給料方式。為了實現大比例摻燒煤泥,最高摻燒比例100%的目標,盤北電廠對煤泥輸運設備和管道進行改造。

表1 鍋爐設計參數
2 摻混煤泥比例對鍋爐物料平衡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國投盤北電廠300 MW CFB鍋爐機組,鍋爐結構較為復雜,因此對鍋爐結構進行簡化,只保留爐膛、分離器、回料閥等主要部分。利用清華大學開發的一維物料平衡模型[7],對滿負荷條件下燃用矸石和煤泥混煤系統的物料平衡進行預測,探究不同矸石和煤泥摻混比例下CFB鍋爐物料濃度、顆粒停留時間、循環流率等參數的變化,采用流態重構理論確定了流態優化的條件。一維模型的詳細介紹可參照文獻[8]。
對于機組燃用的矸石與煤泥2種低熱值燃料,其工業分析、元素分析及熱值見表2。矸石與煤泥的摻混比例為45∶55和65∶35,分別記作混煤1和混煤2,2種混煤粒徑分布見表3。由于煤泥的顆粒粒徑較小,超過95%均在0.3 mm以下,因此煤泥占比大的混煤1中,小粒徑的煤樣比例較大,而中間粒徑的煤樣比例較低。

表2 2種燃料的工業分析及元素分析

表3 2種摻混煤樣的原始粒度分布
2.1 矸石和煤泥的成灰特性
循環流化床鍋爐作為一進二出的平衡系統,床內床料主要來自給煤中的灰和脫硫劑。物料的循環流率、床料的粒徑分布等對于流化床的運行極其重要,可影響燃燒室內的熱負荷分布、燃燒效率和脫硫效率。在特定流化風速下,物料循環流率由床料質量(即床料粒徑分布和床存量等)決定,而床料質量與系統物料平衡密切相關[9]。作為一進的給煤是CFB鍋爐爐內循環灰的主要來源,為了合理設計鍋爐本體和附屬設備,需要了解燃煤的成灰特性。
成灰特性為煤樣經燃燒后成灰的粒度分布特性。前人對成灰特性的研究結果表明,煤顆粒的碎裂過程對顆粒前期磨耗沒有影響[10-11],即在流化床燃燒條件下,磨耗和碎裂對最后灰粒徑分布的影響是相互獨立的,為此,清華大學提出采用靜態燃燒和冷態振篩磨耗進行煤種成灰試驗研究[12]。
矸石的灰分大,但其熱值和揮發分低,因此燃燒不劇烈,基本不存在熱應力及揮發分析出導致的爆裂現象。表4為不同粒徑矸石的成灰特性,可見,成灰粒度分布基本反映了給煤粒度的分布,即矸石的成灰性能很差。

表4 不同粒徑矸石的成灰特性
圖1為煤泥的原始粒度及成灰粒度分布,可以看出,煤泥粒度分布主要在0~1 000 μm,其中100 μm以下占比超過60%。由于煤的粒度較小,在燃燒過程中爆裂現象不明顯,基本不存在由于爆裂導致的粒度變化,除了在最細的30 μm粒度級,煤泥成灰粒度占比約50%,明顯高于煤泥在該粒度級占比40%,因此可考慮用煤泥的粒度分布直接代替成灰粒度分布。其中構成循環灰主體的灰粒度[13](100~300 μm)占40%左右。因此通過在矸石中摻入煤泥可有效改善外循環流率和飛灰的流率。

圖1 煤泥的原始粒度及成灰粒度分布
2.2 不同混煤比例對爐內物料平均粒度的影響
矸石/煤泥為45∶55、床壓降為5 kPa時,經計算飛灰占比約為39%,循環流率為7.52 kg/(m2·s),此時混煤的成灰特性可滿足CFB鍋爐的物料平衡要求[14]。爐膛內平均顆粒粒度為218 μm,排渣粒度為261 μm,飛灰平均粒度為28.1 μm,如圖2(a)所示。當矸石/煤泥為65∶35、床壓降為5 kPa時,經計算飛灰占比約為26%,循環流率為5.56 kg/(m2·s),此時混煤的成灰特性較差,CFB鍋爐內的物料平衡一般,需要改善。爐膛內平均顆粒粒度為208 μm,排渣粒度為304 μm,飛灰平均粒度為27.2 μm,如圖2(b)所示。對比2種混煤比例的模擬結果發現,增加煤泥的比例可提高循環流率,有利于CFB系統內的物料循環,但同時也會增加飛灰份額,對尾部煙道和受熱面產生不利影響。
2.3 不同混煤比例對顆粒停留時間的影響
圖3為不同混煤比例對顆粒停留時間的影響。顆粒粒徑在0.1 mm及以下時,混煤比例對顆粒的停留時間影響較小;粒徑大于0.1 mm時,提高煤泥比例有利于增加顆粒在爐內的停留時間,有利于0.1~0.3 mm煤泥燃盡。矸石煤泥比例為65∶35時,模型計算得到較大顆粒的停留時間約為1 100 s,這主要是由于排渣比例增大,導致大顆粒的停留時間降低,而矸石屬于較難燃盡的煤種,為保證較大顆粒有足夠的停留時間,建議控制矸石的入爐煤粒徑。

圖2 飛灰、循環灰、底渣和床料的粒度分布

圖3 不同混煤比例時顆粒的停留時間
2.4 不同混煤比例對物料濃度的影響
圖4為沿爐膛高度固體物料濃度的分布。2種不同混煤比例下的固體物料濃度分布基本相似,鍋爐下部密相區物料濃度大,上部稀相區的物料濃度較小。根據計算結果,矸石煤泥比例為45∶55時,爐膛上部顆粒濃度可達2.67 kg/m3;矸石煤泥比例為65∶35時,爐膛上部顆粒濃度只有2.34 kg/m3,說明提高混煤中煤泥比例,爐膛上部的顆粒濃度增加,有利于提高爐膛上部的傳熱,降低爐膛溫度,且有利于顆粒團的形成[15],從而強化爐膛物料的內循環,有利于進一步提高煤泥的停留時間,增加燃盡度。

圖4 沿爐膛高度固體物料濃度的分布
3 摻混煤泥比例對鍋爐性能的影響
3.1 負荷和煤泥比例對床溫的影響
由于摻燒的煤泥含水量較高、平均粒徑較細,在大比例摻燒煤泥過程中使床溫降低,嚴重時可導致鍋爐熄火[16]。圖5為摻燒煤泥比例對鍋爐運行床溫(密相區平均溫度)的影響。可以看出,在鍋爐負荷為300 MW時,煤泥出力從0增加到100%過程中,床溫從970 ℃下降到935 ℃;當摻混煤泥達到100%時,鍋爐床溫仍保持935 ℃,處于正常運行床溫范圍內。摻燒煤泥解決了高床溫時環保指標達標困難的問題,降低床溫對控制SO2和氮氧化合物排放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降低了爐內脫硫石灰石的耗量。

圖5 300 MW負荷下煤泥量對床溫的影響
圖6為不同負荷下投煤泥對床溫的影響。可以看出,隨著鍋爐負荷的增加,床溫持續升高。鍋爐負荷在179~300 MW時,投煤泥工況下的床溫均低于不投煤泥時的床溫。

圖6 不同負荷下投煤泥對床溫的影響
3.2 煤泥比例對飛灰和底渣含碳量的影響
在鍋爐負荷為300 MW時,煤泥含量對底渣和飛灰含碳量的影響如圖7所示。可以看出,隨著摻燒煤泥比例的增加,飛灰含碳量呈升高趨勢,主要是由于飛灰占比增加,摻燒的煤泥含水量較高,在爐內燃燒后會增加煙氣流量,導致超細顆粒逃逸增加,同時爐膛溫度降低,這也是飛灰燃盡率降低原因之一。煤泥在入爐后水分蒸發過程中會出現結團現象,影響燃燒效率,增加鍋爐的飛灰含碳熱損失[6]。底渣含碳量的影響規律則呈相反趨勢,即隨著摻燒煤泥比例的增加,底渣含碳量呈下降趨勢。這主要是由于摻燒煤泥后,飛灰占比增加,導致排渣量減少,從而延長了大顆粒的停留時間,提高了矸石的燃盡度,因此摻燒煤泥后底渣含碳量降低。

圖7 煤泥含量對底渣和飛灰含碳量的影響
3.3 摻燒煤泥對排煙溫度的影響
圖8為300 MW負荷下煤泥含量對排煙溫度的影響。可以看出,鍋爐負荷為300 MW時,隨著摻燒煤泥量增加,鍋爐的排煙溫度持續升高。這是因為煤泥含水量較高,大量摻燒煤泥后會增加煙氣流量,這些水分在爐內加熱、蒸發、過熱的過程中會帶走更多熱量[6]。

圖8 300 MW負荷下煤泥含量對排煙溫度的影響
不同負荷下投煤泥對排煙溫度的影響如圖9所示。在相同負荷下,運行中投煤泥后的排煙溫度要高于不投煤泥時,且隨負荷的升高,2種情況下的排煙溫度差值增大,即在鍋爐高負荷時,投煤泥對排煙溫度的影響更大。為了減少排煙損失,建議適當降低煤泥水分,同時加強尾部煙道吹灰和除塵器入口煙溫監測,減少煙道漏風。

圖9 不同負荷下投煤泥對排煙溫度的影響
4 結 論
1)增大煤泥的摻燒比例,可提高CFB鍋爐的循環流率,增加爐膛上部顆粒濃度,延長0.1 mm以上顆粒物料的爐內停留時間,利于降低飛灰含碳量。
2)鍋爐負荷為300 MW時,隨著燃用煤泥的比例增加,床溫呈下降趨勢,最高可降低約35 ℃。
3)鍋爐負荷為300 MW時,飛灰含碳量隨著摻燒煤泥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而底渣含碳量出現降低。
4)CFB鍋爐中投用煤泥后,鍋爐的排煙溫度升高,在300 MW負荷時,排煙溫度隨摻燒煤泥比例的增加而升高。為了實現大比例摻燒,需要強化尾部吹灰或適當調整尾部受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