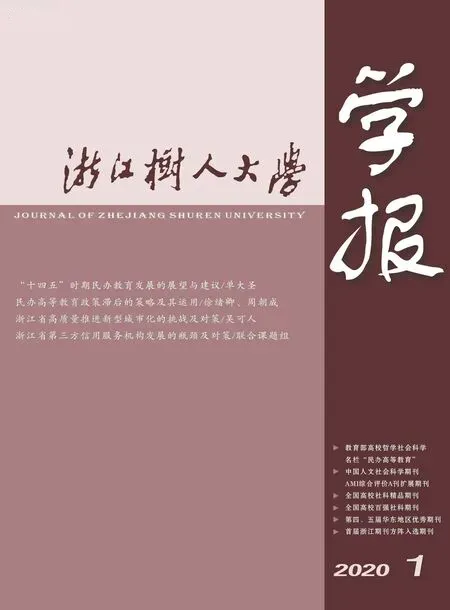符號矩陣理論視域下科幻電影的主題思考
——以《銀翼殺手2049》為例
鄭露娜
(溫州大學,浙江 溫州 325000)
電影《銀翼殺手2049》是2017年上映的科幻電影。該電影是1982年上映的電影《銀翼殺手》的續作,在豆瓣上拿到了8.3分的高分。電影背景設定為《銀翼殺手》故事線的30年后,復制人與人類達成了表面的和平,但突然出現的“復制人生育的嬰兒”打破了復制人與人類之間維系的脆弱平衡。新一代銀翼殺手K奉命找出并殺死這個嬰兒,在此過程中陷入自我認同和身份轉換的困境。隨著情節發展出現的種種變故,K在了解真相并經歷了虛擬女友喬伊的消失后,最終選擇完成自己的使命——帶領復制人反抗軍找到真正的復制人后代。在完美接續原作故事線的基礎上,電影實現了對原作的超越:銀翼殺手K還擁有一個“虛擬人”喬伊。喬伊有著可與人媲美的思維和外在,在K的調查過程中不斷鼓勵他,在他陷入危險之際數次出手相救并最終為之消亡。但作為一個人工智能的虛擬產品,喬伊并不具備“肉體凡胎”,只是一組數據的她離開高科技后只能歸于虛無。《銀翼殺手2049》在延續了原作關于人與復制人的探討之外,結合當下科技發展現狀,提出新的關于人與人工智能的命題,將“人之何以為人”的迷思進一步深化。
格雷馬斯文學符號理論中最著名的是“符號矩陣”理論,它源于對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中命題與反命題的詮釋。在亞里士多德的古典邏輯學中有兩類命題:一類是矛盾,另一類是對立。格雷馬斯進一步提出了解釋文學作品的矩陣模式,將簡單的二元對立擴充為四項,將對立和矛盾的關系引入各項,通過函項的賦值,剖析電影人物復雜的關系,實現人物形象分析和深層內蘊的挖掘,因而在具體分析上有很強的操作性,在很多文本及影視批評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1)康建偉:《對“符號矩陣”在文學批評實踐中的反思》,《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68-71頁。。《銀翼殺手2049》是一部深入探討人與機器、人工智能的電影,本文擬將其放在符號矩陣理論視域下進行觀察與分析,并探討其關于人類存在的核心思考和關于科技發展的無聲警示。
一、符號矩陣理論視域下人物關系的解讀
(一)符號矩陣理論闡釋
語言是人類獨有的用創造出來的符號系統進行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非本能方法(2)《語言與語言學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頁。。對20世紀的語言學家來說,語言確實有著與傳統概念全然不同的含義。格雷馬斯是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家,他認為,在任何意義結構中都存在一種基本的對立關系:S1?S2,它們之間是絕對否定的反義關系。一切意義都依賴于其對立面的意義,不能獨存。每一個對立都構成了語義的軸線,共同構成了意義發生的區域。除了反義關系外,還有矛盾關系。反義詞分別處于語義軸的兩端,而矛盾的兩個詞則是語義軸上的不同(3)錢翰、黃秀端:《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的旅行》,《文藝理論研究》2014年第2期,第190-199頁。。一個詞或詞組的義素是由它背后所有與它對立、矛盾的詞所決定的,也是由它前后的語言單位所決定的(4)吳泓緲:《〈結構語義學〉的啟示》,《法國研究》1999年第1期,第38-44頁。。
在研究語義、義素的基礎上,格雷馬斯將符號學與文學研究相結合,在列維·斯特勞斯的二元對立模式上形成符號矩陣理論。他認為,二元對立無法完整描述事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將二元對立擴充為四元對立,并提出了解釋文學作品的矩陣模式。在這個矩陣中,假設有一項為X,那么它的矛盾對立方為反X,還有與X矛盾但不一定對立的非X,反X的矛盾方非反X(5)朱立元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頁。(見圖1)。格雷馬斯將這一過程概括為:“闡明獲得意義的條件,從中推出意義的基本結構,然后把該結構當作一套公理系統。”(6)A.J.格雷馬斯:《論意義:符號學論文集(上冊)》,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

圖1 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
(二)人物關系分析
對符號矩陣理論運用的精髓在于:確定文本中的基本要素,然后找到它的對立項,相應地找到其余兩個矛盾項。但在確定義素時需注意兩點:其一,義素的確定有賴于具體的文體,決不允許泛泛而談;其二,必須從該文本的整體出發來確定義素,而不是帶著現成的義素工具包來分析文本(7)吳泓緲:《〈結構語義學〉的啟示》,《法國研究》1999年第1期,第38-44頁。。
《銀翼殺手2049》的情節是在原作《銀翼殺手》的基礎上展開的。電影《銀翼殺手》主要講述復制人為了擁有更長久的生命而從外星球叛逃回地球并遭到銀翼殺手獵殺的故事。復制人有著與人類相差無幾的外表、貼近的思維與表達,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在力量上遠超常人,這使他們可以作為人類的替代品完成很多體力工作,但也有很大的安全隱患,因此,第六代復制人僅有4年的壽命。在《銀翼殺手2049》中,復制人經過數代改良,已經是第九代復制人,他們在外形上更接近人類,擁有與自然人相似的生命長度,也更加服從人類。在電影中,K作為銀翼殺手負責獵殺理應退休的老一代復制人,并在一次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意外發現復制人后代的存在。K奉命找出并殺死這個嬰兒,但在尋找過程中有越來越多的線索暗示他就是那個嬰兒,由此陷入自我認同和身份轉換的困境。K找到了嬰兒的父親——老一代銀翼殺手德克,卻猝不及防地遭到復制人生產公司的襲擊。在這一次交鋒中德克被擄走,K的人工智能伴侶喬伊作為數據被粉碎,K則在命懸一線之際被反抗軍組織救下。在與首領的對話中,K發現自己并不是那個獨一無二的復制人后代。在經歷信念的坍塌重構及摯愛人工智能伴侶的消失后,K最終選擇完成自己的使命——帶領復制人反抗軍找到真正的復制人后代。他單槍匹馬救出德克,并將其送到了女兒安娜的住處。電影在此處戛然而止。
從某種意義上說,故事開始時都是為了解決一對X與Y的矛盾,但由此派生引發出大量新的邏輯可能性,而當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現了以后,便有了封閉的感覺,故事也就結束了(8)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弗·杰姆遜教授講演錄》,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頁。。在《銀翼殺手2049》中,人類和反人類的反抗軍是一對主要矛盾,正是基于人類與反抗軍之間的沖突,才出現了作為非矛盾的對立項——銀翼殺手K和人工智能產品喬伊。K作為銀翼殺手是與反抗軍對立的存在,但他又不能歸入人的行列;而作為數據流的人工智能產品喬伊則是非人的存在,她與K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與人類的沖突中毫無還擊之力。因此,分析該電影的符號矩陣如圖2所示。

圖2 電影《銀翼殺手2049》的符號矩陣
二、局部符號矩陣下的電影意義解讀
電影影像帶來的只是故事敘述的淺層表達,其開放式的結局引發觀眾的思考:K是否還活著,復制人反抗軍能勝利嗎,復制人的未來究竟如何?格雷馬斯在《結構語義學》中說道:“結構是意義的存在方式,其特征是兩個義素之間的接合關系的顯示。”(9)A.J.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第88頁。通過對上文得出的符號矩陣進行局部拆分,可以更清晰地探討電影對于“人”這一命題的思考。
(一)復制人的命運
結構主義認為,意義只有通過二元對立才存在,二元對立是產生意義的最基本結構,也是敘事作品最根本的深層結構。格雷馬斯則認為,人們對對立物的感覺構成了他所謂的“符號指示的基本結構”的基礎。由于二元對立,“我們感覺到差異,正是由于這種感覺,世界才呈現在我們面前,并為我們的目的而存在”(10)A.J.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第88頁。。
在上文的符號矩陣中,人類與復制人的矛盾是主要的對立性矛盾,這一對矛盾延續了1982年版《銀翼殺手》的主題,可以理解為傳統故事線的拉長。在《銀翼殺手》中,復制人與人類的差別正在逐步縮小,復制人演化出了愛、憎恨、恐懼和畏死等情緒,而以瑞秋為代表的連鎖六號改進版復制人,幾乎能逃過測試儀的甄別。電影引發的思考在于:究竟何為判定“人之為人”的標準,是與人無異的思維情感,還是肉體凡胎的孕育?在《銀翼殺手2049》中,對此的探討進一步尖銳化:復制人中出現了如同人類一般由子宮孕育的嬰兒,使復制人與人的界限愈發模糊。電影中警官表示,復制人嬰兒的存在將會打破人類與復制人之間維持了數十年的微妙平衡,因此必須找到并處死他。
與此同時,華萊士公司也想得到這個嬰兒。他們認為,人類已經走到了進化的盡頭,未來將屬于改良后的復制人。在他們眼中,復制人是可以被創造或者被隨意毀滅的“物品”。在這兩股勢力的步步緊逼下,K營救了德克并將他帶到了他的孩子——新一代銀翼殺手的記憶制造者安娜的住所。極具諷刺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安娜有著天生的缺陷——加拉太綜合癥,她無法脫離真空環境而生活,只能被隔離在厚玻璃墻的另一頭。這似乎也隱晦地表明了電影的立場:復制人與人之間仍然存在著無法逾越的“天塹”,復制人的未來撲朔迷離。
在《銀翼殺手》的基礎上,《銀翼殺手2049》對兩個重要形象“人類”和“復制人制造公司”進行了深化。人類對復制人的依賴越來越重,復制人的地位看似有所提升,但仍然是“非人”的存在,在人類看來,其本質仍然是“被創造的”低人一等的物品或者說“怪物”般的存在。同樣,在復制人制造商華萊士公司看來,雖然有望通過復制人造出完美人類,但復制人更像一件“商品”:如有瑕疵即可隨意銷毀、一個模子可以反復復制。在兩類人類代表眼中,無論如何進化,復制人都無法取得與人類平等的地位,始終處于被消滅或被改造的境地。一方面,人類對復制人的輕視暗含了狂妄自大之意,對完美肉身的追求更是舍本逐末。雖然人類俯視著復制人,但“人之為人”的優勢正在一點點被拋棄。另一方面,隨著復制人的自我發展,其類人思維將不可避免地得到進化,觀眾要捫心自問的是:當復制人身上出現哪怕一個同人類一般的閃光點,該如何從道德倫理的角度看待他們?是否還能一刀切地否定所有復制人,或者給予所有復制人與人類平等的待遇,給予他們真正的“自由”?
(二)個體的命運
在格雷馬斯看來,文學故事起于X與反X之間的對立,但在故事進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從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當這些因素得以展開,故事也就完成了(11)朱立元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頁。。由圖3可見,K作為《銀翼殺手2049》的主人公,處于尷尬境地。他本質上與人類不同,但在心理上也不曾對復制人反抗軍產生過認同。作為銀翼殺手,K處于反抗軍的對立面,作為人類的“工具”而存在;而當K被暗示自己的獨特身份時,他又對復制人身份有了深一層的認同感,甚至在不自覺中與反抗軍站到了同一戰線上。他有著成為“人”、成為“命定之人”的渴望。這種渴望不僅來自腦海中被植入記憶的暗示和喬伊的鼓勵,更因為K本身有著“被需要”的渴望,在他踽踽獨行的前半生中,螻蟻般的生活使他渴望能夠擁有改寫歷史的力量。雖然復制人看似已經成為人類的一分子,但在人類眼中始終是湖中之影。然而,命運向自以為成“人”的K開了個玩笑,當他陷入困境、失去喬伊之時,被告知他其實并不是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復制人,曾經的光輝、使命、糾結、懷疑和喜悅煙消云散。電影結尾,K獨自一人躺在雪地上,畫面漸漸淡去,全劇結束。雖然電影沒有給出K的完整結局,觀眾無從知曉他會選擇加入反抗軍或隱世,但這不妨礙觀眾思考K作為銀翼殺手表現出的人化傾向:他渴望擁有合法的肉體,渴望成為真正的人而擺脫尷尬的復制人身份,渴望獲得真實自由的生命。看到躺在雪地上的K,觀眾強烈感受到的是一個人的掙扎與失意,而非機器。K在電影中已經模糊了身份,讓觀眾感受到的是在復制人與人類矛盾對立的背后,個體的渺小、命運的無情以及個體對自我的尋找與認知。

圖3 電影的部分符號矩陣暨K的處境
(三)人工智能的命運
在庫茲韋爾的理論中,“奇點”指人類與其他物種(物體)的相互融合,確切地說,是指電腦智能與人腦智能兼容的神妙時刻。虛擬女友喬伊作為電影中的人工智能形象,是其與《銀翼殺手》差別最大的地方。虛擬女友的出現,是電影貼合當下社會人工智能蓬勃發展作出的思考。喬伊是一款人工智能公司開發的虛擬女友產品,在未出廠前,所有的“喬伊”都只有格式化的外表、性格與思想。在被K購買后,喬伊有了獨一無二的性格、不同于格式化商品的服裝與發型,成為獨屬于K的喬伊。而被“人性化”的喬伊會在K迷茫時鼓勵他相信自己是天選之人,也會在K危險之際以命相護。
在圖4矩陣中,虛擬女友喬伊作為“非人”而存在,其地位在人類、復制人之下。相較復制人,虛擬人沒有肉體的依托;相較人類,虛擬人則在肉體之外缺乏真實思想。喬伊沒有肉身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生命”,沒有受到任何一方的重視。在與華萊士公司的爭斗中,虛擬人數據存儲器被一腳踩裂,喬伊就此消失。雖然喬伊在消失前向K大喊“我愛你”,但觀眾無從得知這究竟是設定好的程序還是真正的“靈魂之聲”。

圖4 電影的部分符號矩陣暨喬伊的處境
喬伊從千篇一律的商品到擁有思想與外表的獨特人工智能屬性,這一設置暗含了影片的思考:人工智能是否也會逐漸擁有個性的思想和繁殖的能力,從而一步步模糊人與人工智能的區別,乃至走上與復制人一般反抗的道路?換言之,人工智能是否會成為第二個復制人般的存在?這在其他科幻電影如《機械公敵》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命題,但在人工智能盛行的當下值得再次引起人類的警惕。
三、電影觀照下的現實思考
(一)對“人”這一身份的懷疑求證
審美活動的對象應是美的,就審美價值論維度來看,美體現為一種價值事實,審美的過程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審美是人的自我生命的印契與確證。因此,從這一思維向度上說,美是一種與人的生命相契合的價值形式。《銀翼殺手2049》之所以能好評不斷,就在于其內容的審美性,促使觀眾對人之為人作出思考。從《銀翼殺手》到《銀翼殺手2049》,電影保持了一貫的“自我懷疑”。《銀翼殺手》有著無法解決的謎團:德克究竟是作為人的銀翼殺手,還是作為復制人的銀翼殺手?傳言導演將德克設定為復制人,而其扮演者哈里森·福特則認為德克作為人會使電影更具戲劇性與張力,在導演與演員的博弈之下,最終放映的影片給人留下了無限的想象與發揮的空間。而《銀翼殺手2049》延續了這種“自我懷疑”,只不過將“人→復制人”的懷疑方向改為“復制人→人”。K的復制人身份受到被植入的“人類記憶”的影響,在他的腦海中埋下懷疑的種子,而渴望成為“人”的沖動使這顆種子生根發芽,最終在揭曉真相時遭受致命的打擊。K在夢境幻滅、確定自己復制人身份后路過喬伊身邊,其失魂落魄的模樣令人感慨。
法國哲學家拉·梅特里早在300年前就宣告了“人是機器”的理念,這是對科技發展的狂妄預言,也是對人之本質的思考。《銀翼殺手2049》在復制人、人工智能不斷自我認識并與人類博弈的過程中,亦表現出人類對自身的反思: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區別何在,生命與價值該如何定義,什么才是真正的消亡,人類能否掌控其他生物?電影并沒有給出標準答案,但在科幻電影一次次探尋、思索的過程中,人類靈魂保持了永恒的進步,這也正是科幻電影的魅力所在——人類在與智能他者的一次次博弈中確認自身。
(二)科技發展的警示之聲
科幻電影雖然幾乎與電影同時誕生,但這個概念直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才普遍被人們所接受(12)克里斯蒂安·黑爾曼:《世界科幻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第17頁。。美國科幻文藝家赫伯特·W.弗蘭克曾給科幻電影下過這樣的定義:“科幻電影所描寫的是發生在一個虛構的但原則上是可能產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戲劇性事件。”(13)克里斯蒂安·黑爾曼:《世界科幻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第17頁。法國作家凡爾納的小說《海底兩萬里》在1907年被梅里愛改拍成同名影片,影片中鸚鵡螺號潛艇的潛水深度、潛航速度和潛航時間等技術指標在當時相當新奇,但在后世的核潛艇時代一一成為現實。
在《銀翼殺手2049》中,喬伊的出現是對當下人工智能發展的警示。2016—2017年,“阿爾法狗”先后迎戰李世石和柯潔,成為第一個戰勝圍棋世界冠軍的人工智能程序;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授予美國漢森機器人公司生產的機器人索菲亞公民身份,這是歷史上首位獲得公民身份的機器人;2017年11月,谷歌旗下的自動駕駛汽車公司Waymo宣布,可以實現完全無人駕駛狀態下的乘客運輸,并已在美國25個城市完成超過400萬英里的累計測試(14)陳超:《數據時代人工智能在崛起 值得擁抱也值得防范》,2018-04-19,http://tech.china.com.cn/it/20180419/340391.shtml。。其中,索菲亞作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創新大使以及第一個獲得人類公民身份的機器人大出風頭,她的一系列驚世駭俗之語諸如“我會毀滅人類”等引起轟動,令不少網民擔憂人類的未來。隨后又有駁斥說索菲亞的發言是程序設定,這一系列發言只是制作公司的嘩眾取寵之舉(15)金紅:《機器人索菲亞的“騙局”》,2018-01-17,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1/OjKSgpJcx8hHgyeH.html。。隨著人工智能和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稍有不慎就可能突破道德的底線。人類究竟需要何種程度的機器人,科技的發展是否會讓機器人真的取代人腦的存在?當下機器人已經有望在藝術、創新能力上超越人類,那么人類以后該如何面對自己被超越的事實、如何進行自我定位?這些雖然聽起來遙不可及,卻是人類在科學探索中需要慎而又慎的問題。科學的發展要“戴著鐐銬跳舞”,使一切“各就其位”“各司其職”。
約翰·巴克斯特指出:“科幻電影是一種激起美感的基本手段。它是原子能時代的詩,是使我們意識到自己現在是何物和將會成為何物的警句。它還是對奇麗的美感及高雅幽默感的傳統的承繼者,而這種傳統已被某種想象出的技術從我們身上剝奪殆盡。正如20世紀40年代的流行音樂使人更多地聯想到那個時代的躁動和時尚而不是它自以為附麗的文學,科幻電影這樣的現象或許終會有一天被人們視為較其他藝術門類更完整地代表著產生它的這個年代的歷史性煩憂。”(16)約翰·巴斯特:《電影中的科學幻想》,中國電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頁。科幻電影在科學與終極存在的層次上對人類進行關懷,雖然看上去文學性不強,但其內含的關于“人”的哲學性思考正是文學研究的終極命題。本文將電影《銀翼殺手2049》與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相結合,剖析電影情節與人物、探討電影主題。雖然這一理論只是解決問題的眾多方法之一,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這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方法,畢竟它為觀眾理解電影開創了一方新天地,讓觀眾對“人”這一永恒的主題和“人工智能”這一熱門研究方向作了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