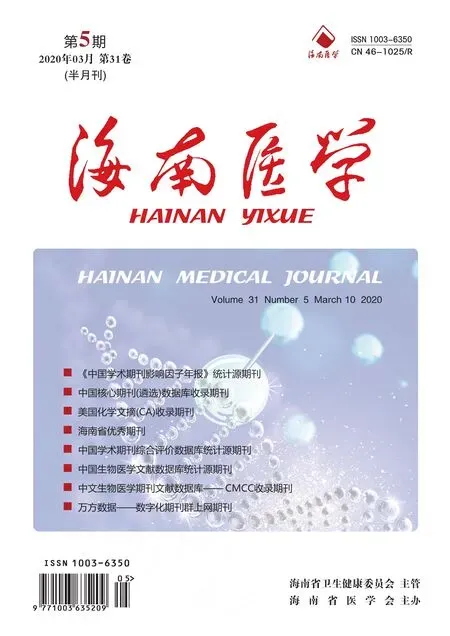兒茶酚抑素抑制血管鈣化的作用及機制
樊小容,譚小青,張旭升,黃戰軍,蔡博治
1.深圳市龍崗區人民醫院心血管內科,廣東 深圳 518172;
2.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分子心臟病學實驗室,廣東 汕頭 515041
血管鈣化為過量鈣鹽沉積于血管壁,是主動的、多因素調節的過程[1],多種活性因子參與調控血管鈣化的發生發展。血管鈣化作為導致臨床心血管事件的重要危險因素已成為共識,防治血管鈣化顯得特別重要,因此,尋求新的活性因子不僅可作為血管鈣化機制的重要補充,也為防治血管鈣化提供新的策略。兒茶酚抑素 (catestatin,CST) 是由腎上腺嗜鉻細胞產生的嗜鉻顆粒蛋白A,由21個氨基酸組成的多肽結構,通過抑制交感腎上腺系統兒茶酚胺的釋放,可調節心血管系統作用如舒張血管、調節血壓及心肌收縮力等[2],然而對血管鈣化的影響尚未見國內外學者報道,因此,本實驗將探討CST 對大鼠血管鈣化的作用以及可能相關機制。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和相關試劑來源 SD大鼠24只,雄性,8周齡,購自北京維通利華實驗動物技術有限公司。CST購自Tocris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維生素D3由Sigma公司生產,尼古丁由Merck公司生產;鈣離子測試盒和ALP試劑盒購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MCP-1試劑盒和TNF-α試劑盒購自北京華英生物研究所。
1.2 動物模型的制備與取材 按隨機數表法將24 只雄性SD 大鼠分為正常組、鈣化組和鈣化+CST組,每組8 只。正常組大鼠在造模當天予生理鹽水肌注和花生油灌胃處理;鈣化組大鼠在實驗當天予維生素D3(300 000 U/Kg 在大腿肌肉注射1 次) ,并用尼古丁灌胃 (25 mg/kg,早晚各1次) ;鈣化+CST組大鼠在造模后第二天開始用CST 2 nmol/ (kg·d) 腹腔內注射。然后三組大鼠常規飼養4周,麻醉后取材,分離主動脈組織,其中一部分組織多聚甲醛固定后制作蠟塊,其余組織錫紙包裹并標記,-80℃儲存。低溫離心分離血清,-80℃保存。
1.3 Von Kossa染色 取大鼠胸主動脈做石蠟切片,1%硝酸銀溶液浸泡,紫外線照射后,5%硫代硫酸鈉溶液浸泡,堿性品紅染色。
1.4 ALP 活性及鈣離子含量測定 將大鼠主動脈組織剪碎并勻漿后,取上清檢測,用甲基百里香酚藍比色法檢測鈣離子含量,用磷酸苯二鈉法檢測ALP活性,詳細步驟見試劑盒說明書。
1.5 血清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 (MCP-1) 、腫瘤壞死因子-α (TNF-α) 含量測定 采用放射免疫法檢測大鼠血清MCP-1和TNF-α含量,具體步驟詳見試劑盒說明書。
1.6 統計學方法 應用Graph Pad Prism 4 統計軟件分析數據,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多組間比較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q 檢驗,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三組大鼠的血管鈣化指標比較 與正常組大鼠比較,鈣化組大鼠主動脈中膜可見較多黑色顆粒表達 (Von Kossa 染色) ,提示鈣鹽沉積明顯,用CST 干預后,主動脈組織鈣鹽沉積明顯減少,見圖1。與此同時,鈣化組大鼠主動脈組織的鈣離子含量及ALP活性明顯升高,與正常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 ;經CST干預后,鈣化+CST組大鼠的鈣離子含量及ALP活性較鈣化組明顯減輕,與鈣化組大鼠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 ,見表1。

圖1 大鼠主動脈Von Kossa染色,黑色顆粒為鈣鹽沉積 (×100)
表1 三組大鼠主動脈組織鈣含量與ALP活性比較

表1 三組大鼠主動脈組織鈣含量與ALP活性比較
注:與正常組比較,aP<0.05;與鈣化組比較,bP<0.05。
組別正常組鈣化組鈣化+CST組F值P值只數8 8 8鈣含量 (mmol/g蛋白) 0.38±0.13 0.94±0.11a 0.78±0.09ab 108.46<0.05 ALP活性 (U/g蛋白) 112.82±13.52 217.50±14.43a 179.88±12.75ab 217.84<0.05
2.2 三組大鼠血清MCP-1和TNF-α濃度比較 鈣化組大鼠血清MCP-1 和TNF-α濃度明顯高于正常組大鼠,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 ,經CST 干預后,鈣化+CST 組大鼠的血清MCP-1 和TNF-α濃度較鈣化組大鼠明顯下降,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 (P<0.05) ,見表2。
表2 三組大鼠的血清MCP-1和TNF-α濃度比較

表2 三組大鼠的血清MCP-1和TNF-α濃度比較
注:與正常組比較,aP<0.05;與鈣化組比較,bP<0.05。
組別正常組鈣化組鈣化+CST組F值P值只數8 8 8 MCP-1 (pg/mL) 65.55±2.35 93.75±3.15a 79.13±2.23ab 512.20<0.05 TNF-α (ng/mL) 0.91±0.05 1.42±0.09a 1.22±0.07ab 233.85<0.05
3 討論
血管鈣化與骨組織的骨化過程類似,細胞表型轉化是關鍵 (由收縮型血管平滑肌細胞轉變為成骨細胞型) ,同時合并局部骨相關蛋白和活性因子分泌增多,ALP 活性升高,促進鈣鹽沉積;促進鈣化因子與抑制鈣化因子在血管鈣化的發展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調節作用。研究已證實,在病理情況下如氧化應激、高血壓、高血糖、高脂血癥、高尿酸血癥以及炎癥反應等可導致血管損傷,一些活性因子作為促鈣化因子協同促進血管鈣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一些活性因子如Ghrelin作為血管鈣化抑制因子可保護血管功能,從而減輕血管鈣化。其過程可能涉及多條信號通道包括TGF-β/BMPs/Smad 通路和MAPK 通路等[3-6]。本課題組的前期研究發現尿酸、醛固酮、salusin β和部分炎癥因子 (IL-6、MCP-1、CRP) 等活性因子的表達促進血管鈣化過程[3,7-9]。LARIVIèRE等[10]也在慢性腎臟病大鼠模型觀察到,隨著血管平滑肌細胞分化為成骨樣細胞,不僅骨信號分子BMP-25 和骨鈣素表達增加,IL-6、TNF-α 等炎癥因子的表達也同步明顯增加。其他文獻也證實單核/巨噬細胞分泌的TNF-α、IL-6等炎癥因子可誘導血管平滑肌細胞向成骨樣表型轉化,導致血管鈣化的發生與發展[11]。以上研究均表明炎癥因子在血管鈣化的發生與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除此,近來研究證實內質網應激和自噬的交互作用可影響血管鈣化的發展,實驗發現用內質網應激激動劑衣霉素和自噬抑制劑3-甲基腺嘌呤干預,血管鈣化程度均有加重[12]。而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抑制鈣化因子在血管鈣化中同樣起著重要作用:胎球蛋白A及焦磷酸鹽可通過抑制磷酸鈣的形成和沉積來抑制血管鈣化[13]。APE1/Ref-1可通過氧化還原來抑制成骨細胞分化和減少氧化應激,對磷酸鹽誘導的血管鈣化起抑制作用[14]。
CST是一種新的內源性多肽,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關注。臨床研究表明CST不僅可作為原發性高血壓、心力衰竭患者的血清標志物,而且在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中還可預測病情的嚴重程度[15-17]。最新的研究表明CST 可通過抑制炎癥反應從而發揮血管保護作用。在糖尿病、結腸炎和動脈粥樣硬化小鼠模型中,CST可減少免疫細胞在受累組織中的浸潤,體內外實驗均證實其能將巨噬細胞的分化從促炎表型轉化為抗炎表型,從而有效發揮抑制炎癥作用[18]。在一項對冠心病患者血清CST 濃度與動脈粥樣硬化程度的相關性的研究中,與健康受試者相比,冠心病患者中血清CST濃度明顯降低,且與疾病嚴重程度呈負相關[19]。對于CST作用的信號傳導通路也有進一步的研究證實,EISSA 等[20]在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發現CST 的蛋白和mRNA表達水平明顯下降,應用CST治療可以使IL-8表達下調,用STAT-3 阻斷劑可以阻斷CST 的治療效應,從而推測CST 可能通過STAT-3 依賴途徑而發揮調節炎癥反應的作用;國內學者在間歇低氧高血壓大鼠實驗中發現,CST可以減輕間歇低氧導致大鼠高血壓的效應,并且可使主動脈組織胞漿中核因子E2相關因子2 (Nrf2) 蛋白表達顯著下調,而胞核中Nrf2 蛋白表達明顯上調,推測CST 可能與通過Nrf2-ARE 信號通路作用有關[21]。
本研究結果顯示,應用維生素D3聯合尼古丁成功誘導血管鈣化動物模型,觀察到大鼠主動脈鈣鹽明顯沉積,主動脈組織中鈣含量增加,ALP 活性上調。各試驗組中炎癥指標 (MCP-1、TNF-α) 明顯高于正常組,與國內外學者實驗結果一致,再次證實炎癥因子與血管鈣化密切相關。經CST干預后,血管鈣化的程度明顯改善,且大鼠血清炎癥因子MCP-1、TNF-α表達明顯低于鈣化組,提示CST可能通過抑制炎癥因子表達改善血管鈣化的程度,從而發揮血管保護作用,但是否通過其他機制作用尚不清楚 (如抑制其他促鈣化因子的協同作用) 。
綜上所述,兒茶酚抑素能抑制血管鈣化的進程,可作為臨床防治血管鈣化新的作用靶點,然而可能涉及的信號通路需進一步研究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