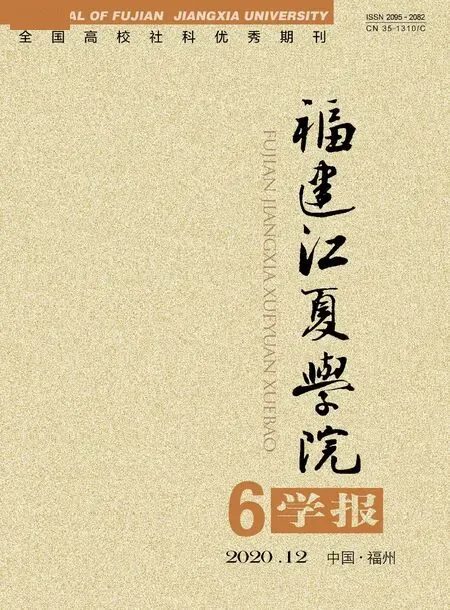“荒誕世界”與“反抗哲學”
——敘事視角下解析加繆的《鼠疫》
鄭美香
(福建江夏學院外國語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法國存在主義大師阿爾貝·加繆于1947年創作《鼠疫》,小說描寫了北非阿赫蘭市發生一場鼠疫被封隔后的情形,通過瘟疫持續9個月間里厄、塔魯等居民的所作所為,表達了他關于人類在荒誕世界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真諦的思考和理解。近年來國內外研究《鼠疫》的論文不斷出現,其中不乏從敘事學角度去分析讀解的文章,如國外的埃德溫·摩西的《結構的復雜性:〈鼠疫〉的敘事技巧》(Functional complexity: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the Plague,1974)以及波特·勞倫斯的《從編年體到小說:加繆〈鼠疫〉的藝術構造》(From the Chronicle to Novel:Artistic Elaboration in Camus'LaPeste,1982)等,主要從敘事形式和結構方面去研究《鼠疫》的文本內容①轉引自謝魏學位論文《加繆〈鼠疫〉的瘟疫敘事研究》,浙江師范大學,2016年,第5頁。;國內主要有:安霖從敘事技巧的運用和功能來分析小說的主題和風格[1];李煒從敘事者、敘事聲音、敘事視角和敘事時間等方面研究小說文本的內容和藝術功用[2];楊曉敏通過零聚焦敘事、外聚焦敘事、內聚焦敘事三方面解讀小說文本內容②楊曉敏《〈鼠疫〉中的多重敘事聚焦》,福建省外國語文學會《2008年年會論文集》,第467頁。;謝魏從小說題材和敘事內容等方面分析小說中雜糅著偵探小說、多重敘事聲音、互文本等后現代小說的特點[3]。
國內外這些研究論文多數從宏觀視野對《鼠疫》的敘事策略和功能進行探討。本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擬深入解讀文本,具體研究《鼠疫》獨特的敘事視點、敘事風格及敘事功能,首次提出加繆在小說中設置三組獨具特色的敘事視點——嵌套式+“鏡中人”+雙視點人物敘事,進而分析小說獨特的主題內涵、藝術張力和敘事風格。加繆構建的三組敘事視點形象展現了“荒誕世界”與“反抗哲學”,對小說主題建構、人物關系、情節鋪展、敘事風格等具有重大意義,也賦予小說深廣的歷史文化內涵和雋永的藝術魅力。
一、雙視點人物互動敘事記錄瘟疫事件
加繆在《鼠疫》中設置了里厄與塔魯兩個視點人物,講述一個由鼠疫引發人類行動的故事,構建了“囚徒們”和“覺醒者”之間的張力,形成紀實小說的風格。
加繆一再強調《鼠疫》的紀實風格,指出這部小說類似新聞報道,具有客觀敘述的性質,他甚至以“紀事”來稱呼這部小說。小說選擇里厄和塔魯這兩個視點人物第三人稱內部聚焦來敘事。里厄作為醫生堅守疫情一線治病救人,是這場持續九個月鼠疫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醫生這一身份確保他對這場瘟疫見識客觀、科學、精準。與此同時,為了更加全面客觀地敘述這場給阿赫蘭市千千萬萬居民帶來重大影響的鼠疫事件,加繆又設置社會活動家塔魯記錄的瑣事細節予以補充印證。小說以一種不夾雜個人情感的視角,來講述一個由鼠疫引發人類行動的故事,展現小說的荒誕世界與人類反抗,使《鼠疫》成為一部紀事體小說。通過雙視點人物互動敘事,小說以見證人眼光切入這場疫情,全面客觀地記錄鼠疫肆虐下的荒誕世界。“作為忠實的證人,他必須首先記錄的是人的行為,有關的資料和傳聞。”[4]227-228小說的敘事客觀而冷靜,而選擇第三人稱內部聚焦寫作,則有助于敘述人與其他人物保持某種距離,保持客觀性和全景視角。在以里厄和塔魯展開的敘事中,始終采用“客觀”“冷靜”“不帶感情色彩”的零度敘事,形成了紀實小說的風格。
選擇雙視點人物第三人稱內部聚焦來講述瘟疫事件,與之對應的小說藝術張力也隨之架構起來。加繆在1942年8月的《手記》中提到:“小說。不要把‘鼠疫’放進標題中。而是諸如‘囚徒們’之類的。”[5]這里“囚徒們”是指被隔離在阿赫蘭市惶恐無助的眾多居民。小說以里厄和塔魯作為雙視點人物,描寫他們和格朗、朗貝爾、帕納盧等“囚徒們”的所作所為,記錄他們以各自的方式走出荒誕的狀態,從恐慌無助的“囚徒們”變成攜手而戰的“覺醒者”。這里“覺醒者”是具有群體性抵抗精神的人,小說講述一場瘟疫引發人類反抗的故事,以“零度聚焦”來宏觀展現由鼠疫引發的人類行動,展現不同身份、觀點迥異的人們在荒誕世界中走向覺醒和集體抗爭之路。通過雙視點人物敘事,小說展現眾多人物面對瘟疫的不同態度以及走向“反抗”的不同方式,小說一系列主題依托各具特色的人物一一展開。
在小說《局外人》中,加繆著力表現“荒誕世界”的真相,筆下的人物都是“囚徒們”,而在后來《鼠疫》《反抗者》等作品中,出現了“覺醒者”和“反抗者”形象。在《鼠疫》中,里厄只想做一個盡職的醫生投身于與鼠疫的抗爭中,不信上帝的塔魯為了內心安寧組織志愿隊抗“疫”,格朗作為政府人員每天統計疫情死亡人數,記者朗貝爾從局外人變成覺醒者留下來“和大家有難同當”[4]156,神父帕納盧目睹奧通幼子被病痛折磨致死后,認為“上帝逼得我們走投無路”[4]168,里厄的母親“能看透包括鼠疫在內的任何事物的本質”[4]208,患哮喘病數鷹嘴豆的老人說“鼠疫就是生活”[4]232,認為自己“一直是一個鼠疫患者”[4]189的塔魯堅持抗疫,科塔爾在瘟疫消退后變成瘋子……當鼠疫來臨,人們掙扎著抵御瘟疫的奴役,小說通過眾多人物表達出人類對瘟疫的反抗態度,而對瘟疫持歡迎態度代表荒誕的科塔爾的行動則是一個反例。小說眾多人物體現了有血有肉的真實,正是荒誕引起的分離與反抗,形成了“囚徒們”和“覺醒者”之間的巨大張力。
加繆在《鼠疫》中多次交代小說類似新聞報道,這一構思是通過雙視點人物敘事得以實現,小說的整個故事線沒有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更像是一部寫實的報告文學,形成了紀實小說的特點。加繆強調,《鼠疫》描寫的眾多人物“直面同一荒誕時諸多個人觀點的深度對等”,他講述一座被隔絕城市里的故事,描寫掙扎在疫情一線的人們的所作所為,各個人物觀點呈現不同觀念的沖突與交融。他通過雙視點人物敘事,寫出眾多人物從“囚徒們”走向“覺醒者”的轉變歷程。其中,視點人物里厄和塔魯代表著加繆的一部分觀點。加繆曾說過:“最接近我的,不是圣人塔魯,而是醫生里厄。”[6]他在1957年的受獎演說中,指出“作家只有忠心耿耿竭盡所能地為真理和自由服務,他的職業才能因此變得偉大。”[7]163-164福克納在給加繆的悼文中寫道:“加繆說過,誕生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上的人唯一真正的職責是活下去,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7]154-155在小說中,加繆通過雙視點人物講述一個由鼠疫引發人類行動的故事,寫出眾多人物從荒誕中覺醒,在反抗中尋找生命存在的意義。
二、“鏡中人”互文敘事講述寓言故事
加繆在小說中設置了“鏡中人”互文敘事,講述了一個充滿感情與思考的寓言故事,構建了“冰山風格”和“生命激情”之間的張力,形成了寓言小說的風格。
加繆在小說中設置一面“鏡子”,“雙重敘事人”身份的里厄作為“鏡中人”互文敘事,通過“自畫像”來審視自我。開篇引出超敘事“筆者”,而主敘事則以里厄醫生為視點人物,作品結尾透露“筆者”原來就是里厄,超敘事“筆者”時時對主敘事里厄“照鏡子”,進行自我觀照、反省和思考,作為敘事人里厄與人物形象里厄之間的界限消融了。加繆說過:“反抗,即時時刻刻都質疑世界……反抗,就是人時時刻刻面對自身。”[8]63他在小說中設置“鏡中人”互文敘事,通過里厄“時時刻刻面對自身、時時刻刻質疑世界”來講述一個令人深省的寓言故事,提醒讀者小說的醒世意味。
警示作品堪稱法國文學的一大特色,加繆創作《鼠疫》的初衷是取得某種歷史性的警示效果。《鼠疫》的核心意義不是描述鼠疫事件本身,小說中講述的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類故事,加繆通過“鏡中人”互文敘事,構建一類關于人與災難、荒誕抗爭的寓言故事,從而豐富了小說的主題,《鼠疫》也成為一部警示小說。《鼠疫》卷首題詞引用笛福的一句話寄寓小說意旨:“用另一種囚禁狀況表現某種囚禁狀況,猶如用某種不存在的事物表現任何真實存在的事物,都同樣合情合理。”加繆以冷靜客觀的態度介入小說敘事,“筆者”里厄充當忠實的記錄者身份,視點人物里厄作為親歷者和見證人,通過“鏡中人”互文敘事去思考“如何為自己畫好像”。
《鼠疫》在表層上是記錄一場關于鼠疫的故事,而更深的表意層次上,這一故事隱含著一個令人回味、發人深思的寓言。加繆通過雙重敘事人里厄,不斷回顧、反省“鏡中人”,使小說成為反思人性意識的心靈獨白。正是通過真誠的反省,里厄找到了人性的弱點與光輝,激發了生命的激情,實現了自我救贖。加繆通過講述這個充滿感情和思考的寓言故事,提醒讀者不要忘記曾經發生的災難。
在小說中,加繆所講述的寓言故事包含著豐富的象征含義與隱喻色彩,隱含著人類的處境、內在的沖突以及人性的問題,他使用法國后現代主義理論家羅蘭·巴爾特“零度寫作”的敘述手法,即中性的、非感情化的寫作,排斥主觀情緒和感情的敘述調子,這一點與海明威“冰山風格”很相似。同時,加繆存在主義哲學的內核是生命的激情,這種激情是要熱愛生命,在對荒誕的反抗中尋求生命的意義。通過里厄“鏡中人”互文敘事,加繆將客觀的描述、主觀的情感貫穿在整篇小說中,講述一個充滿思考與感情的寓言故事。“冰山風格”和“生命激情”形成巨大張力,使讀者內心深為震撼,進而去思考和領會小說的警示意味。鼠疫象征的是人類面對的生存困境,它們潛伏在人類身邊,隨時有可能爆發,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面對生存困境,加繆尋求解答“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他的答案是要用愛的力量去戰勝苦難。
在小說中,加繆通過“鏡中人”互文敘事寫到三個人的死,就充分彰顯了“冰山風格”和“生命激情”之間的張力。首先,客觀地描述守門人的死,門房是阿赫蘭市第一例鼠疫感染死亡病例,象征著鼠疫攻入“城門”,主敘事的里厄見證了門衛之死,而作為超敘事的里厄則思考瘟疫發生的危機。其次,客觀詳實地描寫預審法官奧東的兒子之死,敘事人記述了孩子整個死亡過程的每個細節,描述了里厄、塔魯、格朗、朗貝爾、帕納魯神父的神情與態度,尤其是為后來神父滿懷悲憫之心改變態度投身于抵抗鼠疫的行動埋下伏筆。再次,“儀式般”描寫塔魯在鼠疫悄然退去之前死去,里厄聆聽他臨終前的自述式演講,目睹這個自稱小鼠疫患者的“圣人”死去,超敘事的里厄借數鷹嘴豆老頭之口說“最優秀的總活不長”[4]231,彰顯了寓言小說的意味。小說描寫這三個人的死亡極具象征意味,面對死亡威脅,作者敘述三類人:死了的人、瘋了的人(科塔爾在鼠疫末期發了瘋)、活著的人。在瘟疫無情的荒誕世界中表達“死亡”意識時,加繆通過里厄這個“鏡中人”互文敘事,引發人們思考一個人類永恒主題:面對生命的苦難特別是死亡時,人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與狀態去生存,警醒人們要從災難中記住什么。對于過去了的這場災難,加繆通過“鏡中人”互文敘事,把瘟疫故事作為一個寓言小說寫下來,他并不是為了記錄人類戰勝瘟疫,而是要人們在共同的困境下用愛去抗爭,因為“知道人的內心里值得贊賞的東西總歸比應該唾棄的東西多”[4]233。
三、嵌套式敘事展開深刻哲思
在小說中,加繆精心設置了嵌套式敘事,展開了一場面對人類災難圖景的存在主義哲思,構建了“歷史敘述”和“文學虛構”之間的張力,形成哲理小說的風格。
嵌套式敘事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敘事視點層層相套的方式敘事,現代小說常常采用這種敘事方式。熱奈特在《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對敘事層進行區分,指出敘事者有時會再造出觀察者,將“說的人”和“看的人”分為幾個敘事層。[9]加繆在《鼠疫》中將三個敘事層的敘事視點層層相套:一是“超敘事”,敘述故事前添加序言,引出“筆者”即“說的人”,說明故事的來源,使敘事人獲得全知全能敘述的權利,這是小說最大層的敘事套;二是“主敘事”,里厄醫生作為“看的人”,讓這個瘟疫事件的親歷人講述其所見、所聞、所感,呈現有限視角的敘事,這是小說第二層敘事套;三是“次敘事”,小說在里厄的敘事中又造出塔魯這個“看的人”,主敘事不斷引用塔魯的記錄本作為鼠疫事件的補充見證,塔魯這一人物視點形成小說第三層敘事套。以上三個視點一層套一層,形成超敘事、主敘事、次敘事等三個敘事套,視點層層相套完成小說敘事。
加繆認為“想成為哲學家就寫小說”,他繼承伏爾泰哲理小說的傳統,通過《鼠疫》這篇虛構的小說來表現其哲學思想,創作一部哲理小說。他設置的嵌套式敘事視角除了承擔講述故事、表達情感、塑造人物形象之外,還展開一場面對人類災難圖景的存在主義哲思。加繆主張用形象而非用推理寫作,認為“偉大的小說家是哲理小說家”[8]117,他在《鼠疫》通過嵌套式敘事層層相套展開小說文本,把相關的視點人物當作某種思想、某種品格的物質承擔者,在小說中表達某種哲理,從而把小說打造成形象化的哲學。
小說的虛構性往往需要我們對虛構者的真實意圖有所了解和理解,加繆深受存在主義影響,他稱自己的思想為“荒誕哲學”,在《鼠疫》采用三個層級的敘事套子進行嵌套式敘事,一方面,小說突出編年體的史詩化寫作方式,以歷史學家“見證”敘述的視角,使得《鼠疫》成為一部歷史敘事小說;另一方面,這場瘟疫明顯是“不存在的事”,小說采取一種不夾雜個人情感的敘事視角來敘述,其真實感來源于文學虛構。加繆采用超敘事(筆者)、主敘事(里厄)、次敘事(塔魯)等三個層次的敘事視角,整合了編年史的歷史敘事和文學的藝術虛構敘事,表現為以故事來建構“歷史”,通過小說書寫“歷史”,再經由文學藝術的加工,借助史詩般的情感敘述,賦予一場瘟疫超脫于生活真實的震撼力。
憑著對歷史敘事和文學虛構的獨特理解,加繆在小說中設置這一組嵌套式敘事,形象地展現他面對人類災難圖景的獨特思考與理解,傳達其存在主義哲學觀和世界觀。他并不要求讀者相信鼠疫是真實的歷史事件,而是營造一種歷史真實感,在讀者內心認同鼠疫事件真實可信。加繆從表現存在主義哲思出發,在小說中采用嵌套式敘事,通過虛構的“歷史”藝術地反映真實的現實生活,進而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不要簡單地把小說當成一部虛構故事或者記錄歷史的編年史來讀,而要通過小說對現實生活進行思考,要穿過小說的虛構透視荒誕世界和現實人生,去追問生命的真諦。
總之,加繆在《鼠疫》中成功運用嵌套式+“鏡中人”+雙視點人物的敘事視點,通過小說敘事構建一系列藝術張力,展現豐富的情節內容,表達多層次的主題內涵,寄寓深刻的存在主義哲學思考,營造小說龐大的精神世界,形成了融紀實、寓言、哲理于一爐的多樣化風格。這一套“組合拳”的敘事功能是放射性的,收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藝術效果。加繆從《局外人》到《鼠疫》《反抗者》的創作變化,展現出他著力思考、闡釋的哲學對象及其論述的哲學體系由“荒誕”走向“反抗”的流變過程,構建起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及體系。也正是注入“反抗哲學”,形成加繆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鮮明特色,“他成為二戰后歐洲乃至全世界幾代青年的‘精神導師’”[7]扉頁。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對加繆作出這樣的評價:“他(加繆)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7]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