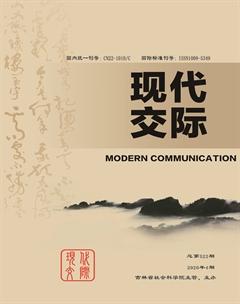關于譯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創新問題的思考
孫菲菲
摘要: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走出去”的過程中,依靠官方力量譯介作品的做法,忽視了國外讀者的閱讀喜好和習慣,不符合科學規律。要切實有效地推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需要當代的中國作家了解西方的寫作方式,譯作內容符合海外讀者的閱讀喜好,借助海外出版社成熟的市場運作方式推介作品。基于此,從三方面圍繞譯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創新問題展開思考,以助力中國文學“走出去”。
關鍵詞:譯介 作家 譯作 出版社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20)04-0070-02
我國譯介學的創始人謝天振教授認為,“翻譯文學是一種獨立的存在,在人類的文化生活中發揮著原作難以代替的作用”[1]。翻譯文學“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1]。中國文學“走出去”,作家、譯作和出版社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一是作家要具備雄厚的寫作能力;二是譯作能被海外讀者接受和喜歡;三是出版社有在海外市場推介作品的能力。
一、作家實力
作家余華、蘇童、莫言的小說《活著》《妻妾成群》和《紅高粱》等被改編成電影并在海外放映取得一定反響之后,原著小說也引起了海外讀者和出版社的關注,這便說明了海外文學市場對中國當代作家寫作實力的肯定。
更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一些青年作家直接嘗試英語寫作,這一方面是客觀因素使然,如青年作家謝宏在國外文學雜志成功投稿之后,就是礙于譯者工作時間、文學雜志讀者有限等客觀因素,所以開始嘗試用英文寫作。2018年4月,他的英文長篇小說Mas Town已由Whyte Tracks Publishing出版社發行。“85后”作家錢佳楠,她在2016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工作坊參與了創意寫作項目,學習用英語寫作,如今作為美國獨立文學網站The Millions的特約作者已出版多部短篇集、長篇小說和譯作。作家謝宏和錢佳楠的親身經歷說明,青年作家可以通過提高自身英語水平,和世界讀者展開更直接的溝通。
二、譯作在海外的接受度
在世界語言中,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是大語種,而漢語盡管使用人數不少,但畢竟使用國家只有一個,所以也只能算是小語種。作為小語種的中文文學作品要在保持特色的同時能被更廣泛的讀者所接受,這便要求譯作要國際化。換言之,譯介效果取決于讀者,即為誰而譯,不能以“信達雅”的標準固步自封,要考慮目標語讀者的閱讀感受。同是翻譯《紅樓夢》,楊憲益、戴乃迭和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的譯本就形成了鮮明對比,從美國大學圖書館的借閱率可以看出,霍克斯版本更受歡迎。所以譯者即便提供了完全忠于原文的譯作,但其譯本不符合目標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情趣,在國外圖書市場上無人問津,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而言,這部譯作就是失敗的。過于強調對原作的忠實度的這種認識和國內翻譯界長期以來一貫忽視翻譯規范和普遍性,片面強調“中國特色”不無關系,反而有“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泥坑”的危險[2]。
“紙托邦”的創始人艾瑞克·阿布漢森(Eric Abrahamsen)在訪問中也曾表示,很多中國作家語言表達往往比較啰嗦,喜歡煽情,代替讀者作價值觀判斷,而這些都是西方讀者難以接受的。西方的文學傳統強調“Keep it short;less is more.”讀者閱讀時側重的是作品的沖突和張力,再以簡潔有力、有節奏感的英語語言表達來展現沖突。這些都需要中國文學作品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考慮西方讀者的閱讀喜好,適當改寫。
三、作品“走出去”的渠道
渠道狹窄是當前制約中國文學作品傳播的巨大障礙之一。以青年作家謝宏為例,由于對國外文學作品發表的渠道缺乏了解,所以他只得自己把譯作投給國外知名文學雜志。相比這種小眾的做法,目前國家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給予資助。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走出去”的渠道主要包含以下三種:一是通過國內出版社的海外分社出版;二是直接由國內出版社出版譯作;三是由國外出版社出版。
由于海外讀者不了解中文出版機構,一般不會隨意購買海外分社甚至是中文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英文書,所以前兩種渠道的效果較差,實際上更多地選擇與知名的英語發行機構合作。這些機構往往歷史悠久,了解當下英語讀者的閱讀品位和出版市場運作方式,從而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銷售策略,保證宣傳力度和效果。
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國外出版商和發行商便開始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在這股浪潮中,他們首先關注的是已經在國內積累了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作家麥家就坦承相繼被美國FSG出版公司、英國企鵝出版集團、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團三家世界出版巨頭看中。2019年,其合作方英國企鵝出版集團更是把《解密》《風聲》列入“企鵝經典文庫”,并作為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送到了女王的書架上。在2019年的倫敦書展上,作家麥家的三部小說《解密》《暗算》《風聲》售出的版權已至33個語種。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更是在兩個月內先后9次介紹了他本人及其作品;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更是對他進行了封面報 道,并將小說《解密》評為“全球年度十佳小說”。麥家的作品近年來在海外熱銷,正是借助于企鵝集團的成熟運作方式,帶動其他重要媒體作出相關報道,令作家的知名度大增,形成了宣傳推廣的良性循環。
青年作家謝宏的首部英文作品即便是和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Whyte Tracks Publishing合作,但在全球的實體和網上書店都可以購買到這本英文版小說,甚至還登上了亞馬遜美國、英國的暢銷書排行榜,更有World Literature Today、South Morning Post等媒體在互聯網上推介。這些事實都證明,即便是國外小型出版社,其運作和發行都遠比通過國內渠道效果理想。
以作家劉慈欣為例,2019年電影《流浪星球》上映之后,更是引起了國內外讀者對其系列小說的熱議。目前《三體》在美國的銷量已經接近百萬,在英國的銷量也近50萬冊。除去紙質書,也有相當部分海外讀者是通過“紙托邦”這樣的網絡平臺了解中國文學。“紙托邦”更是積極投入幫助中國出版方策劃、執行書籍推廣方案的工作中。可見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數字化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文學譯介出版要與影視作品、網絡平臺等其他媒介積極互動,通過互補和協調出版模式,開拓傳播渠道,助力中國文學“走出去”。
不容忽視的是,同屬小語種的拉美文學如今在世界文壇上爆炸式發展,這離不開著名文學經紀人卡門·巴爾塞斯(Carmen Balcells)的功勞。包括《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在內的眾多西班牙語作者都是經由她推向歐洲和北美的。反觀國內,目前還沒有成規模的文學經紀公司或者經紀人為作者代理出版的相關事務。
四、結語
回顧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歷程,就不免提到《中國文學》雜志和“熊貓叢書”這些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失敗案例。自1951年創刊以來,《中國文學》雜志先后發行過英文版、法文版,從年刊改為季刊、雙月刊、月刊;隨后又大手筆地以效法英國“企鵝叢書”的方式出版了“熊貓叢書”,但這種自行組織寫作、翻譯、推銷的強硬推介方式最終在國外遇冷,難逃停止出版的命運。文化譯介的規律是弱勢文化主動引入強勢文化。我國各類政府機構多年來組織的中國文學推介活動,實際上是把在世界文壇上還沒有處于強勢地位的中國文學強勢傳播出去,那么依據譯介學的規律,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規律的。在當前的情勢下,唯有在譯介途徑上向西方文學市場靠攏,才能以更多元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圍內傳播當代的中國文學作品。
參考文獻:
[1]謝天振.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M].臺北:臺灣業強出版社,1994.
[2]張南峰.特性與共性:論中國翻譯學與翻譯學的關系[A]//翻譯的理論建構與文化透視[C].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