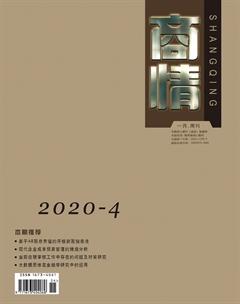“擾亂法庭秩序罪”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官照鈞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對擾亂法庭秩序罪進行修正:一是增設行為類型;二是增加毆打行為的對象;三是刪除“聚眾、毆打”型入罪的程度要求。本文擬對該罪的行為主體和責任主體,“情節(jié)嚴重”等認定標準,罪數及管轄問題進行研究。
【關鍵詞】擾亂法庭秩序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一、本罪的行為主體和責任主體
(一)本罪的行為主體
有三種情況,一是訴訟參與人擾亂法庭秩序的;二是合法旁聽的人員擾亂法庭秩序的;三是不被允許旁聽的人員擾亂法庭秩序的。此外,單位不是本罪的主體,為了單位的利益實施本罪行為的,不能對單位定罪處罰。
(二)本罪的責任主體
除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外,一般參加者原則上也可構成本罪。但本罪法定最高刑僅為三年有期徒刑,一般只處罰首要分子即可。
二、“嚴重擾亂法庭秩序”和“情節(jié)嚴重”的認定標準
《刑法修正案(九)》將“侮辱、誹謗、威脅司法工作人員或者訴訟參與人,不聽法庭制止,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有毀壞法庭設施,搶奪、損毀訴訟文書、證據等擾亂法庭秩序行為,情節(jié)嚴重的”增設為本罪的第(三)、(四)項,“嚴重擾亂法庭秩序”和“情節(jié)嚴重”的標準,需要研究。
(一)“嚴重擾亂法庭秩序”應以不聽法庭制止作為前置要件。不聽法庭制止是評判“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前置要件。
(二)“嚴重擾亂法庭秩序”和“情節(jié)嚴重”的認定以危害后果為主要標準。建議標準為:一是使法庭秩序嚴重混亂,致使案件審理活動無法繼續(xù)進行;二是因法庭秩序被破壞,導致案件審理工作被迫中斷;三是不聽勸阻,多次擾亂法庭秩序;四是損壞法庭設施較為嚴重;五是毆打司法工作人員致多人、多處受到輕微傷害等。
(三)“嚴重擾亂法庭秩序”和“情節(jié)嚴重”的認定應綜合衡量犯罪三性。應全面衡量行為的“刑事違法性、社會危害性、應受懲罰性”,審慎做出認定。
三、罪數問題
本罪主要涉及與妨害公務罪等罪的競合問題。
(一)本罪與妨害公務罪系法條競合
在法庭上行為人采取毆打、威脅方法妨礙司法工作人員進行庭審,同樣侵犯了國家的正常管理活動,也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特征。妨害公務罪屬于一般法規(guī)定,本罪屬于特別法規(guī)定,按照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的原則,應以本罪論處。
(二)本罪與故意傷害(重傷)罪與故意殺人罪系想象競合
本罪可能會造成輕傷、重傷甚至死亡后果。毆打司法工作人員或者訴訟參與人構成本罪并不要求構成輕傷后果,而故意傷害則要求輕傷后果,故就輕傷及其以下后果而言,本罪的量刑相較故意傷害罪重,應以本罪論處。但造成重傷或者死亡的,均應當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論處。
(三)本罪與侮辱、誹謗罪系想象競合
對于行為人在法庭上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或者捏造事實誹謗司法工作人員者訴訟參與人,情節(jié)嚴重的,同時構成本罪和侮辱、誹謗罪,屬于想象競合犯,但侮辱、誹謗罪屬于自訴案件,而本罪不屬于自訴案件,在受害人沒有提起自訴的情況下,應以本罪論處為宜。
(四)本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系想象競合
對于行為人在法庭上破壞法庭設施、實物證據造成損壞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同時構成本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亦屬于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罪論處。
(五)本罪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系法條競合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表現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其必須具備聚眾和情節(jié)嚴重兩個條件。而擾亂法庭秩序罪則不要求必須聚眾,兩罪之間系法條競合且較易區(qū)分。
(六)本罪數罪并罰情形研究
本罪發(fā)生在法庭審判過程中,一般是從宣布開庭起至宣布閉庭止。只能發(fā)生在法庭這一特定場所(應從廣義上來理解,包括在人民法院外為審判案件而設置的非正規(guī)臨時場所,如為普法而在農村臨時設置的審判場所)。以上罪數問題的探討,都是僅僅限定在符合本罪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如果是之外對法院的工作(比如在法官的辦公場所糾纏使得庭審無法開展)進行干擾,構成犯罪的,不適用本罪名,又有擾亂法庭秩序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應數罪并罰。
四、管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9月26日作出的《關于辦理嚴重擾亂法庭秩序案件具體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中規(guī)定:“……對于這種案件,可以由該法庭合議庭直接審理判決,如果原審判組織是獨任審判的,則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人民法院審理嚴重擾亂法庭秩序案件,應當依法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雖然該批復已經失效,但仍有意見認為該批復的精神可以適用于修正后擾亂法庭秩序罪,原因是擾亂法庭秩序罪是一種法官親眼所見的犯罪,由親眼目睹這類犯罪行為的審判組織對該犯罪進行直接審判有利于對該犯罪的迅速處置。
本文認為,最高人民法院之前批復規(guī)定的精神不能適用于修正后的擾亂法庭秩序罪的處理,理由如下:
1.違反了刑訴法規(guī)定的控審分離的訴訟方式。我國刑法對犯罪的追訴分為公訴和自訴兩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使法院集控告和審判于一身,既不是公訴程序,也沒有自訴人,法院對擾亂法庭秩序罪直接審理又自行作出判決,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機制。
2.有悖于刑法關于回避精神的適用。我國刑訴法明文規(guī)定了回避制度,擾亂法庭秩序罪本身侵害的是司法機關的正常工作,甚至可能是因誹謗、威脅司法人員而因言獲罪,如果同一審判組織直接予以審判,這樣就會出現“受害人”審判“加害人”的局面,應該把涉及該罪的法院視為擬制的當事人,適用回避制度。
3.不符合法院內部分工、專業(yè)化審判的要求。如果適用最高法院的批復精神,民事、行政審判庭的合議庭、包括海事法院等原本沒有刑事案件管轄權法院的任一審判組織都可以審判“擾亂法庭秩序罪”的刑事案件,嚴重違背了人民法院的庭室分工范圍,造成各個庭室職責不明,甚至會引起訴訟程序上的混亂,也不符合專業(yè)化審判的要求。
參考文獻:
[1]吳占英.論擾亂法庭秩序罪的幾個問題[J].三峽大學學報, 2006年第2期.
[2]姚莉,詹建紅.擾亂法庭秩序罪追究程序探析[J].法學,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