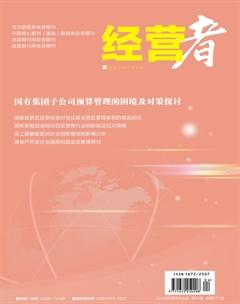無人駕駛汽車交通肇事之刑事責任研究
王子康 吳雨滔

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強人工智能體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的刑事責任主體資格問題,并認為應當否定其刑事責任主體地位;第二,在否定強人工智能體刑事責任能力的基礎上,依據教義刑法學明確無人駕駛汽車的使用者、生產者、銷售者的刑事責任。
關鍵詞 無人駕駛汽車 人工智能 交通肇事 刑事責任
一、無人駕駛汽車概述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征求意見稿)》,所謂無人駕駛汽車,就是指通過搭載先進傳感器、控制器、執行器等裝置,運用信息通信、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具有部分或完全自動駕駛功能,由單純交通運輸工具逐步向智能移動空間轉變的新一代汽車。
美國機動車工程師學會根據無人駕駛汽車的自動化程度,將無人駕駛汽車分為6級:
同時,無人駕駛汽車也是人工智能的一個子產品,因而其自身也必然具有人工智能的一部分特性。故也有學者以人工智能是否能夠在編制的程序范圍以外做出決策為標準,將無人駕駛汽車劃分為弱人工智能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與強人工智能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弱人工智能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只能在編制的程序范圍內做出決策,而強人工智能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既可以在設計和編制的程序范圍內進行決策,又有可能超出設計和編制的程序范圍,進行自主決策并實施相應行為予以執行。[1]
二、強人工智能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刑事責任主體資格審視
基于上述對無人駕駛汽車的分類,有學者認為,具有強人工智能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可以自主學習,并且可以通過對外界的感知以及自身程序的設定來辨認和控制自己的“行為”,而有些超出研發者設計程序之外的“行為”是人類無法完全預測的,因此應當賦予其刑事責任主體地位。也有學者認為,無人駕駛汽車即便有自主學習的功能,也沒有人類的情感,故不能賦予其刑事責任主體資格地位。
由此可見,無人駕駛汽車的特殊性導致了其是否應當成為刑事責任主體之爭,而該問題又成為本研究關于探究無人駕駛汽車肇事后相關主體該如何承擔刑事責任的首要問題,本文有必要首先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一)刑事責任能力之本體審視
如要賦予某一“主體”以刑事主體資格,其首先應當具備刑事責任能力。我國學界一般認為,所謂刑事責任能力,就是指行為主體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其中,辨認能力是指行為主體有認識自己行為的性質、意義以及后果的能力,而控制能力則是指行為主體能夠依其認識而自主決定其行為或不為之能力。一般認為,辨認能力以感知為中心,而控制能力則以情感、意志等為重點。但二者并非相互獨立的內容,因為控制能力以正常的辨認能力為前提和基礎,[2]如行為主體無正常的認識能力,對自然世界和社會生活中的現象、善惡、是非無法有明確的認識,那么就無法期待其基于此認識而能夠產生意思決定從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如果行為主體在擁有正常認識的基礎上欠缺正常的意志能力,那么就不能期待其對自己行為有正常支配的能力。因而,刑事責任能力是建立在行為主體正常的心理、生理基礎之上的,是行為主體感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的有機組合。基于上述對刑事責任能力概念本身的分析,下文也將通過對強人工智能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分析來判斷其是否應當成為刑事責任主體。
(二)強人工智能體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之刑事責任能力審視
1.辨認能力審視
在辨認能力方面,強人工智能體雖然能夠通過對外界的感知和內部的自主學習來做出某種決策,但強人工智能體對這種外界的認識并不是刑法上的辨認能力。上文提到,辨認能力是指行為主體認識自己行為的性質、意義以及后果之能力,故這種認識能力不僅應包括事實層面的認識,還應包括價值層面的認識。而強人工智能體屬性的無人駕駛汽車雖然能夠在設計者的編程之外自主對外在環境進行感知并決策,但這種對外界的感知僅僅是一種事實層面上的感知,不包括其價值層面上的感知。進而言之,強人工智能體僅僅具有智能屬性,而不具有人類的智慧屬性。智慧是指生物體所擁有的高級綜合能力,主要是指對外在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環境的思考、分析和決定等能力,包括情感、理性、生理機能、心理機能等諸多因素。而智能主要包括邏輯智能、語言智能和身體活動智能等。強人工智能體與人類相比,其具備的僅僅是一種以理性邏輯能力為基礎的智能,而非包含感性認知和非理性判斷在內的人類智慧。[3]
2.控制能力審視
刑法意義上的控制能力是指行為主體能夠依其認識而自主決定其行為或不為之能力,故又可將其稱為意志能力。如前所述,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在構成刑事責任能力上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辨認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前提,只有行為主體能夠辨認行為的事實和價值,才能形成自己的意思決定;而控制能力則是辨認能力的繼續,行為主體只有通過對其身體的支配和控制,才能實現其主觀意識。然而,基于上述對強人工智能體辨認能力的分析,由于強人工智能體只有智能而無智慧,只有理性而無感性,因此缺乏刑事責任能力所要求的辨認能力。故此,強人工智能體之辨認能力的缺失也同時導致了其失去了控制能力所產生的前提和基礎,即強人工智能體缺乏意志自由,從而不具備刑法意義上所要求的控制能力,故不應當賦予其刑事責任主體資格。
三、無人駕駛汽車交通肇事之刑事責任歸屬
(一)使用者的刑事責任認定
法律上的責任,是指由特定的法律事實所引起的,對損害后果予以補償、強制履行或接受懲罰的特殊義務。法律責任也是法律義務,是一種由于違反第一性法律義務而產生的第二性法律義務,故當我們說應當對某一主體追究責任時,其必然是違反了某種先行義務。而對于使用者來說,其先行義務在于,無論其使用的是具有部分駕駛功能的無人駕駛汽車,還是具有完全駕駛功能的無人駕駛汽車,其都應當負有定期檢查車輛狀況、定期檢測與保養等義務。如果使用者因為疏忽大意或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的結果而未履行上述義務,從而導致無人駕駛汽車某些功能出現故障,那么當無人駕駛汽車由于這種故障造成交通事故且危害重大時,就應當以交通肇事罪追究使用者的刑事責任。如果使用者履行了這些義務,而無人駕駛汽車在自動駕駛狀態下由于系統作出的錯誤決策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由于使用者在這種情況下未制造法所不允許的風險,因此不能認定損害結果的發生與使用者使用無人駕駛汽車的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從而就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通過對無人駕駛汽車本身的程序、機器零件等進行檢查,明確無人駕駛汽車的生產者或銷售者的責任。
(二)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刑事責任認定
如上文所述,當使用者履行了對無人駕駛汽車定期檢查、保養等義務時,即便無人駕駛汽車在自動駕駛狀態下由于錯誤決策造成了嚴重的交通事故,也只能通過分析其技術瑕疵的產生原因來確定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刑事責任。而對于無人駕駛汽車的技術瑕疵,在這其中,技術上的瑕疵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現代科技條件下能夠發現且能夠通過某種措施避免的,而另一種則是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條件下無法避免的。
對于第一種情形,由于無人駕駛汽車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產品,因此若生產者生產的無人駕駛汽車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或汽車銷售者明知其所銷售的無人駕駛汽車不符合上述標準而仍予以銷售且均造成了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嚴重后果,那么對生產者和銷售者應當按照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定罪處罰。故此,及時制定無人駕駛汽車的國家、行業標準,將有利于對無人駕駛汽車行業進行規范。然而,如果行為主體在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無人駕駛汽車時同時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按照第一百四十條規定處罰更重,那么根據《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二款規定,對行為主體應當按照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如果生產者和銷售者實施了生產銷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的無人駕駛汽車,但未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財產損失等嚴重后果,那么生產者和銷售者將不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由于無人駕駛汽車的價格一般以百萬計,據業內人士稱,谷歌每輛無人駕駛汽車的造價高達 30 多萬美元,故根據《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對無人駕駛汽車的生產者和銷售者應當按照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對于第二種技術瑕疵情形,即使無人駕駛汽車在客觀上造成了危害社會的結果,也不應當追究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刑事責任。根據折中的相當因果關系,判斷某行為與某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需要從事實因果關系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兩方面來判斷。其中,事實因果關系是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事實因果關系,就不可能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則是對事實因果關系的過濾,即在認定某行為與某結果存在事實因果關系的前提下,如果某一行為的結果依社會一般人所認識或所能認識,而行為人所不認識或所不能認識,或某一行為為一般人所不認識或所不能認識而為行為人所認識或所能認識,那么就應當認定某行為與某結果直接存在因果關系,[4]折中的因果關系說以其合理性而為我國和日本等國家廣泛采納。基于此,在折中的因果關系說的理論基礎上,對某一行為主體進行歸責時,首先需要考慮其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允許的風險。而在無人駕駛汽車的場景中,因科技水平限制而難以避免的技術瑕疵所帶來的風險顯然不是法所不允許的風險,而是被允許的風險。其原因便在于,任何社會都廣泛存在各種風險,而風險往往是同利益同在的,沒有風險就沒有利益,社會就難以發展。例如,汽車能給人們出行帶來方便,但也會造成交通事故;刀具能方便人們生產生活,但也會威脅人們的生命健康。而我們當然不能因為這些風險的存在而禁止使用汽車、禁止使用刀具,這顯然是很荒謬的做法,這種風險的存在應當為社會所允許,為法所允許。故此,無人駕駛汽車的普及將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減緩人們駕駛壓力,是為人們所普遍承認的。科技水平限制而存在的難以克服的技術瑕疵所帶來的風險不足以使社會抵制無人駕駛汽車的發展,這種風險也是為社會所允許的,為法所允許的。因此,當無人駕駛汽車由于其難以克服的技術瑕疵在客觀上出現危害社會的結果時,該結果與生產者或銷售者的生產、銷售行為就不存在因果關系,從而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作者單位為華北理工大學)
[作者簡介:王子康(2000—),男,河北邯鄲人,華北理工大學本科生,研究方向:刑法學。吳雨滔(1999—),男,江西南昌人,華北理工大學本科生,研究方向:刑法學。基金項目:本文系華北理工大學創新性實驗計劃研究成果,項目編號:X2019059。]
參考文獻
[1] 劉憲權.人工智能時代的刑法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5.
[2] 黃丁全.刑事責任能力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9.
[3] 張成東.強人工智能體刑事主體地位之否定[J].時代法學,2019,17(05):54-62.
[4] 陳興良.本體刑法學(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