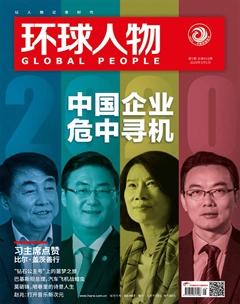王常申:我們有挑戰3M口罩的決心
王常申(口述) 王媛媛(整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內很多口罩生產廠家加班加點趕制口罩。
了聯系到山東日照的三奇醫保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常申,《環球人物》記者打了20多通電話,不是因為別的,就是電話一直占線。我們特地詢問工作人員,是不是他設置了陌生電話不能接通功能?工作人員回復說:“真不是,確實是電話占線,他的電話我們也打不進去。”為了能順利完成這次采訪,三奇公司一位副總硬是站在他的旁邊,守著他幾十分鐘,不讓別人打擾。
疫情暴發后,王常申接到工信部的電話,全力督戰國內工廠,天天加班,電話不斷。他說,不惜一切代價,優先保證國內訂單,滿足國內需求,“盡企業的社會責任,盡中國企業的責任”。
最難的是疫情暴發后的前10天
我是在1993年創業的,到現在也有27年了。想一想,過去這一個多月,應該是最忙的。從2020年1月20日到今天,我們公司全體員工沒有休息過一天,當然我自己也沒有。今年的大年三十、初一我們都在公司上班,我已經連續一個多月一天只睡4個多小時。現在回想這一個多月,最難的應該是前10天。
難處有這么幾點。疫情開始后,我們接到了工信部的指令,要承擔國家的口罩調出任務,保證武漢的需要。但由于事情緊急,很多信息不對稱,出現了多個部門同時指揮的情況,有些事情反反復復沒有確定下來,事情定下來后,廠里也出現了問題。過去,廠里的生產量比較平穩,每天能生產七八十萬只醫用外科口罩、一兩千件醫用防護服,還有一些其他的醫療產品,主要是走出口。要忽然間加大生產量,也是挺困難。首先,前期要拿出這么多錢購買原材料就很困難。再者,人手不夠,當時我們廠有300多名工人。當然,事情一件件都解決了。國家工信部、山東省工信廳、日照市委市政府,包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領導都給了我們強有力的支持,高新區第一時間提供了2300萬元資金支持,我們瞬間購入很多原材料。廠里員工很快增加到上千人。增加的這些人,有少部分是當地政府召集的,大部分是公司之前的員工,他們因為各種原因離職了,現在又回到廠里生產防疫物資。他們很多人接到電話,二話沒說就趕了過來,也不問報酬有多少。這些老員工上手快、效率高,所以產量增加得很快,現在廠里每天能產出300萬只口罩,是原來的4倍。
這一個多月,我很受觸動。疫情發生前,有一位母親一直在廠里工作,疫情發生后,她兩個上大學的孩子第一時間趕到廠里來,跟母親一起加班加點。在我們廠,中層管理人員中女同志較多,很多是母親,常常凌晨兩三點下班,第二天一早正常上班,她們舍棄孩子愛人,真的很拼命!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三奇醫保公司每天給湖北提供上百萬只口罩。
另外,工信部、政府部門的領導來到廠里,幫著我們解決實際問題,比如購買原料、協調方方面面的關系,山東省藥監局也對我們進行現場的技術指導。這些老領導和我們一樣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經常搞到凌晨兩點半,有些領導在公司一待一個多月,家都不回。他們完全沒有領導的架子,車間里膠條能不能粘住?具體流程怎么把控?一項一項去落實。廠里員工都把這些領導當成依靠了,有了困難,第一時間不找我了,先找他們。如果沒有他們給我們幫助,渡過這一關真的太難了。
我們需要一個口罩的民族品牌
我創辦三奇醫保用品公司,是從一張白紙開始,那是一張實實在在的白紙。這個企業原本是國有企業,1993年,我接手后成為一家民營企業。當時,政府就給我一紙任命書,其他就沒什么了。最開始那幾年是真沒錢,我記得最困難的時候是1998年,難到什么程度呢?公司總共37名員工,每個月需要發的工資不到7000塊錢,但我們硬生生9個月沒發工資,最后還是撐下來了。我們的員工真的非常好,他們從家帶煎餅和其他吃的東西來廠里上班,這些我都記得很清楚。1998年以后,我們就慢慢開始做外貿,逐漸有所發展,在國際市場上的口碑越來越好,客戶群越來越多。從2000年開始,我們的營業收入每年有25%到30%的增長。雖然有所發展,但2003年抗擊非典的時候,我們還是規模較小,每天的口罩產量大概也就20萬只,主要供應香港市場。產量不多,但是我們在香港市場獲得了很好的口碑,因為香港是國際化都市,我們的品牌開始傳播到東北亞地區以及歐美地區。也是因為在非典中的良好表現,我們打出了名聲。從2003年開始,我們接到的訂單越來越多。
2005年禽流感流行時,我們的企業規模還不是太大。到2009年,甲流H1N1流行時,公司規模就比較大了,那時候廠里一天口罩發貨量最高達到460萬只。但當時,國內需要的口罩不是太多,我們的口罩大部分出口國外,特別是日本市場。甲流過后,我們產能翻了幾十倍,進一步在國際市場贏得了非常好的信譽。
從2009年開始,我們成為工信部指定的全國13家重點防備物資監控企業之一。這次疫情出現后,工信部第一時間找到我們,也是因為我們這個資質。另外,非典時期、禽流感時期、甲流時期,我們多多少少積累了些實戰經驗。目前,我們的產品已經出口到世界上42個國家和地區。隨著規模的擴大,我們陸陸續續成立了多個專業性子公司,也在越南設立了分廠。
疫情發生的這段時間,三奇在國內取得了不錯的口碑,一提起口罩,有些人會想到三奇了。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人一提口罩,想到的還是美國的3M(明尼蘇達礦務及制造業公司)。美國的3M口罩質量好,是我們的標桿,但也值得我們去超越,我們也有超越的決心。如果沒有,我們就不會到美國注冊商標了。
去美國注冊“3Q”商標時,我們受了阻。3M公司3次向美國聯邦政府提出抗議,理由是“3Q”中的“3”對他們造成傷害。別看美國人大講知識產權平等,實際上不是的,他們的排外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嚴重。在越南、韓國等國家,這些就不是問題。在韓國,從2017年開始,我們的銷量把3M生生壓到第三名甚至第四名。
我想借這個機會,也呼吁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幫助國內的口罩品牌打入國際市場。我們這么一個大國,一年生產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只口罩,卻沒有一個民族品牌,也算是一個遺憾。美國的3M口罩在中國賺到了大把的銀子,其實他一個口罩成本很低,換取幾倍十幾倍的利潤,而且形成了一個非常不公正的競爭態勢,對我們國內的企業非常不公平。我們政府需要做一些工作,企業也要做一些工作,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民族品牌,樹立起信心,這是非常重要的。
長久的發展要靠我們自己去想
近幾年,有些聲音在唱衰實業,作為一家實業公司的董事長,我深有體會。實際上,民營企業這幾年確實比較難,尤其是融資貴、融資難這個問題,我想這不光是我的感受。舉個例子,一開始我們公司去銀行貸款只需要股東簽字就可以了,后來股東的妻子也要簽字。我每次貸款,我太太都要簽字,銀行現在是在一個更強勢的地位了。我有時開玩笑說,公司一旦出現問題,我很可能是房無一間、地無一畝,我擔心會不會到時候連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沒有。對我們來講,這是最可怕的。當然,任何一家企業都想賺錢盈利,但市場風險是不可控的,融資問題是我們感受最強烈的一點。
再一個,國家的政策紅利具體到一個企業,有“最后一公里”的問題。我有時候也調侃,太陽升起來了,紅彤彤的,很燦爛,但是溫暖有些少,要自己去尋找。未來,我們希望能感受到更多直接的、實實在在的對民營企業的利好政策。
這次疫情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公共經濟領域的活動幾乎是完全停止了。從整個經濟態勢來講,我覺得一方面企業要樹立信心,再一個,恢復經濟需要一個過程,國家政策的調整要到位。
像我們這種做醫療防護用品的企業,現階段獲得一定收益,有些企業表現非常不錯。但在這個時間段非常紅火的企業,明天是不是依然紅火呢?我常和員工講,今天的三奇很輝煌,明天的三奇可能會很凄涼。這種情況,我們已經感受過一遍了。2009年甲流時期,我們做到日產460萬只口罩,但到了2010年,我們5個車間停掉了3個。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只能給員工發70%的工資。再有這種情況,我們怎么辦?我們這幾百號人怎么生存?這是我要考慮的問題。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興和衰。現在的醫療器械、醫療防護用品企業處在一個紅火鼎盛的時期,但疫情過去以后,減產是難免的,風險是存在的。所以,生存問題還是首要的,因為我無法去預測市場,也無法預測未來。這一次國家在短時間內出臺了優惠政策,我估計未來全國可能會再有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生產口罩、防護服的企業,這勢必會對我們形成很大的壓力。
我記得是2013年左右,霧霾天氣很嚴重,人們對口罩等防護物資的需求大增,使得我們從2010年的困境中慢慢恢復了。后來幾年我們一直做調整,又專心去攻國際市場。現在,我想的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僅僅依靠這種突發性事件、突發性疫情來贏得發展,我們要把這些當作一個波動,但是長久的發展戰略要靠自己去想,要做一個長遠的規劃,這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