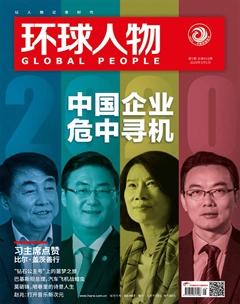人人愛張湯,人人恨張湯
劉勃
漢武帝時代,酷吏特別多,其中張湯最著名。司馬遷筆下的張湯,有兩個細節(jié)令人過目不忘。
一個是審訊老鼠。張湯小時候,家里的肉被老鼠偷了,連累他挨了父親一頓打。張湯就挖老鼠洞,抓住老鼠審判。剛巧這時候,張湯的父親回家,看見兒子走審訊流程、寫判決書,簡直是老獄吏的水平。
二是“腹誹”的罪名。有一天,一位客人對大農(nóng)令顏異說起國家新政策的壞話,顏異嘴巴動了動,沒有回應。張湯就向漢武帝舉報:顏異嘴巴動了,自然是有話想說,想說而不說,一定是壞話,這就叫“腹誹”。身為九卿之一,對政策有意見,不來向皇帝反映,卻在那里腹誹,這是死罪。就這樣,顏異被判了死刑。
這兩個小故事,戲劇感都很強,使人感覺張湯就是一個天生的酷吏。但實際上,張湯的形象要復雜得多。
討人喜歡的“酷吏”
張湯的仕途履歷,大多和司法、監(jiān)察有關,這些工作都很容易得罪人,但他經(jīng)得起360度考評。
對前輩高官,張湯非常恭謹,“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但他媚上卻不欺下,做了大官之后,仍然很謙和,一點不擺架子。
身為張湯的下屬,會慶幸自己遇到了一個好領導。向漢武帝匯報工作,挨了批評,張湯會說:“這是我的錯誤,之前我的下屬已經(jīng)告誡過我不要這樣做。”建議提得好,得到表揚,張湯會說:“這不是我自己的主張,是我的下屬的意見。”
普通民眾也喜歡張湯。張湯喜歡嚴懲豪強,弱勢群體犯了罪,哪怕確實應該依法懲處,他也會設法向皇帝說明罪犯的難處,要來特赦。
這樣一個人,怎么會是酷吏呢?
要解釋也很簡單。張湯做上面這一切,主要不是因為善良,而是因為聰明。也正因為聰明,張湯特別清楚,自己的前途歸根結(jié)底掌握在誰手里——那當然就是漢武帝。
張湯接手的第一個特大案件,是皇后陳阿嬌用巫術詛咒皇帝的案子。那一次,張湯的酷吏作風得到充分展示,最后殺了300多人,陳皇后也因此被廢——敢對皇后這么狠,當然是看準了漢武帝夫婦感情不好,早憋著廢皇后的心。
后來,張湯又審理了淮南、衡山、江都幾個諸侯王的謀反案,做法是“皆窮根本”,處死了上萬人。漢武帝想輕判幾個人,張湯竟一反常態(tài),據(jù)法力爭,認為這些人非處死不可。
眾所周知,打擊諸侯王是漢武帝一朝的基本國策,但他又不愿顯得太漠視親情。面對一個“外施仁義而內(nèi)多欲”的皇帝,張湯的表現(xiàn)當然不奇怪——按照角色分配,完成自己的表演而已。
總之,張湯的作風是凡事順著漢武帝的心意,皇帝想嚴辦誰,就嚴辦誰,而且一定辦得特別漂亮,讓圍觀者也沒話可說。皇帝推崇儒術,張湯的判決就要在法律依據(jù)之外,上升到儒家倫理的高度。他特別招了一批精通《尚書》《春秋》的博士弟子,重大案件的判決書上,一定會引用幾句圣人的言論。
明代的大才子王世貞,讀史的時候提出過一個疑問:張湯的兒子是張安世,父子倆都是出類拔萃的聰明人,為什么張湯刻薄而陰險,張安世謹慎而謙恭呢?
父子性情差別大,固然是常有的事,但張湯的天性也未必就是“刻而險”。他之所以成為酷吏,是因為漢武帝需要酷吏;如果換一個需求完全不同的皇帝,張湯也許會成為一個作風完全不同的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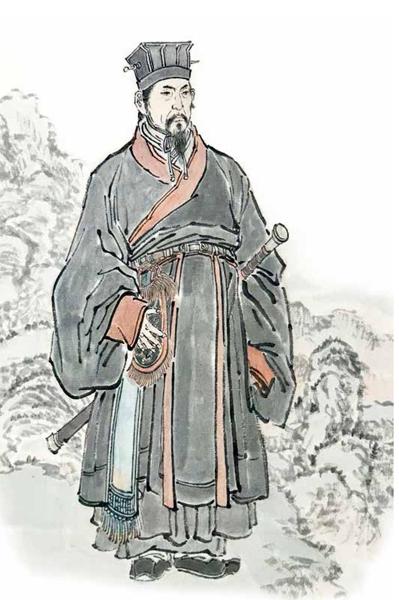
張湯之所以成為酷吏,是因為漢武帝需要酷吏;如果換一個需求完全不同的皇帝,他也許會成為一個作風完全不同的官員。(李云中 / 繪)
“長君之惡”與“逢君之惡”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張湯升任御史大夫,雖然排名在丞相之后,但因為負責監(jiān)察工作,震懾力還在丞相之上。這時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參與國家財政的決策。
元狩年間,正是漢朝和匈奴戰(zhàn)事最激烈、花錢如流水的年份。
回到一開頭用“腹誹”罪名處死顏異的事件。當時,朝廷極度缺錢,為了籌措軍費,張湯和漢武帝商量出一個“白鹿幣”的創(chuàng)意。諸侯王朝賀天子的時候,要進獻一種蒼璧,蒼璧下還要用一種特別的白鹿皮做墊子。這種白鹿皮,只有皇帝的上林苑有,定價四十萬錢一張。
這樣一來,諸侯王就要額外再上繳四十萬錢。顏異當時是大農(nóng)令,相當于今天的財政部長,聽說這件事后,說了一句“本末不相稱”。這個表態(tài),顯然是站在了諸侯王那一邊。在國家最缺錢的緊要關頭,如此不配合決策層的工作,漢武帝當然對他起了殺心。張湯弄出一個“腹誹”的罪名,前提是漢武帝本來就想置顏異于死地,以此來震懾那些有不同意見的官員。
除了白鹿幣,張湯幫漢武帝制定的改革方案都集中在一個主題,就是籌措更多的錢。但在改革的第一個階段,人民身上的剝削加重了,朝廷卻沒有獲得多少好處,好處都被中間經(jīng)手的官吏拿走了。
張湯本人,仍像當年一樣八面玲瓏。但那些敲骨吸髓的經(jīng)濟政策都是他制定的,那些殺人狂一樣的酷吏也是他提拔培養(yǎng)的。
于是,張湯開始為漢武帝培養(yǎng)一批新型官員,這些人才更符合我們印象中的“酷吏”:他們出身卑微,青少年時代活得壓抑,沒有為人生做長遠規(guī)劃的興趣,只是享受大權在握的爽感……他們像瘋狗一樣,咬官員、咬豪強、咬民眾,也互相撕咬。他們就像一顆顆炸彈,把朝廷向社會汲取資源的阻塞通通炸開。朝廷因此可以源源不斷獲得金錢,支撐著漢武帝開疆拓土的雄心。
而張湯本人,仍像當年一樣八面玲瓏。但那些敲骨吸髓的經(jīng)濟政策都是他制定的,那些殺人狂一樣的酷吏也是他提拔培養(yǎng)的。官員們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也看得清楚,所以“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張湯成了社會各階層的千夫所指。
孟子說:“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君主交代了一個壞任務,你去貫徹執(zhí)行,這叫“長君之惡”;君主有了壞想法,還沒想好怎么做,你替他把方案拿出來,這叫“逢君之惡”。如果說其他酷吏只能算“長君之惡”,那么張湯這樣一個掌握財經(jīng)、法律、意識形態(tài)的全方位高手,就是真正的“逢君之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