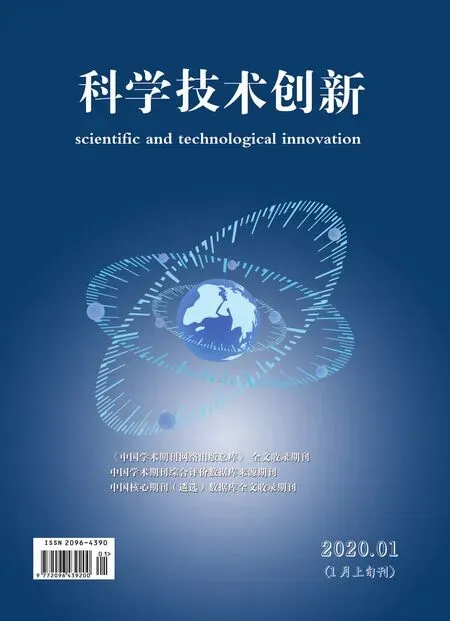基于馬爾可夫鏈的過程性評價量化研究
陳亞麗 譚 琳 楊潤涵
(西南石油大學 理學院,四川 成都610500)
教學評估以一定的教育價值觀或教學目標為基礎,采用可行的科學手段,系統地收集信息進行分析和整理,對教學活動的實際或潛在價值、過程和效果進行判斷,研究教學和提高教育質量,并為教育決策提供依據。為保證教學質量,各高校普遍開展了教學質量評價工作,評價指標體系已基本趨于完善,但評價體系的差異較大,大多采取學生為主、教師為輔的體系,這種評價體系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缺失對教學活動全過程運行效果的評價[1]。
1 過程性評價的理論與實踐
過程性評價的內涵是在實施教育項目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有效的溝通和互動手段,使教學評價貫穿于教學的全過程,分析教學過程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從而達到教學目的,實現提高教育質量的目標[2]。過程性評價在學生評價系統中的優勢有以下三點:首先,過程性評價方法可及時反饋教師的教學信息和學生的學習信息,并通過課程評價與課程教學的結合將反饋信息有效回流至后繼的教學安排和學習計劃中;其次,過程性評價對學生的考核范圍更全面,考核手段更科學,考核依據不僅僅包括考試分數,還有對學生的學習動態變化的評估;最后,過程性評價發生在整個教學環節中,對學生學習的引導作用更加突出。過程性評價在實際開展中也存在兩點局限:首先,過程性評價難以統一評價的規范和標準,它使用更開放和即時的評估方法。評估數據和判斷標準是動態的,因人而異,其評價標準不能嚴格統一。過程和程序的標準化和規范化需要進一步加強。第二,過程評價更難實現嚴格的公平和公正,在教學評價中,過程評價更體現了教師和學生的主體性和個性,這就對教師專業標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將以上述數據作為依據來評估A 班3 個小組在這一階段的學習效果,為避免產生“基礎先入為主”和“期末分數定好壞”的結果,決定采用具有馬爾可夫 性質的馬爾可夫鏈模型進行計算和分析。考慮評價指標的不確定性[3],上述評價項目的設計非唯一設定。
2 馬爾可夫鏈法的應用及分析
2.1 馬爾可夫鏈法的數學模型
2.2馬爾可夫鏈法的步驟及計算
2.2.1 統計學生的成績,確定初期向量


2.2.2 確定成績轉移矩陣
2.2.3 求平穩分布
2.2.4 求期望成績
2.3 結果與分析

表1 計算結果統計
在優化過程性評價體系的探索中,期末考試成績不再成為唯一的評判標準,本研究中對試點班級中3 個組學習效果的評價指標除期末考試平均分外,還考慮了各組的基礎差異與進步情況、協作學習能力以及學習過程中的行為的影響。試點班級3個組的初始狀態、預期成績分布等數據的計算結果如表1 所示。初始狀態中,各組成績百分比較高的等級分別為B、A、B,即2組在初始狀態中的等級上占優勢,說明2 組的優生略多,而3 組在實際初始成績中占優勢,說明該組學生的整體基礎較為扎實,1 組為中等水平,成績等級呈正態分布;單從A 班的實際考試成績平均分來看,3 組平均分最高,其次為1 組,2 組,若直接判定各組學習效果的優劣則有失公平,但可以看出優生略多的2 組在期末考試中成績最低,而整體基礎較為扎實的3 組平均分最高。預期成績分布中,3 個組都是等級C 所占比例最大,而在實際成績分布中占優勢的為3 組,其次為2 組、1 組,1 組的成績期望值最高,而2 組在該兩項指標中都是最低分,說明成績呈正態分布的1 組在學習過程中的進步最大。
3 結論
通過追蹤和記錄試點班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行為數據,結合上述計算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整體基礎扎實或水平平均的團體發展趨于穩定,而兩極化或一邊倒分布的團體中,由于存在基礎差異較大導致互助困難和疲倦影響整體水平;其次,從平時的學習行為數據來看,優生偏多的小組在線上和線下兩個維度中的交流互動頻率較低,在課堂表現中獲得加分項的多是基礎較好的學生,幾乎沒有呈現共同討論和幫助基礎較差的同伴獲得表現機會的情景,而整體基礎較為扎實的小組和水平平均的小組則會在線上線下自發組織討論活動,并在課堂表現中盡量讓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機會從而獲得加分項,說明在協作學習中,擁有同質學習特征的同學更容易成為學習伙伴;最后,通過獲取試點班級所使用的互聯網學習平臺的數據,發現初始狀態略微落后但水平平均的小組學生的在線瀏覽MOOC 視頻時長最長,觀看預習課件次數最多,且該組學生的在線活躍度較高,說明在混合式學習中,在線學習的積極性也是影響最終考核成績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