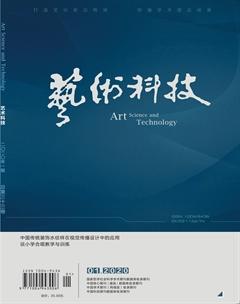文化變遷視閾下的鄉土文化發展研究
摘 要:面對現代性力量沖擊,鄉土文化正在發生變遷,表現為鄉土文化活動的衰退和鄉土文化精神的異變,鄉土文化變遷的過程造成了文化儀式異化、價值體系衰退等問題。本文從文化變遷的視閾,從創新、傳播和涵化的維度,提出引導鄉土文化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文化變遷;鄉土文化;發展
鄉土文化指“以村落空間為基本依托所形成的村民共同參與、共同分享的文化活動,是建立在村落歷史記憶、精神文化、生產生活之上的文化綜合體”,[1]具體指我國在幾千年來傳承和發展中不斷形成的習俗規范、認知共識、價值思想等。面對現代化力量的沖擊,“農村新經濟的發展帶動了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遷,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遷是現代化建設的趨勢”。[2]在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推動下,鄉土文化正處于變遷的關鍵節點。文化變遷是指文化在結構、形式和功能上發生的變化,對鄉土文化的發展的分析具有較強解釋力:首先,鄉土文化的變遷包含在文化變遷中;其次,文化變遷理論能夠以發展性的視角探析鄉土文化變遷過程。基于此,本文擬從文化變遷的視閾,通過分析鄉土文化活動和文化精神的變遷來把握其發展邏輯并提出建議。
1 鄉土文化活動的衰退及根源
進入21世紀之后,城鎮化和工業化開始打破農村地區地方性、封閉性的特點,現代性力量侵蝕著農村的傳統生產生活,傳統鄉土文化活動發生衰退,不僅文化活動的次數減少、規模縮小,而且內容不斷簡化,形式愈加單一,甚至一些鄉土文化活動失去了傳承而逐漸湮沒。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幾方面:
其一是鄉村中公共空間的“萎縮”。鄉土文化活動的生命力根植于鄉村的公共空間,但當前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和農民集中居住情況的涌現,農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革,尤其是消費觀念和娛樂方式愈加私人化。[3]與此同時,原來在村落中的傳統公共空間消逝,村民日常交流、休閑、娛樂的非正式公共空間不斷變少,限制了鄉土文化活動的開展。此外,公共權威人物在村莊治理體系中也逐漸失去了話語權,鄉土文化活動失去了主導者和組織者,農民對鄉土文化活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不斷降低。
其二是鄉村中社會參與力量缺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了城市,出現了大批農民工。”[4]由于大部分中青年農民周期性地外出務工,農村已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生產生活模式,這就導致地方的傳統農耕社會中的傳統文化活動和儀式活動沒有人力的支撐與參與,也就不足以完成其延續與傳承。社會參與力量缺位亦使得中青年農民對鄉土文化活動陌生且疏離。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由血緣和親緣構成的文化活動過程必然衰敗。
其三是鄉村中現代文化的蔓延。“文化本來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環境里得到的生活就會形成什么方式,決定了這人群文化的性質。”[5]傳統鄉土社會中的農民能夠體味鄉土文化,但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以都市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文化通過電視、廣播、自媒體等形式開始全面向鄉村蔓延并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現代文化逐漸替代鄉土文化成為了鄉村社會中的文化主導,其急速蔓延的態勢不斷擠壓著鄉土文化的生存空間,致使傳統文化活動和儀式活動對地方農民難以形成吸引力。
2 鄉土文化精神的異變及根源
鄉土文化精神是道德認同感、時空認同感和價值認同感的集成:道德認同感是指鄉土文化具有內在的道德追求和倫理準則;時空認同感指的是農民對自身村落共同體的“歷史感”與“當地感”認同;價值認同感主要指農民的精神信仰和人生目標追求。從文化變遷的視閾動態來看,鄉土文化精神已經發生異變,其表現及根源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道德認同感的異變。“微觀系統理論中,將環境看作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動態過程,強調環境對人的影響。”[6]傳統鄉土社會依靠人的道德輿論作為治理方式。但當下依靠社會輿論所維系的道德體系對人的約束作用越來越小。傳統鄉土社會農民的行為受到傳統道德觀念的約束,但當下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新型價值觀形成主導,農民的價值觀念轉向財富的占有和個人地位的獲取,農民群體在不受約束的情況下開始追求個體化的價值目標。
其二,時空認同感異變。當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之后,留在農村的只有老年人和留守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7]原來的地緣與血緣關系不斷地弱化,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歷史感”和“當地感”都在弱化,不僅弱化了人們對村落生產生活方式的認同,價值認同面向村莊之外的城市,而且逐漸模糊了村莊的歷史,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缺失了對鄉土的歸屬感。伴隨著文化變遷,鄉土文化精神傳承和延續的基礎逐漸衰落,農民在價值體系上出現了真空。
其三,價值認同感異變。“貨幣下鄉”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經濟理性逐步成為農民的價值觀念,原本由血緣紐帶構成的“差序格局”在傳統鄉土社會的低流動、封閉的環境中能夠發揮作用,但面對流動速率快、利益交換為先的市場經濟,“差序格局”不斷向“工具性差序格局”蛻變,人們建立關系時考慮的主要是利益。現代性力量的進入打破了鄉村社會原有的價值格局,這種蛻變趨勢亦可表述為農民的原子化特征,利益代替價值成為最重要的取向。
3 從文化變遷視閾引導鄉土文化正向發展
鄉土文化活動及鄉村文化精神的異變最終帶來了鄉土文化的衰弱。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的宏偉戰略,重點提到了鄉風文明建設,作為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基礎性組成部分,鄉土文化應發揮積極作用。文化變遷理論認為,文化的變遷過程要經過文化創新、文化傳播和文化涵化,鄉土文化的未來發展也應從3個層面切入。
其一,從文化創新入手,強調挖掘鄉土文化的內生性價值。鄉土文化的創新不能僅僅依靠城市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注入,這種“送文化”的形式難以在鄉土社會扎根,因此要注重對鄉土文化內生性價值的挖掘,從鄉土文化自身進行活化和創新,例如創新地方民間戲曲、節日儀式活動等文化活動,逐步形成有吸引力的文化品牌。“做好本土化的同時推陳出新,找到文化與自然的獨特吸引力,而不是一味照搬模仿城市文化。”[8]應以“種文化”的形式挖掘鄉土文化內生性價值,打造適應新時代的現代鄉土文化。
其二,從文化傳播入手,通過新媒體等手段傳播鄉土文化。鄉土文化難以憑借其自身力量實現很好的傳播,國家可以通過資源輸入等形式幫助鄉土文化實現正向傳播。同時也要注重與新媒體的結合,在傳播過程中保障鄉土文化的“根”和“魂”,使其逐步為大眾所接受。亦可通過打造休閑農業、文化產業進村等項目重塑鄉土文化新形象。[9]通過文化傳播,不論是外出務工的中青年農民,還是留守群體,都能夠革新對傳統鄉土文化的認知。
其三,從文化涵化入手,結合現代性的力量發展鄉土文化。“保護傳統民俗文化從來不是靠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的努力就能夠做到的,靠的是整個社會對這項技藝的尊重和認可。”[10]鄉土文化的發展最終要在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融入現代社會,一方面應將其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合,形成新的價值內核,另一方面,將其與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相融合,使農民可以更好地享受鄉土文化。鄉土文化發展可以建構新型價值體系,改善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為“美麗鄉村”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 韓鵬云.鄉村公共文化的實踐邏輯及其治理[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8(3):106.
[2] 陸紅紅.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思考——基于“沙集鎮”的電商模式[J].經濟研究導刊,2018(27):29.
[3] 孫彬.近年來農業發展對農村傳統社會文化的影響[J].神州,2018(28):12.
[4] 孫彬.農村養老問題的分析以及解決方案的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8(27):29.
[5] 魏俊宇.試論電影《流浪地球》背后的價值觀[J].戲劇之家,2019(19):122.
[6] 高海梅.試析生態系統理論下人的變化趨勢——觀《福貴》有感[J].戲劇之家,2019(23):113.
[7] 張國棟.由《系紅褲帶的女人》談農村留守婦女[J].戲劇之家,2019(14):111.
[8] 李笑儀.實景演出之內核:文化、生態和效益——以大理實景演出《希夷之大理》為例[J].戲劇之家,2019(22):17.
[9] 陸紅紅.淺析鄉村文化發展之路——石頭寨村調研有感[J].青年文學家,2018(30):192.
[10] 孫彬.農村傳統民俗文化的沒落——觀《百鳥朝鳳》有感[J].青年文學家,2018(30):179.
作者簡介:蘇鎏一(1997—),男,河南開封人,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