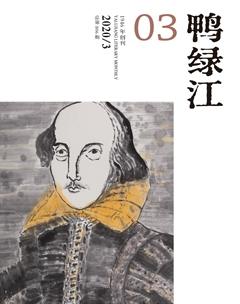心存敬畏
今年的春節(jié)和藏歷新年正好隔了一個月,很多時候兩個節(jié)日之間只相差一兩天。我是1月14號從內地趕回拉薩的。隨著內地來西藏做生意、打工人員的返程,拉薩城變得空蕩蕩的,失去了往日的喧鬧和擁堵,那幾天的天氣也陰沉沉的,非常冷。鐵鼠年就這樣到來了。沒有想到的是“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這兩個名詞成了出勤率最高的詞,一下攫住了人們的眼球。拉薩從春節(jié)初三開始進入到抗擊疫情的戰(zhàn)斗中,一切娛樂場所和旅游景點都暫時關閉了。拉薩人通過手機和電視關注著武漢的疫情。拉薩藥店里的口罩、消毒液銷售一空,甚至糌粑都被搶光了,人們突然進入一種惶惶的氛圍里。每天最主要的事就是手機上打開騰訊新聞,看“抗肺炎”頻道,祖國的版圖上只剩西藏一片雪白。可是,沒過幾天有消息出來,說一位從武漢坐火車過來的人被隔離檢查,那片雪白變成了淺黃色。拉薩城里人人都戴著口罩,飯館、商店、發(fā)廊逐漸關門,但人們的情緒逐漸恢復了理性。
可能是不習慣整日待在家里,各種調侃憋悶的小視頻在微信和抖音里發(fā)來發(fā)去,以此消解這時間的漫長。也有人發(fā)來藏族祖先關于蝙蝠的文章,以此證明藏族先人的真知灼見。更有的拿來藏醫(yī)院天文歷算機構出的年歷,證明這個疫情在年歷里早有記錄。從拍照發(fā)過來的年歷上,我看到了“零散爆發(fā)鼠疫”這幾個字,確切地說,它沒有指向具體的地方。這藏族年歷也挺有趣的,之前,它對日食出現(xiàn)的時間精確到了分秒里,西藏電視臺為此專門拍過一個小專題片,還聽人說汶川地震前年歷里也有過相關記載。西藏的文藝界也以書法、攝影、詩歌等各種形式,祈福湖北盡早戰(zhàn)勝疫情。對我個人來講,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能走到現(xiàn)在這個地步,跟武漢是緊密關聯(lián)的,是武漢的刊物和編輯發(fā)現(xiàn)和扶持了我,才使我走出了藏地,心里始終對他們滿懷感恩。也巧,我的小孩高中是在武漢西藏中學讀的,那里的老師們對藏族學生的成長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當疫情逐日擴散,武漢被封城成為一座孤島時,我們只能祈禱那里的所有人能平安地度過這次劫難。
二十多年前,我讀過加繆的《鼠疫》,可能那時沒有親身經歷過這種災難,對所敘寫的那種遭際沒能產生強烈的共鳴。后來,我國發(fā)生SARS,對這種災難性的疫情有了切身的感受。2004年,我讀到了北村的長篇小說《憤怒》,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余杰在序中引用的《尼金斯基手記》中的那段話:“我不需要邪惡——我需要愛。人們以為我是個邪惡的人。我不是。我愛每個人。我寫出了真實。我不喜歡虛假,我需要善良,不要邪惡。我是愛。人們當我是個稻草人,因為我戴一個我喜歡的十字架。”我們每個人的心里應該有敬畏,那是與自然、與萬物和諧相處的法則。記得我小的時候,每年第一次吃到時令的水蘿卜或蘋果、桃子時,老人都會教我們念一遍:“請你讓我吃掉你,求你千萬別傷害我!”長大后覺得這是個很幼稚的行為,甚至覺得有些可笑。但是后來看到《和諧拯救世界》這個片子時,其中有一段講日本的一位科學家從世界各地的江河湖泊里采集水,然后倒進試管里,上面用世界各種文字寫上“愛”“恨”兩個字,讓其冰凍結晶。寫有愛的結晶體花紋很漂亮,寫有恨的結晶體花紋極其丑陋。由此可見人心與自然萬物是相通的。我們的內心應該有敬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躲過很多劫難,與地球融洽地生存。
當下醫(yī)務人員和科研工作者們正夜以繼日地奮戰(zhàn)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其中有很多人被感染離世,讓我們扼腕嘆息。敬佩這種崇高的犧牲精神。文學應該記錄這場艱難的時刻,但需要時間的沉淀和升華,不是為了歌頌,而是為了反思,為了杜絕中華大地上無謂地再次襲來一次災難,為了阻止更多的生命凋謝、家庭破碎。
作者簡介:
次仁羅布,西藏拉薩市人,1981年考入西藏大學藏文系,獲藏文文學學士學位。現(xiàn)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委會委員、西藏作家協(xié)會常務副主席、《西藏文學》主編,一級作家。西藏自治區(qū)學術帶頭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西藏民族大學駐校作家。2004年參加了魯迅文學院第四屆高級研討班。小說《放生羊》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祭語風中》獲中國小說協(xié)會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版第三名,小說《殺手》獲西藏第五屆珠穆朗瑪文學獎金獎,中篇小說《界》獲第五屆西藏新世紀文學獎。作品被翻譯成英語、韓語、日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