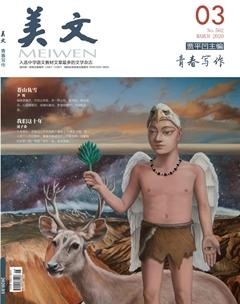湖濱夜話
王一塵
“嗚呼!吾輩進退不茍,生死唯命,務請尚方寶劍斬彼元兇,頭懸國門,以儆天下墨吏!”康熙三十六年,一個書生糾集四百余名落榜舉人,抬著財神擁入南京貢院,撒了他一城揭帖,攪了他一個四腳朝天。
書生叫鄔思道,才華冠絕,行文鋒銳。南京春闈,紅榜無名。
畢竟鄔思道只是被歷史選擇出面的那一個,如若非他,歷史還可以選擇更多的“鄔思道”。而逼得他不得不翻臉的,是清朝腐朽的教育制度——八股取士。它死板木訥,但也精密詳盡。我甚至難以想出還有什么制度能在當時與這個沒落的封建王朝相契得嚴絲合縫。 事實上呢,當時清朝的龐大的官僚體系營生出遍地的朋黨,在封建制度搖搖欲墜之時,這群官僚不可避免地膨脹、壯大,在王朝中生根。出于政治需要,必通過這不公開不透明的八股取士制度扶植本族后代,出于經濟需要,收賄斂財,扶植傀儡,如每年科考,從各路考生手中刮取數萬兩銀子。這些考生中的大多數,無可避免地加入他們的官僚體系,使之愈加壯大。清朝的官僚體系的大部頭都以這種方式趔趄著。所以在清朝抄家高官時,一個人背后就是宛如沙漠植物根部的錯綜的龐大體系。 殺不凈,斬不絕,留一脈,生一叢。 科舉,這個看似穩妥的體制背后盡是埋葬清朝的劇毒。
清朝輸在哪?沿用前人成功探索出的體制有什么錯?怎么會最終導致封建官僚政體的消亡?
清朝只看到當下需求——如何給這個“老者”續命,能多活一天算是一天。而沒有想未來之勢——怎樣讓這個老者“返老還童”,帶動岌岌可危的清朝重新煥發生命力。這好比衣服,先朝的科舉制度大都是根據自己的國情量身定制,適用范圍僅限于前朝。而清朝,是誕生于前朝的覆滅。若一個人胖了,依然穿著舊衣服,穿下是能穿下,但合不合身就要另講。畢竟過緊的衣服穿久了,扣子崩開只是早晚的事。清朝,連再做一件更合身的衣裳的意識都不具有,依然讓腐朽的舊科舉拴著整個王朝的書生學子。直到近代,這件衣服終于爆成破布——人才匱乏、民眾愚昧、國力衰弱,赤身裸體的清朝只能被一刀一刀地往下剜肉。清朝真正所需要的,不是這件不合身的衣裳——八股制,而是合身的那件——改革體制,汲取更為先進全面的西方教育的優勢,結合國情,為己所用。
民國,則更善于為自己縫制合適的衣裳。它在風口浪尖中誕生,各路江海奔涌呼嘯成這一潭源頭活水。它“活”,就活在它的常新:教育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使民國的學風教風煥然一新。以蔡元培先生為例,“大學要擺脫官場習氣,具備自由的品格”“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政治上,京師大學堂萎靡之風肅清,北平成為民主科學陣地,愛國政治運動的大潮層浪相疊,潮水灑到越來越多國人身上,更多國人隨其勇赴民族救亡之路,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學術上,宛若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各路觀念沖擊碰撞,思想火光熊熊燃燒,學者及著作以高質高量的形式涌現,學術花園百花繁密。“溝通文理,廢科設系,改變‘輕學而重術的思想”“教育是求遠效的,著眼于未來,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內表現出來,所以講‘百年樹人”,蔡先生敏銳察覺出教育的長遠性,以他為代表的具有高瞻遠矚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們,共同創立了學習、學術并舉的近代教育體制,育人、育才,進一步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家發展,且看:文士輩出,思想解放促時代文化研究冉冉上升;科學不泯,理學人才作中國科技飛躍中堅鐵臂。
追溯千年,宋初與宋中,各地書院盛行,書院的獨特教育宗旨自覺與官學劃出一道分水嶺:書院不作科舉附庸,愿培養傳道濟民之才。教書先生們大都反對以追逐科舉及第為直接目標的學校教育,強調教育的首要任務在培養人的德性。大師以“人師”自律,弟子以“正其誼不謀其利”的“醇儒”自策。教育上的自由活力滲透至社會各面。范仲淹、歐陽修等諫臣,王安石等革士,在政界刮起正氣素風;蘇軾、柳永等文才,于詞壇開創琳瑯各派;畢昇等匠人于科技引領世界創新。然而南宋以后,理學逐步作為思想正統被統治者扭曲為統治根基,致使思想進一步僵化,人們對于功名的過度追求以及統治者的約束固化了教育模式,自由講學最終為封建專制主義所不容。人才的培養又被拘于官僚體制下的需要,范仲淹般的諫臣幾近絕跡,加重了官僚體制的腐敗性與脆弱性。這樣看來,清朝和民國的教育道路就宛若將宋朝的教育道路倒著走了一遍似的。
時代的教育之路上,前人或深或淺的足跡分明昭示著:教育不能只依循舊制,模式化“造人”,更應該探索適合當下及未來所需,依據發展趨勢“成人”“育才”。
我作為高考大省的學生與現代教育的體驗者,正經歷一輪輪教育革新。就目前的語文教育來看,大部分地區語文教育的技巧性、規律性的學習特點遠大于其實用性、思想性。再細化至詩歌學習,我所經歷的詩歌學習,是將詩歌細密分為幾大類、數十小種,總結答題模板,用模型化的思路套進詩歌的身體,從詩歌身上榨取圓滿的得分答案。但當自己去誦讀詩歌時,由于缺少師長的點睛,經常會在誦讀過程中將詩歌籠統地一筆帶過。這好比將野生極樂鳥馴化為家養金絲雀,若將其深鎖籠中,雖能發揮其短期的觀賞性價值,但鳥兒在籠中只能消磨生命,自然賦予其的瀟灑靈動被囚籠碾磨殆盡;若將其驟然放歸自然,鳥兒會因難以適應自然而生存困難。所以作為主人應該做的既不應是絕對的固化與囚禁,這只是觀賞一時的狹促需求,也不應給其絕對的放飛與自由,這是不計后果的理想觀念。應該教會它的是全面的適應——既能在院中安靜守望,也會在天際縱情翱翔,它知道何時回家,也知道該飛多遠,適應得了庭院,也熱愛自然風光。現代語文教育自然比養鳥兒般復雜得多。從全局來看,既應發揮其技巧性——適應高考人才選拔的既定制度,也要開拓其思想性、實用性——讓學生在文史海洋徜徉、在現實生活中靈活運用語言,使其針對面從短期高考擴展至學生的長期社會生涯,學會語言使用與文化思辨。當今時代,“第四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般進行,多極化趨勢與全球性聯系迅速加強,人口流動、種族融合、各國交往……愈發復雜的世界形勢下,中國更需要具有全球性視野、長遠性眼光的教育體制,不拘于一時所需,在教育過程中注重學生全面發展,在各個領域培養具有更高格局、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創新型人才。教育,應當成為汩汩清渠,為國家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水。
養德池濱,靜話歷代教育,是夜月明,默言世事滄桑。嗚呼我嘆:“論各朝教育之制,清之腐化,蓋其頑冥,不善革新,專于官僚維系所求,不瞻其時更迭之需,其制必亡。民國之常新,蓋其兼容,勇革舊制,既已知現時之待,且深明將來之勢,其制甚效。今世界諸國通密,既欲民族興復、吾輩自強,高瞻遠矚之制,豈可不出?”
今吾中國者,乃萌芽自八代興衰,自立于萬國列邦。天地大矣,前途遼矣,吾當任重而道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