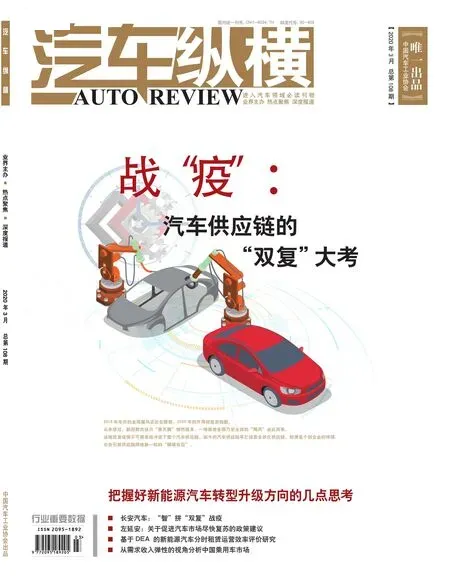憂與優
——“疫”中汽車供應鏈的湖北樣本
特約作者/《建約車評》 孫利
以東風集團為龍頭,湖北汽車產業已經成為中國汽車工業一股重要的力量。產量一直位居全國前列,市場份額在8%左右。2019年,湖北省汽車產量為224 萬輛,排名中國第4,占據全國8.8%的產能,而武漢占據了湖北80%的產能。武漢的汽車供應鏈體系也很發達,汽車零部件公司有650 家之多,不僅供應武漢本地市場,也向全國以及全世界輸出產品。武漢的疫情對汽車供應鏈沖擊力更大,持續時間更久。
湖北“老周們”在憂心什么?
“各類企業先按不早于3 月10 日24 時前復工。”2 月20 日晚,老周在武漢的家里剛吃過晚飯,不久便收到了公司新發的延期開工的通知,武漢封城以來,這是他第三次收到公司的延期開工通知,而這一次是湖北省政府統一下達的復工通知。收到通知的老周松了一口氣。

老周曾是二汽的老員工,后來去了一家大型合資零部件企業做了高級經理,他們公司幾乎給武漢所有的車企供貨。在復工再次延期之后,他們同事之間每天在群里討論最多的是大家是否安全,家人是否健康,家庭需不需要幫助。
談及關于疫情對武漢汽車行業的影響,老周認為:“毫無疑問,銷量方面,在武漢建廠的車企受影響很大。像東風本田和上汽通用,在武漢的產能特別高。去年東風本田銷量那么好,公司的產線幾乎沒停過,這次銷量影響會比較大,不知道下半年能不能拉回來。但是像神龍和東風雷諾這樣銷量不好的車企,今年的形勢就更難了,少虧當贏吧”。
相比車企的復工,身在零部件公司的老周現在更擔憂武漢的供應鏈恢復問題。“我們公司的二三級供應商都在武漢和周邊,大家都沒法動工。即使復工,人員到崗也需要不少時間,很多還是湖北省外員工,湖北省內的人很多心態還需要調整。”和很多企業一樣,老周的公司供應鏈正處在完全停滯的狀態。
“現在真正的麻煩是,供給海外的零件交不出貨。有的要丟單賠款,但是最怕的是丟客戶。海外車企現在急得不行,都在跟蹤,有的在想辦法從別的地方調產能。”老周強調,現在比較擔心供應鏈的產能外遷,尤其在海外有產能的跨國公司,他們能夠騰挪的空間更大。
“我們公司目前還好,海外其他地方的企業一時半會沒辦法轉產,但是有的公司已經在研究這個問題,如果疫情4 月底不能結束,會有更多企業要尋求轉產。”老周的擔憂也是很多業內人士正關心的問題。
中國的汽車供應鏈產業是否會面臨因疫情而導致產業外遷的問題?
這是需要正視和回答的問題。疫情對供應鏈的沖擊正擺在眼前,對汽車企業的產能布局和供應鏈網絡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末了,老周說了一句“二汽這次太不容易了”。

湖北產能之傷
和很多年紀稍長的湖北人一樣,老周還是習慣把“二汽”掛在嘴邊。在年長一輩的人眼里,中國第二汽車制造廠才是“東風”的本名。這是一個充滿時代感與榮譽感的名字,也是湖北汽車工業無法繞過的名字。
2003 年,為了加強國際化協作,利用好湖北的區位優勢,更名后的東風集團將總部從湖北十堰搬遷至武漢,東風集團和旗下的多家企業走向了發展的快車道。
目前,東風旗下的神龍汽車、東風本田、東風乘用車、東風雷諾等公司均在武漢投建工廠,并慢慢形成東風汽車集團今日的格局。依托東風集團的發展,湖北的汽車產量一直位居全國前列,市場份額在8%左右。背靠九省通衢的武漢,東風汽車仿佛打開了任督二脈,逐漸形成汽車產業集群優勢,成為全國汽車重鎮。
2015 年,處在產能擴張期的上汽通用看中了武漢的產業集群和區位優勢,決定南下武漢,成立上汽通用武漢分廠。上汽通用入局之后,湖北汽車產量再上一個臺階,產量在全國占比接近9%,排名全國第4。以東風集團為龍頭,湖北汽車產業成為中國汽車工業一股重要的力量。
蓋世汽車研究院數據顯示,2019年,湖北省規劃的乘用車總產能超過300 萬輛,根據2019 年的乘用車產量,總體產能利用率在62%左右。
在車企端,東風旗下的分公司表現各有不同,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以東風日產和東風本田為代表的日系合資公司表現最為出色,產能利用率幾乎100%。東風本田產量甚至超過規劃時的產能,幾次擴容之后,達到80 萬輛,但市場依然供不應求。
東風日產的布局更為分散,主生產基地在廣州花都,湖北只有一座襄陽工廠。目前襄陽工廠主要生產東風日產的高端車型樓蘭、天籟以及英菲尼迪國產車型,年產能25 萬輛。除了日系雙雄,東風自主乘用車東風風神的產能利用率也達到90%以上。但是東風風神的體量較小,只有10 萬輛的產能。產能利用率最低的是東風神龍以及東風雷諾。
近年來,法系車遭遇前所未有的市場下滑,產能利用率處在極低的運行水平。為了降低損失,神龍汽車已經計劃關停部分工廠。
東風集團下各公司兩極分化的表現,印證了中國汽車市場集中度正不斷提高。除了東風系,武漢堪稱上汽通用的風水寶地,其產能利用率一直處于滿負荷狀態。武漢工廠年產量超過60 萬輛,在上汽通用全年160 萬輛的產量中占比38%,超過三分之一。
目前,疫情依然是影響產能恢復的主要因素。依當前趨勢,全國除湖北外的疫情基本處在被牢牢控制的狀態。根據衛健委專家組的判斷,4 月底,全國的疫情有望結束,湖北之外的省份可能要更早一些。
目前各省新增確診病例已經降至兩位數,全國疫情見頂的趨勢比較明顯。湖北省內武漢以外的多個城市已經出現了0 新增。武漢市的新增病例數量不斷下降。在當前的收治力度下,有望在4月底結束全部戰斗。
2 月份,在疫情面前,全國生產處于一盤棋的狀態,銷售端完全被抑制。湖北省內的汽車產能雖然為0,但是省外企業一時也難以復工,員工多處在居家隔離的狀態,產能差距并不大。
拉開產能差距的關鍵在3 月份。各地企業完成員工14 天隔離之后,車企開始真正全面恢復生產。生產端的拉動主要是為了恢復供應鏈活力,以及為4月份解禁備庫存。如果3 月10 日之后,湖北能夠順利復工,在復工節奏上湖北比全國其他地區晚一個月左右。在14天的隔離后,隨著員工陸續到崗,湖北企業有望在3 月24 日左右組織有序生產,產能開始逐漸恢復。4 月份疫情完全結束后,產能和銷售恢復正常。
總體上,按1 月23 日武漢封城日計算,相比往年同期,全國其他省市的產能損失在1.5 ~2 個月,但是湖北的總產能損失可能在2.5 ~3 個月,存在1 個月左右的產能時間差。按照去年同期產量224 萬輛計算,今年湖北省大約損失40 萬~50 萬輛總產能,其中東風系大約損失30 萬~40 萬輛,“二汽”真的太不容易了!


產業鏈外遷之憂
在供應鏈端,老周對產能外遷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雖然湖北的疫情更為嚴重,生產恢復所需時間更長,但是湖北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湖北的供應鏈體系已經延伸至全國,甚至全球。
湖北之外的國內和國外車企,也正飽受供應鏈端復蘇的困擾。首當其沖的是海外汽車市場,尤其是對中國依賴度非常高的海外車企和零部件企業。
據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2018 年我國汽車零部件出口金額達到551.2 億美元。2019 年前三季度,汽車零部件出口金額達到351.17 億美元。
瑞銀集團的數據顯示,2019 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在全球汽車工業產量中所占的比例約為27%,在全球汽車零部件出口中所占的份額為8%。日本從中國進口的汽車零部件占到整體進口量的37%左右。在武漢,至少有1200 家汽車零部件制造企業。
中國供應鏈的中斷,已經引起日韓等國部分車企的減產和停產。通用、福特等美國車企,不惜成本空運中國零部件來救急。由于疫情的不確定性,部分車企開始尋求海外供應商的替代方案。
供應鏈對海外市場的沖擊引發了外界另一層擔憂,這波疫情會不會引發外資企業從中國市場外遷?以東南亞為代表的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市場,會不會以低價搶奪中國市場?
近年來,消費電子產業的外遷,尤其是向東南亞地區的外遷,一直牽動著國人敏感的神經。此次疫情對汽車供應鏈的沖擊難免加劇了外界的擔憂。
從企業供應鏈安全的角度考慮,的確有部分企業在當前疫情下尋求將武漢的產能轉移。
2020 年1 月,生產汽車底盤、懸掛裝置的日資零部件企業偉福科技宣布,將其在武漢工廠部分產能轉移至菲律賓工廠。如果疫情持續蔓延,不排除將更多在華產能轉走。
事實上,在全球多個區域有產能布局的企業,在特殊時期通過協調各區域產能以應對供應鏈問題,是正常的應急處理方式。企業為了供應鏈安全采用多區域布局無可厚非。
但是跨國產能的外遷,并不容易,更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做出的決定。對企業而言,將產能外遷需要考慮諸多因素,并且具備諸多條件,比如異地是否有現實產能和市場,以及重塑供應鏈體系需要時間和資金投入等。
難以替代的中國優勢
供應鏈的關鍵在“鏈”,包括交通鏈、資金鏈、人才鏈、文化鏈、科技鏈。而且,鏈條本身的健壯程度也很重要。疫情雖然讓個別企業重新調整了全球產能布局,但是中國汽車供應鏈的強大在于每個鏈條上都有一定的優勢,這些優勢是海外市場難以替代的。
中國汽車供應鏈的第一大優勢就是供應鏈網絡的完備性,以及對供應鏈上下游產生的強大黏性。
中國的供應鏈已經形成一個高度復雜的網絡,當一個個鏈條形成網狀的網絡,節點和用戶越多,節點與節點之間的組合創新能力就越強,運作效率和應變能力也越高,對用戶的黏性越強。
舉個例子,大家每月去超市集中購物時,總是喜歡去沃爾瑪之類的大型超市。因為大型超市里商品齊全,一次就能買到所有的物資,價格還更便宜。而在中國的汽車供應鏈體系中,你能很快找到任何你想要的原料以及合作伙伴,并以十分高效且低廉的方式,迅速完成供應鏈的布局。中國的汽車供應商種類和數量都很龐大,供應商之間的切換和組合更多,供應鏈整體的彈性更強。和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和成本以及基建速度和政策依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這些優勢對跨國車企而言是難以拒絕的。
中國汽車供應鏈的第二個優勢,是坐擁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也是全球唯一的2000 萬輛級市場,本土供應鏈非常健壯。
2000 萬輛級的汽車市場,創造的需求是海量且穩定的。很多跨國企業最初在中國投資正是看中了爆發中的中國市場。相比手機等消費電子產品,汽車供應鏈由于涉及零件種類繁多,零件的物理重量和體積大,零件需求批次多,準時性要求高,因此對供應鏈的運輸成本非常敏感。跨國車企選擇在一個地方設辦工廠,不僅要考慮自身的經營問題,還要說服和協助其供應鏈上的關鍵企業一同搬遷。汽車供應鏈具有了極強的集群效應。
尤其是武漢地區。當年本田與東風在武漢合資,與本田關系深厚的眾多日系供應商一呼百應,紛紛來華。
隨著中國汽車市場的持續爆發,主機廠和供應商的產能在不斷擴張。當整個體系開始高效運轉之后,精明的全球供應商們發現,完全可以利用中國市場的現有產能和條件,通過共線生產,大幅降低制造成本,實現海外供貨。這正是中國汽車供應鏈能夠持續對外輸出的原因。在強大的內需帶領下,供應鏈的產業集群效應正在凸顯,生產端穩定且低價。
除了集群帶來的成本優勢,中國汽車供應鏈潛在的第三大優勢就是人才鏈——大量“物美價廉”的工程師資源。
和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相似,東南亞目前承接的是低價值的過程裝配和半成品加工。長期來看,中國已經失去了和東南亞比拼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作為一個正在向發達國家不斷邁進的大國,中國也不再需要和東南亞比“蠻力”,拼的是內力,是智力。低價值、低成本、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外遷,有助于倒逼中國企業和政策向技術含量更高的價值鏈升級。
當前,對中國汽車產業大而不強、沒有核心技術的埋怨不絕于耳。但是歷史的發展總有其規律,需要過程和時間,不能求全責備。在過去的30 年,中國汽車供應鏈完成了“大而全”的布局,這一過程中勞動力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優勢居功至偉。現在,第一階段的完備性建設已經逐漸完成其歷史使命,第二階段的任務是向“大而強”發展。這是一個更為艱巨的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我們必須拋棄低價值、高污染、高消耗的產業。東南亞承接的更多的是某個生產環節的轉移,本質上是中國汽車供應鏈網絡的對外延伸。中國當前最亟需的是利用好龐大的工程師資源,大力投入研發,幫助中國的汽車產業,乃至現代制造業完成升級。

工程師是創新的源頭。和東南亞相比,我國有數量極為龐大的優質工程師團隊。從1999 年起,中國大陸開啟高校擴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迅速上漲。到2015 年,全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達到了1.71 億,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俄羅斯的總人口,可以排在世界第八。
這些豐富的智力資源是我們國家幾代人的家底,也是其他國家,尤其是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難以追趕的優勢。當年德國和日本的跨國巨頭們在中國大量辦廠,誕生出“國外負責創新、中國負責生產”的模式。但是國外企業通過對核心技術的牢牢把控,并不影響其在中國賺取巨額利潤和外匯。能輕易被遷走的產能,不是真正核心的產能,遷不走的產能才是核心資產。
中國還有一個優勢是,電動化和智能化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
智能電動車的興起給了中國切換賽道的歷史機遇。在電動化和智能化賽道上,中國和海外的起步時間差距不大。這意味著國外靠歷史積淀形成的技術壁壘更小。
以寧德時代和比亞迪為代表的動力電池產業,與日韓一眾電池廠齊頭并進。這與中外在傳統發動機和變速器領域的差距有天壤之別。
蘋果的成功帶來了移動互聯網行業的興起,中外在同一起跑線上起步,憑借著全球第一的市場和海量的IT 程序員資源,中國的移動互聯產業幾乎和美國并駕齊驅。在未來,智能化產業在汽車產業結構中的價值比例越來越高。
特斯拉的火速入華猶如當年的蘋果,具有極強的示范效應和產業引領作用。當大眾CEO 迪斯要將大眾汽車轉變為一家軟件公司,并滿歐洲找程序員時,中國市場的程序員將展現出本土集團軍作戰的優勢。在本土市場幾乎沒有輸過的中國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這個重要的市場上勝算更大。在本土市場上打敗所有對手,是中國互聯網信息技術公司和IT 程序員們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汽車產業的機會。
武漢,除了擁有強大的汽車產業集群,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還擁有僅次于北京、上海的優質大學資源,在人才引進方面力度空前。武漢的光谷和半導體等新興信息科技行業正在形成規模優勢。在未來智能化的賽道上,武漢擁有更廣闊的施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