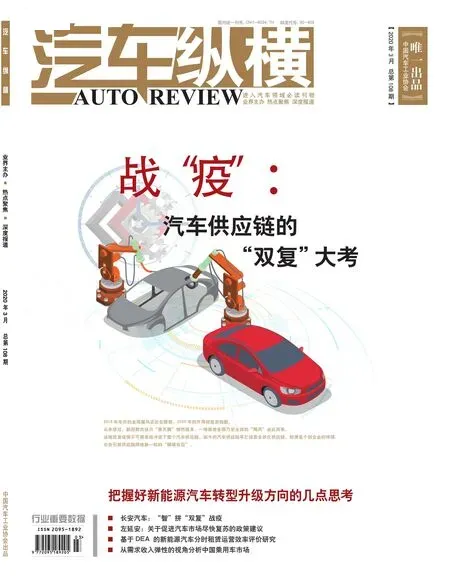“雙復”大闖關
——從動力電池領域看產業鏈的焦慮與自救
特約作者/《建約車評》 陸鑫
全國生產類企業節后復工要過三個關,首先是當地政府的復工批準,其次是防護物資要到位,最后是大量的外地員工還需要完成返崗。這三關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來說,關關都是挑戰,大多數企業采取的方式是“等”。疫情導致的大面積延期開工,讓整個產業鏈在這一時期的正常運轉受到影響。在動力電池行業優質供給本就不多的情況下,供應的問題雪上加霜。
開工百態
2 月11 日,在國內企業剛剛陸續開工之際,遠在歐洲的捷豹I-Pace 卻被曝出因LG 化學電池供應短缺,將從2 月17 日開始暫停I-Pace 的生產一周。另據韓媒報道,保時捷Taycan 近期向LG 化學訂購了6000 輛車的電池,但僅收到了3000 輛的。
特斯拉和松下也一度因為電池產能問題鬧得不太愉快,后來又在中國引入LG 化學、寧德時代,試圖通過三家供應商來滿足特斯拉產能以及低成本的野心。

優質電池產能的短缺已經成了世界性的難題。
不論是汽車新貴還是傳統巨頭,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人身上,紛紛與中國企業簽協議,下訂單。
受補貼政策驅動,國內動力電池產業也確實爭氣,不僅成長出了寧德時代這樣市值3000 多億的行業巨頭,還有上百家的上市公司,以及上千家的產業鏈上下游企業。
但時間進入到2020 年2 月,曾經熱鬧一片的生產場面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千廠開工的轟鳴聲被一片寂靜所替代。電池的供應雪上加霜,電池供應短缺仍然像緊箍咒一樣,緊緊地套在了各個主機廠的頭上,短時間內還摘不下去。
“韓國的客戶沒有停止生產,一直在跟我們催貨,但是我們現在開不了工,國際物流也沒恢復。”一家江蘇南通的正極材料商表示。
到2 月10 日,本該是很多工廠開工的日子,但事實上,汽車和電池供應鏈上的廣大中小公司還有很多沒開工。
“我們還在等通知,沒有得到批準不能開工。”地處江蘇的另外一家電池材料廠商負責人表示。“復工生產起來也快,但現在就算我可以生產了,其他人沒生產,物流也沒恢復,我也轉不起來。”該負責人繼續表示。
而此時,下游的電池廠商卻先轉了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國內排名靠前的動力電池廠商多數都在2 月10 日實現了開工。但已開工企業多數處于部分開工狀態,產能利用率尚處于較低水平。對于電池企業來說,低產能利用率就意味著高成本,就意味著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以及隨之而來的虧損。

這些對于整個產業的影響則更為深遠,因為原來預計的動力電池降價可能會更遲到來,電動車在2020 年的降本之戰也將更加艱難,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由于汽車和電池產業鏈較長,上游供應極其復雜,搞不定上游供應,而僅自己開工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電池廠和主機廠的最終產能恢復水平,是依上游整體供應鏈的恢復水平決定。而像汽車這種擁有1 萬多個零部件的產品,缺少一個零部件,整個工廠就要停工。整個生產環節拼的是木桶效應,整體恢復效率由最短的那一塊木板決定。
北京奔馳已經做出了榜樣。
為了幫助供應鏈企業恢復生產,2月6 日,北京奔馳向天津市政府以及天津武清區發函,請求特批其在天津武清的19 家零配件供應商提前復工。
然而,也許Tier1 的復工之難可以靠一紙文書解決,那再上游的Tier2、Tier3、Tier4,還有更多中小供應商呢?
對于開不了工的中小廠商,不能生產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企業就面臨關張。大面積的關張會帶來供應鏈的雪崩效應,毛細血管的大面積阻塞最終也會影響到動脈的供血不暢。
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對于更靠近終端消費者的主機廠、Tier1、電池廠來說,僅僅算自己的小賬已經不能完成止損。他們還必須幫助鏈條上生存的廣大中小企業收復失地。同時,廣大中小企業主們作為這場抗爭的主力軍,必須完成自救。
對于大多數地方的中小企業來說,要想恢復生產,實現進賬,還需要先解決好三大問題。
疫情期的復工資質
各地方政府為了應對返工大潮,防止連日來的防疫工作功虧一簣,在企業復工層面,提出了各種要求。具體到執行層面,各地政府展現了不同的智慧。各地政策不一,大致分為下面幾種:
1、企業承諾書
例如,“江蘇泰州要簽署法人承諾書,要求外地返回員工需隔離14 天,并確保消毒、防護儲備充足,可滿足7~10 天使用才能開工。”江蘇泰州一電池回收企業負責人表示。
又如,上海奉賢區對于申請復工的生產企業,要求其除了遞交復工申請外,還需要提交復工方案、人員信息登記表、應對疫情預案措施以及填報開復工防疫事項承諾書,保證做到“9 個承諾”,包括承諾設立24 小時熱線電話;嚴格管控來自或經過重點疫區人員;具備口罩、消毒藥劑、體溫測量設備等防疫物資儲備;每天早晚上下班分2 次實施體溫測量并做好人員記錄;在廠區交通便利處設置至少1 個容納5-10 人的臨時隔離觀察點等。
2、“白名單”審批制
例如,杭州對于復工實行“白名單”企業制。2 月10 日起,杭州對全區符合復工條件的企業按“一企一方案”實行分類分片分時段申報,嚴格審批、有序復工。2 月9 日杭州市企業嚴格防控有序復工專班發布的復工情況顯示,29814 家企業提出復工申請,最后核準的是162 家,杭州西湖風景區、建委和交通局提出的復工申請,一家都沒有核準。
3、實地審查制
企業要想完成復工申請,除了遞交書面材料,有些地方還必須接受實地檢查。經查不符合條件的應立即督促整改,并及時將情況報告企業復工審批組。
4、其他制度
例如西安市2 月上旬明確了市級重點續建項目和規上工業企業開工必須要經過審批,確保沒有任何輸入和擴散的風險。而其他企業一律不得開工。從2月份的各種公開信息看,一些地處農村的企業,由于各村的防控規定各不一樣,復工要解決更多的問題。
復工資質的核準,很多地方政府按具體情況逐步排產,依次復工。動力電池廠商由于規模較大,基本都能拿到開工資質,但是他們的上游供應鏈還需等待能否復工的通知。如果每家廠商都像北京奔馳一樣給地方政府去函,地方政府也會不堪其擾。
小規模調查顯示,一些規模較大的供應鏈企業已經在2 月10 日左右陸續實現開工,而一些規模較小的廠商還處于等待審批狀態。而大多數未得到批復的企業主的心態是“等”。
2 月11 日,發改委相關領導明確表態,當前形勢下需要兩條線作戰,除了抗疫前線,“另一條線”就是經濟發展前線,主要任務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降低疫情帶來的影響,特別是要為抗擊疫情前線提供充足的“武器”和“彈藥”。并將嚴格制止以審批等簡單粗暴方式限制企業復工復產的做法。
錯峰返程與錯峰返工的目標已經逐漸在實現,隨著地方政策走向平穩,中小企業要邁出這復工復產的第一步,僅僅是時間問題。
復工必備的防疫物資
疫情爆發之初,大多數的人可能還沒來得及做出類似的決策,就已經出現了口罩荒。
2020 年的頭幾個月,全民帶口罩和一罩難求已經是國民記憶中最深刻的部分之一。
口罩的短缺讓每一個需要外出的人感到焦慮。囤積口罩對于個人來說,是安全感的需要。對于企業來說,是復工的必備條件。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開工規定中,要求開工企業必須準備夠7 ~10 日的每人每天兩個口罩,方能開工。
對于鋰電產業鏈來說,由于作業情況特殊,多數企業是存儲有一定數量的防護物品的,但那點庫存物資在疫情面前是不夠的。
在這一時期迅速搞定口罩對于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類企業來說,太難了。
根據工信部此前提供的數據顯示,疫情之前我國口罩最大產能是每天2000 多萬只。疫情發生后,受生產廠商春節停產影響,口罩產能受到了較大的限制,而口罩不屬于普通消費者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在藥店內都不屬于大宗儲備商品,庫存有限。疫情爆發后,不少消費者哄搶口罩導致口罩庫存進一步告急。
隨著全國各地陸續開始復工,人員流動增大,原有口罩企業的那點產量和巨大的需求相比,遠遠處于供不應求狀態。再加上前線醫療資源吃緊,國家緊急征用企業的口罩,企業復工準備口罩的難度加大。
口罩成為企業復工行動中最緊缺的戰略物資之一。大多數企業很難有底氣地說口罩已經準備充分。采購口罩對于企業的行政采購等部門,是個不小的挑戰。各種群里、朋友圈、網絡上充斥著求購信息。拼人情、拼關系,可能最后還是解決不了口罩的問題。
正規3M 口罩一度漲到70 ~100元/個。不僅是朋友圈中的口罩價格驚人,就連在源頭的采購價都已經達到不能讓人接受的程度。據報道,年前3元一只的韓國口罩(采購價)在2 月下旬已經漲到了20 ~25 元/只,有的甚至達到48 元/只,而且每個小時可能都在變。
制造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按照當下疫情,操作規范的生產現場,每人每天要消耗2 個口罩。很多企業不僅采購無門,采購成本也吃不消。
好消息是,口罩的需求缺口上出現了很多跨界生產的熟悉身影。
上汽通用五菱、比亞迪、廣汽等廠商紛紛抽出部分場地,利用自身業務優勢,建設口罩以及其他防護用品生產產能。
在醫用口罩生產過程中,對生產環境有無塵、恒溫恒濕等要求,而汽車行業的部分汽車電子行業本身就具有很多無塵車間、防靜電車間,車企生產中的“涂裝車間”對“無塵環境”要求極為苛刻,可以滿足口罩生產要求。
而對于上游的廣大供應鏈企業來說,下游的車企客戶們已經紛紛開始布局口罩產能,這無疑會給他們的復工增強信心。
雖然口罩荒給中小企業的開工帶來不小的影響,但以中國世界工廠的能力以及政府、企業集中突破口罩等防護物資的產能,口罩危機很快度過。
口罩對于大多數的中小企業來說,還是“等”的問題。
除了口罩,測溫槍也是企業復工的搶手貨。疫情發生后,很多社區、公共場所門口都安排了專人使用測溫槍測量通過者的體溫。隨著企業的復工,市場對測溫槍的需求激增。
這也使得測溫槍這種原本稍顯冷門的產品,一下子成了復工關注的焦點。
原本BOM 成本不過三五十元,零售價不過百元的測溫槍,疫情期間售價動輒數百。即使以這個價格,在正規渠道,買到現貨難度很大,缺貨是常態。而朋友圈等臨時購買渠道,關于購買測溫槍的各種詐騙新聞也層出不窮。測溫槍參次不齊的質量,以及測溫槍測不準鬧出來的笑話,就更不必說。
一桿小小的測溫槍,對企業采購人員而言也是不小的難題。企業要正常復工復產,配齊基礎防疫物資必不可少。
復工必須的人、物流動
當前復工最大的問題是人員的到崗問題。在鋰電企業聚集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地,主要生產從業人員多來源于內地各省份。而本次除了湖北省之外,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勞務輸出大省也受疫情影響較大。生產企業的年后招工本就是一年比一年更難,再加上今年的疫情,人員返工更是雪上加霜。
在一些農村地區,村村封路,跨村通行都成了難題。更不要說公交停運、省際客車停運,高速非本地牌照下不去等各地臨時不同的情況。這些人員限流措施,在防控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跨省返崗。
同時,各回流重點區域對人口流入也采取了非常嚴格的限制措施。例如,“無錫發布”公布的政策,是將來自湖北、浙江、廣東、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七省的人員一律勸返。非七省人員,要在本地有身份證件、暫住登記或是有自主住房等條件的人才能進入。無錫的情況較為特殊,不具有可比性。而在其他地區,對于回城人員,一致的規則是應按規定接受為期14 天的隔離觀察。
由于人員回流難度大,也影響到回流意愿,2 月10 日在一些地方就成了名義開工日期,當地大多數企業并沒有完成開工所需要的足夠準備。再加上鋰電行業比較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中部地區都受疫情影響較大,開工更是難上加難。即使已經開工的企業,當時的到崗率還遠達不到正常水平。
開工的企業在節后復工的第一件事,也是先把防疫工作落實。復工之后要做員工回流統計、員工健康排查、人員診斷隔離、廠區消毒、防護用品籌備等工作。一旦工廠里出現感染,不但工廠面臨停工消毒,同期工人也都要隔離觀察。執行上的細節來不得半點馬虎。保持作業人員之間的距離,在公司食堂的餐桌加隔板或一人一桌,這些也都是基本操作。


但這些工作并不具備生產力。
復工的另一個阻礙就是物流以及運輸的不暢。
鋰電行業產業鏈長,需要上下游企業通力協作完成生產。即使個別企業復工,但產業鏈上游的原材料供應也未必能保證,再加上物流渠道的中斷,導致企業難以真正開工。
而下游的主機廠、電池廠等客戶,受物流阻斷影響,一方面要和供應鏈企業負擔巨大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也要一起捱過被物流耽誤的時間成本。
對于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相對于開工資質和口罩等硬性門檻,人、貨流動的彈性要大很多。不能讓人貨流動起來的更多問題是出在企業的信心層面。有交付壓力和對未來有信心的企業會想盡一切辦法,讓人和貨快速運轉起來。
而信念較弱的企業則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當下就是哪哪都轉不動,沒有辦法,繼續“等”吧。恰恰這種“等”的心理是最要不得的,隨著“等”,流逝的是企業的生命力和員工對于復工的信心,還有客戶。
經歷過非典的眉州東坡老板王剛在面對此次疫情時表示,“如果你把員工都放回去了,連續幾個月都開不了張,這支隊伍就散了。所以我說人在精神在,人在軍心在。”他的信念是“不管多難,都絕不等死。”
評論
前段時間,在西貝的“現金流只夠撐住3 個月”的熱點下,不少企業開始關起門來算自己還能活幾個月,結果算來算去發現,3 個月還算不錯的。
在新能源汽車行業,受補貼退坡和車企壓力轉移影響,應收賬款成了二線動力電池廠商和上游材料廠商的噩夢,一家廠商的高管在復工之后的會議上反問,“我們能給員工發應收賬款嗎?”
再加上,韓國廠商在面板、半導體兩次逆勢加產能戰勝日本廠商的殷鑒尤未遠,不禁讓人背后發涼。據韓媒報道,連韓國的后進廠商SK 創新都開始準備研發NCM9/0.5/0.5 體系了。而中國的廠商受疫情影響,研發節奏被打亂,能否在2020 年還繼續保持領先是行業不得不開始思考的問題。
而要想保住中國新能源行業來之不易的優勢,首先要保住這個產業的基本盤,這個基本盤不是抗風險能力較強的頭部廠商們,而是廣大的供應鏈企業,這些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
在這場廣大中小企業的生存之戰中,“等”是個最讓人無奈的詞,它既可以說是企業應對風險的穩妥之舉,又可以成為逃避現實的托詞。“等”來的可能是更大的機會和市場,也可能真就是倒閉。
而置身于事中的我們,可以選擇以更積極的心態去面對。有兩個詞比“等”更適合來應對這場危機。
面對當下,以“防”為主
防疫情,防風險。
在防控條件下完成復工,已經成了企業的必備生產技能。企業需要的是科學防控,避免過度焦慮。相對社會的群防群控,企業內部的防控是相對可控的。為什么在社會上會出現大量的瞞報新聞?是因為人在社會中的權利與義務并不對等,很難通過權利義務關系去約束每一個人。
而在企業與員工的雇傭關系下,瞞報行為相對來說,會因為權利與義務對等的關系,受到抑制。對企業瞞報的代價,企業是有辦法快速落實的。
所以,企業在摸排員工情況時,既不需要過分恐慌,但同時也要把工作做到細致。
雖然多數企業在防控工作上沒有經驗,但由于鋰電企業多數對無塵環境有要求,相信經過科學的培訓,企業是有能力實現自治防控的。
防風險,防的是企業猝死的風險。
這段時間,各家企業都在反復算賬,自己的錢還能撐多久,應該怎么花。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再定位,相信每家企業心里的賬目都會非常清楚。一季度本來就是制造業的淡季,相信也不會有企業對一季度抱有太多的幻想,這種本來就不高的預期,恰恰可以保護企業穿越低谷。
只要不是“猝死”這種非戰斗減員,應對接下來的挑戰是可以“強身健體”的。
面對未來,以“調”為主
在當前形勢下,所有的企業和個人都需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調整自己的目標,年前定下的個人目標和企業目標,都需要根據新的形勢做出修改。心態上的調整也很重要,去年加了產線,想要大干一場,今年只想活著。這種心態不丟人,反而更務實。
現金流和利潤想要哪一個?該做出調整了。須知,在調整心態和預期之后,人和組織的潛力都是無窮的。
積極的心態可以讓人更全面地審視這一次危機。就像丘吉爾說的“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
大多數企業是沒有機會經歷周期的,而只有周期才能錘煉偉大的企業。
在疫情的壓力之下,更容易看清一個人和一家公司的底色,這時候也是企業價值觀和個人品質真正外露的時候,平常很少有機會能讓大家互相觀察的這么清楚。
而在疫情結束之后,人員的流動一定會特別大,那這時候,無論對于個人還是企業都是很好的重新再選擇的機會。
同時,這也是企業重塑價值觀、錘煉團隊的好機會。墻上張貼的那些口號在當下更容易被檢驗,而能在當下環境突出重圍,則會使得團隊面對未來更加自信。
之前一直在推進的自動化、智能工廠到底是不是雞肋?這一次可以拿出來檢驗一下了。
而對于上下游的供應商、客戶來說,這次同樣也是壓力測試。平常大家不是互相都想探個底嗎?這次真的到底了,珍惜機會吧。
對于一些經營狀態較好的企業來說,這一次有機會低價收購優質資產,最好的投資機會到了。
而危機一定會造成更多的企業掉隊,而“肉身”隕滅的企業,它的優秀員工、優秀客戶這次可能為你所用,前提是活下來的是你。
梅花創投創始人吳世春在評價這場危機時表示,“在所有組織里,企業是最脆弱的。因為一旦員工拿不到工資,軍心不穩,整個團隊就會很快喪失戰斗力。所以,相比國家還能繼續收稅,家庭還能繼續還債,中小企業是當下最容易受傷的一個群體。”
這場戰役拯救的不僅僅是肉身,還是一個個無形的組織。在這場戰斗中也沒有救兵,每個人必須學會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