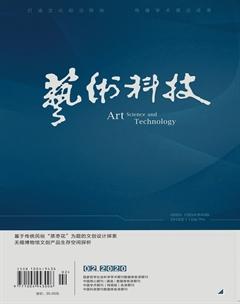高超靜遠
摘 要:徐渭花鳥畫的境界主要依靠豐富寬廣的文人畫基礎得以彰顯。在徐渭的花鳥畫中,不僅有前輩大師精華的積累,更重要的是他將花鳥畫拓展為一種心智的、超越再現的藝術,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心象。本文以徐渭晚年的作品《花果魚蟹圖卷》為切入點,體會徐渭暮年的藝術達到靜雅之氣的境界,并分別從筆墨之靜、物象之靜和格調之境來分析。
關鍵詞:徐渭;格調;境界;靜謐
清代的陶元藻可謂是懂徐渭的人,他在《越畫見聞》中寫道:“余竊謂文長筆墨,當以畫為第一,書次之,詩又次之,文居下,其書有縱筆太甚處,未免野狐禪,故易于偽作;至其畫高超靜遠,雖慧心人猝難模仿,是以一展卷而真贗了然,學步者無從躲閃。”陶元藻一語中的,說出了徐渭繪畫的藝術真諦——“高超靜遠”。[1]作《花果魚蟹圖卷》時,徐渭已是60歲的老人了。“從來壯士都無聊,一寄雄心于歌舞。”早年的癡狂與不幸已經過去,心態也逐漸趨于平和,性格上也慢慢沉靜下來。當下的他,寧愿做一片自由自在漂浮的行云,不受世俗所累。以前的舊相識都已經不在身邊,只是依稀記得他們的樣子,也是在說畫,也是在說人。在這幅畫卷中,我們更能體會徐渭暮年的藝術達到一定境界的靜雅之氣,分別體現在筆墨之靜和物象之靜兩個方面。
1 筆墨之靜
徐渭在《花果魚蟹圖卷》中描繪的物象不似早期的用筆潑辣,代之以輕柔的筆觸,稍有放逸的地方,也是偶爾為之,處處體現一個靜謐的世界。在這幅畫卷中,很多地方徐渭都以中鋒為之,筆勢凝重而又變化多端,樸茂酣暢,頗有含蓄的味道,突破了前期橫掃涂抹的用筆方式。[2]而此時徐渭在畫風上也開始刪繁存簡,以少勝多。在筆墨上,徐渭更是發揮了生紙滲化的效果,通過對毛筆中水分的控制,使筆墨出現更豐富的變化,這種變化濃淡干濕相間,空靈又極富節奏,意境古樸老拙,幽靜蕭遠。與八大山人的《荷花圖卷》相比較,我們就更能感受到這兩個經歷人生大起大落的藝術家晚年都追求的是靜逸的生命狀態。
繪畫作為色彩的藝術,用色最是體現玄機。但徐渭的水墨畫純用水墨而不設顏色,最能體現徐渭筆下的禪宗意蘊,體現筆墨的靜雅。徐渭繼承了文人畫的優秀傳統,以“水墨為上”,單純以墨色作畫。為了符合文人繪畫的特有審美——平淡天真,他將墨分五色發揮到最大限度,用其多種變化呈現出來的層次來象征性地表達客觀物象。徐渭在此畫卷中用單純的水墨塑造的物象簡練而生動,處處彰顯出生命的綻放,凝成了剎那即永恒的禪靜。此境亦是徐渭自己追求的人生境界,不是單純的技巧,也不是形式上的筆墨功夫。
徐渭繪畫的真正魅力就在他的筆墨運用當中,在于筆墨間表現出來的神韻,以及由此基礎上所展示出來的生命力。中國繪畫中使用的毛筆很容易體現所畫的線條和筆觸中的韻律和節奏。徐渭通過草書的練習極大地豐富了線條的質量和線形的變化。在各種書體中,草書的筆法最為豐富,有中鋒、側鋒、方筆、圓筆、藏筆、露筆、提筆、按筆等,是各種書體中集筆法之大成者。草書癲狂的書寫狀態、放縱姿勢的書寫形式也是禪宗中按照自然的本性、尊重個人內心的覺悟。狂亂而不失禮法的點畫變化無窮,天馬行空又神韻無限。[3]
2 物象之靜
徐渭在此幅畫卷中描繪的物象沒有風霜雨雪的殘酷打擊,只是按照自身的生長規律展示自己最美麗的時節,也許徐渭此時對世間不平的事看得多了,也看得比較淡了,此時繪畫對于徐渭而言,既不是謀生的手段,也非借物抒懷,就是簡單的畫。尤其是一尾不知名的小魚更是體現了這幅畫卷的大美,“以物寓意”,體現了文人畫的一個明顯的特點,也是成就徐渭繪畫的一個最重要的標志。與早期人生理想不一樣的是,徐渭現在已經不會盲目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不是時刻想著“上天河”,而是慢慢學會享受人生的一些樂趣。
藝術發展的規律正如唐代書法家孫過庭描述的那樣:“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險絕既立,復歸平正。通會之際,人書俱老。”繪畫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清代的蔣和說:“孫過庭謂學書有三時,余以學畫亦然。初學時當求平直,不使偏跛邪僻,以就規矩;不令濃膩涂飾,以求骨干。中則開拓其心思,以盡丘壑之變;遍尋其作法,以備材料之資。然必因前古所有而擴充之,不當師心倍理也。后則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矣。舉向者之所博涉而遠騖者,一約之于樸實簡易之中。似淡也,味之而愈長;似淺也,求之而愈深。功夫至此,則已顛毛種種矣。”這就是古人對于藝術規律的認識,徐渭從“絢爛之極”歸于“平淡”,這也是他所達到的人畫俱老的境界。[4]
在創作中,靜雅之美體現了藝術的最高境界。正所謂“精神到處文章老,學問深時意氣平”的境界。古人認為:畫中靜氣最難,骨法顯靈則不靜,筆意躁動則不靜,全要脫盡縱橫習氣,無半點喧熱態,自有一種融合閑適之趣浮動丘壑間,正非可以躁心從事也。“筆意躁動”和“縱橫習氣”被認為是達到靜氣最大的兩個障礙因素,而此時的徐渭用筆老道成熟,不激不厲,靜在其中。所謂靜則雅,躁則俗。作畫者,俗不去,則雅不來。此中的和雅,是和畫家本身的修為密不可分的,神恬氣靜,此時的徐渭無欲無求,達到這樣的境界是藝術的必然結果。而徐渭成就最高的水墨寫意,掌握這種雅和俗的分寸就十分不易。因為“寫意畫最易入作家氣。凡紛披大筆,先須格于雅正,靜氣運神,毋使力出鋒鍔,有霸悍之氣。若即若離,毋拘繩墨,有俗惡之目”。中國古典花鳥畫追求象外之意,觀其真形而融匯于心,然后以書法的筆法、縱橫的點線揮灑出自然的生命神韻。這種觀念源于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的“游于藝”的儒家哲學。
3 格調之靜
中國藝術創造出的靜謐意象,其寂靜的境界超越了時間,使觀者在雅靜的環境中感受到永恒的魅力。這也是文人畫所追求的格調。在中國的哲學觀念中,極動之中必定孕育著極靜,而大多數藝術家對靜的追求大多表現在山水畫中,對著青山流水似乎更能表達這種感覺。明代吳門山水大家沈周在詩中這樣寫道:“碧嶂遙隱現,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靜自太古。”在詩中,詩人把出世瀟灑的情懷描寫得恬淡靜雅,極富文人情趣。[5]
追求靜的傳統,中國繪畫歷來有之,而且在這方面積淀了相當深厚的理論基礎。惲南田就曾說:“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惲南田在藝術中極力追求靜雅的境界,為此他“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并且認為“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即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表達對繪畫格調中靜的追求。徐渭畫中體現出來的靜不僅和外在世界的喧囂形成對比,在靜中也包含著對世俗事務的淡薄,在保持靈魂的高傲獨立之外,達到“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境界。這也是文人畫的最高境界,也是徐渭對明末花鳥畫在境界開拓上的一大貢獻。
4 結語
徐渭是中國藝術史上少有的苦難天才,正如唐寅詩中寫的“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表達一個在封建禮法約束下以避害保身的知識分子形象。癲狂、不拘禮法是徐渭率真的一面,但是晚明的環境卻不容許社會個人有半點的逾越。但歸根結底,徐渭作為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的文人,骨子里還是渴望正常人的安逸生活。新時代下,我們回頭看晚明徐渭的繪畫藝術,是出于后輩對其高貴心靈的景仰,更是出于我們對未來前景的展望。500年前的徐渭借助走筆如飛的勾畫、酣暢淋漓的潑墨,獨具一格地將人生境界與藝術境界合為一體,使人生境界升華為一個璀璨的藝術境界,而藝術境界又展示出一個充實的人生境界。徐渭花鳥畫的最高境界在于其“永恒性”,“高超靜遠”直指文人畫的審美意趣,創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心象。將繪畫的模仿自然表現外部提高到表現畫家本人精神世界的高度,是畫家自我精神的覺醒,解放自我,發現自我,尊重自我,打破中國花鳥畫長期以來的寫實主義藩籬,成為精神的藝術寄托的集中體現。
參考文獻:
[1] 錢倉水.中國蟹畫的歷史考述[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8(05):643-648+700.
[2] 汪沛.徐渭文化心態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07:22-23.
[3] 李普文.嬉笑怒罵的抗爭精神——徐渭繪畫意象綜論之二[J].齊魯藝苑,2007(04):8-12.
[4] 李陽.淺析徐渭的繪畫藝術風格[J].美術教育研究,2019(20):26-27.
[5] 鐘艷紅.徐渭大寫意水墨花鳥畫風格成因研究[D].揚州大學,2019:32-33.
作者簡介:付博(1984—),男,碩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畫筆墨意象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