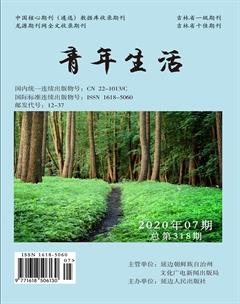論《漢書》對《史記》中公孫弘形象的改造
摘要:公孫弘在《史記》和《漢書》呈現著不同的面貌,前者使用了小說的筆法,而后者變得更為嚴肅、規整。在班固有意地安排下,通過增加公孫弘奏折、改變同傳人物、改變段落位置、突出“福禍速焉”的政治環境這幾種手段,成功地改變了司馬遷所塑造的公孫弘形象。班固對官員的這種回護式的感情傾向,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一以貫之的做法。
關鍵詞:公孫弘;《史記》;《漢書》;形象構建
以往史家,從傳統史學到現代史學,關于“史漢異同”的研究頗多,在不同層面不同視角已有可觀成果。公孫弘,在《史記》里,表現為一個典型的阿諛奉承的官場老油條的形象;而在《漢書》中相反,甚至表現出一個面對世界卻作了相當努力而終不成的無可奈何的可憐形象。關于這點,在司馬遷和班固的傳末的評價里表現得尤為明顯。前人已有論述,但重點放在二者形象不同的具體闡述上,或偏于司馬遷,或偏于班固,但沒有從書寫的筆法上進行探討。
不容忽視的是,班固所使用的材料與司馬遷相差無幾。從歷史書寫的角度便有一些問題:班固是通過何種手段來完成公孫弘形象的轉變呢?這種觀點的差別,前人往往歸結為班固時代經學意識形態確立,且往往以評價項羽的異同為代表,進而說明班固失去了司馬遷的勇氣和眼光。這固然不錯,但卻不盡如意。那么,具體到公孫弘身上,這種頗為相異的評價是普遍的嗎?產生這種原因,更為具體的是什么呢?
從《史記》、《漢書》兩篇公孫弘傳的記載來分析,撰寫與材料的鋪陳大約有以下不同。首先,在班固《漢書》中,和公孫弘同處一列傳的人為卜式和倪寬,取代了《史記》里主父偃的位置。主父偃之死,司馬遷記載說,公孫弘頗為出力。而本身來說,主父偃是“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的人,與司馬遷最為欽佩的魏公子以及諸游俠人物并不相同,總體上持貶斥態度。同時,《史記》中,這種形象往往充滿了“戲劇”或者“小說”色彩,與后世更為嚴肅的史學并不相同,尤其是班固對這種筆法作了相當程度的修改。在《漢書》里,卜式和倪寬卻是和公孫弘有頗為類似的地方。班固著重點明了這幾個人未入仕途時的困頓,把他們都放置于“漢之得人”的興盛上面,從而完成對漢王朝的歌頌和贊揚。
第二,班固在《漢書》中史料所異于《史記》的,在于增加了兩段公孫弘的奏疏。增加奏疏,好引文章,固然是整個《漢書》的特點。但考察此處,作為原始材料的奏疏,更是直接反應了公孫弘在政治中的所作所為。至少在這份奏折里,公孫弘遣詞造句恭敬而有理,說明了他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見識。盡管公孫弘最終位居宰相有著漢武帝的另一層考慮,但無論如何,這個奏疏作為通行證的作用,是不會被挑出什么大錯誤的。這樣,班固歷史記錄的色彩壓過了《史記》的小說色彩,顯得更加有根據且實際了。
第三,班固改變了司馬遷《史記》里鋪設材料的順序。在列傳里,人物的活動大體上是遵循時間順序,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物活動必須嚴格地按照時間順序來排列。最為典型的是頻繁使用的“初”、“時”字,這些詞句往往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是為了表達某種觀點或者感情傾向。以《公孫弘傳》的兩處不同來說明這點。
汲黯詰難公孫弘是很銳利的,并且是嚴重的罪名:對同僚兩面三刀、諂媚君王。但終究是沒有成功,兩書中均記載公孫弘以“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巧妙地化解質問:忠誠與否不在于別人怎么說,而在于君王的明智。他避開了汲黯背約的直接指責,將具體問題變成抽象的、沒有直接標準的隱藏的反問,正中漢武帝的下懷。司馬遷在此段后的是:
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這個寫法可謂是意味深長。而班固的在這個事件之后寫的司馬遷在此事前已經寫過的一條:
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后母孝謹,后母卒,服喪三年。
在心理學這門學科還沒有出現的時候,班固就已經使用了其中的一些手段了,同樣的夸獎或者詆毀,位置不同,表達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這里就充分顯示出來了班固的歷史編纂的傾向。很顯然,這兩種撰寫,表達出來是截然不同的好惡傾向。再看一條,公孫弘取得丞相位置后并以此終老,司馬遷筆下這樣: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馀歲,坐法失侯。
而《漢書》里則是:
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后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牦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牦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余盡伏誅云。
司馬遷強調了公孫弘蔭極子孫,而班固凸顯了丞相位置的危險性,前者是官僚的好處,暗含著某種做官的目的,是收獲,而后者是官僚的戰戰兢兢,是小心翼翼的付出。
通過這一系列步驟,班固在《漢書》里連著自己在列傳末的評價,成功地改變了《史記》里公孫弘的形象。類似于這種的評價并不少見,在平哀之際對官員的評價里,這種傾向尤其明顯,班固無比地寬容了幾乎所有——除了董賢和王莽以外——的官員,而其中不乏逢迎董賢、王莽的,也不乏危及皇權的。在“王商史丹傅喜傳”的論贊里,他可能是回答了最重要的原因:
自宜、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班固早年有入獄的經歷,以及班家祖上作為外戚的教訓,讓他對政治漩渦里面的人物都抱有一絲絲感同身受的哀憫。封建社會里,正如劉澤華強調過的,權力不僅支配社會,也支配者參與者的生死榮辱,這種人治下的政治危險的烙印,就很容易打在傳統史學家的思想里。班固首先是作為官僚而存在的,其次才是史學家,這是他對公孫弘持有這種與司馬遷截然相反態度的根本原因。
參考文獻:
[1]李靜.公孫弘在《史記》和《漢書》中的同與異[J].文學教育(上),2016.01
[2]曾小霞.《史記》《漢書》的敘述學及其研究史[D].蘇州大學,2012.
[3]朱維錚.班固與《漢書》——一則知人論世的考察[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6
作者簡介:趙巖松(1994— ),男,漢族,籍貫:山西臨猗,天津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