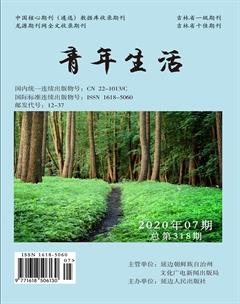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反思
摘要:浙江省出臺《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實施辦法》,發布當日即引發網友熱議,據此出發明晰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制度設立以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何以不受擁戴并提出適當反駁,進一步解讀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適用條件和適用現狀,從而嘗試展望完善芻議。
關鍵詞:犯罪記錄封存;未成年人犯罪狀況;制度解讀;適用實效;適用展望
1.引言
2019年12月9日,浙江省人民檢察院聯合浙江省委宣傳部、共青團浙江省委等12家單位,共同出臺了《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細化完善了刑訴法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該實施辦法一經發布即在網絡上引來了大量的討論,題為“浙江未成年人犯罪不歸入檔案”的標簽登上了新浪微博熱搜榜單,從標簽語義看,社會公眾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認識極其片面化,對其制度意義更是不明就里。而從網友的留言可見,公眾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態度不太友善,很多網友表示不支持未成年人犯罪不歸入檔案),閱讀評論可知不支持的理由主要有三點,部分網友出于對受害者的共情憐憫而表示反對,主要認為同態復仇方能彰顯正義,部分網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提出激烈反對,該類觀點主要認為隨著社會發展,民事責任能力的年齡界限尚有討論空間,未成年人的認知狀態已與成年人無異,未成年犯罪人應接受成年犯罪人同等程度的懲罰。此外還有部分網友對檔案封存后未成年人再犯罪概率表示擔憂。除此外,根據部分微博賬號發起的投票結果顯示,也有部分較為理智的網友對此提出了類似分級適用的概念,恰與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規則和立法原意不謀而合。
2.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意義再思考
2·1未成年人犯罪特點之更新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公布的《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之未成年人犯罪》中相關數據顯示,在2009-2017年間,未成年人犯罪率已經接連9年持續降低,其中2012-2017年間犯罪人數降幅較大,平均下降幅度高于12%。總的來說,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已位居世界最低水平。從罪名類型上講,未成年人最易犯盜竊罪、故意傷害罪和搶劫罪等輕罪。同時2017年全國法院新收案件中未成年人犯此類輕罪的比例較之2016年有所下降,但未成年人涉尋釁滋事罪、聚眾斗毆罪案件的比例較上一年有增幅。
在地域構成上,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北京等沿海地區和發達城市成為了外來未成年人犯罪高發地區,浙江、上海和北京是外來未成年人犯罪占比較高的三個省份。同時該部分地區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預防管理等措施也值得重點學習,譬如上海踐行未成年人法律保護工作30余年,積累了大量的寶貴經驗。
在年齡構成上,全國法院新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中初中生占比為68.08%。此外農村地區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占比為82.06%,表明農村地區未成年人犯罪率更高,農村未成年人預防犯罪工作也面臨更大的挑戰。對家庭環境的分析顯示,來自流動家庭、離異家庭、留守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的未成年人排名全國法院審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前五位,可見上述家庭中的相關因素嚴重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幾乎每一起惡性低齡犯罪案件的曝光都頻頻撩撥公眾脆弱的神經,引發對現行刑事法律政策的檢討風暴,認為其有對未成年犯罪人過度保護之嫌,輿情沸騰,如前述,網絡環境中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寬容度很低。實則綜合前述數據不難發現,因九年義務教育深入推進等多方面進步,未成年人犯罪率整體呈下降態勢,惡性低齡犯罪事件畢竟是極少數,低齡化、輕罪化、外來未成年人的犯罪高發區域構成以及多數未成年人的低層次文化水平的數據彰顯著未成年人犯罪不僅僅應歸責于其自身原因,更多的是家庭關愛缺失、學校教育失敗、周圍環境不良等諸多因素所致,其罪錯行為是反噬社會錯誤的必然惡果,折射的是時代病癥的殤痛。
2·2記錄封存對未成年犯罪人之保護
雖然目下未成年人的生理、心智成熟期大大提前,但未經成長的洗禮,未成年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尚未辯證統一,極易受激情沖動和外部環境影響走入違法犯罪的深淵。具有先導性、感染性、終身性等特點的家庭教育環境對未成年人成長影響卓著,譬如著名歌唱家之子李某某,同樣如前述數據,非常態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學校方面,“唯分數論”的教育評價體系下部分所謂的“雙差生”心理長期受挫,也具有極大犯罪可能性。社會方面,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文化沖擊著未成年人的心理發展,金錢至上的錯誤導向讓有些未成年人盲目追求物質享受,可能鋌而走險走上犯罪道路。
另一方面,未成年犯罪人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均明顯遠遠低于成年犯,且具有巨大的人格重塑空間,由此應貫徹保護性懲罰這一少年司法原則的基礎。若如輿論一般因極端個案輕易顛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過早任由犯罪記錄產生的“標簽效應”發酵,只會加劇反社會人格,所以應當特殊處理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弱化未成年人的犯罪“標簽”心理,權利,使得已經受到法律懲罰并誠心改過的罪犯再次融入正常社會生活。
2·3記錄封存降低對未成年人威懾作用之辯駁
從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出發,我國立法對一定范圍內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記錄予以封存,但是我國立法亦慮及社會利益保護和輿論環境下的未成年人保護和社會利益之間的矛盾加劇,將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予以部分“封存”,而非“銷毀”。且2017年12月國務院發布的《中國人權法治化保障的新進展》白皮書聲明:“近年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基本控制在1%-3%,未成年人罪犯數和犯罪案件數整體呈下降趨勢”,至少從整體上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并未導致未成年人再犯罪率上升,刑法的威懾效果并無減損。而關于多數反對者主要基于受害者的共情憐憫而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否定,筆者認為經定罪量刑后,施害的未成年人已經為其犯罪行為承擔了相應的法律責任,對刑法的震懾、預防和行為規制的功能沒有任何不利影響。
2·4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于政策之回應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對寬嚴相濟之刑事政策的積極響應。《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4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雙向保護”原則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一以貫之地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的懲戒基礎上重振未成年犯罪人,浙江省檢察院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16年浙江省檢察機關及時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以來,已有145名未成年犯罪人努力考上大學,重獲新生。
其次,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順應了國際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潮流和改革趨勢。譬如《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準則》第21條規定:“對少年犯的檔案應嚴格保密,不得讓第三方利用。”
3.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解讀
新刑訴法第275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3·1犯罪記錄封存適用對象之界定
在刑訴法有關規定的基礎上,部分地區適當細化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適用對象,除法律明確規定的未滿18周歲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外,還具體歸入了其他兩個類別:一是封存部分非犯罪記錄,主要包括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后被依法撤銷案件中止偵查的未成年人的記錄、未滿18周歲實施違法行為而被行政拘留的記錄以及被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未成年人的相關記錄。二是對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參與實施的犯罪案件記錄予以封存.至于具體這部分犯罪記錄如何封存尚且是司法實踐中亟待談論的難點之一。在溯及力上,明確規定新刑訴法出臺之前契合封存條件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也應當封存,同時還補充規定了相應期間被公安機關處以治安處罰、收容教養的未成年人違法記錄也是封存制度的適用對象之一,力求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權益。
3·2犯罪記錄封存內容之厘清
封存的內容為“犯罪記錄”,一是有關未成年人犯罪內容和刑事訴訟程序的信息;二是載明前述內容的載體,并對該犯罪檔案材料嚴格封存保密。根據“兩高三部”《意見》的有關規定,犯罪記錄涵攝范圍包括:犯罪人基本身份信息、關涉機關的名稱、判決書編號和日期、罪名、刑罰及刑罰執行情況。“可適用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案件,由法院制作《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告知函》,與生效裁判文書一并送達司法行政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案件電子信息同樣歸屬犯罪記錄封存犯罪,實行加設封存模塊或專門標注的的專門管理制度,未經合法授權不得查詢。
3·3犯罪記錄封存效力之簡析
犯罪記錄封存僅僅是保持相關犯罪記錄的封閉狀態和秘密性,與犯罪前科消滅存在本質區別,犯罪記錄封存例外的適用犯罪記錄查詢,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被封存時,有權查詢的特定單位在存在法定事由時可以遵循法律規定進入查詢程序。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裁判文書顯示當未成年時的犯罪記錄是再次犯罪后刑罰裁量的法定依據且對定罪量刑具有實質性的影響時,該犯罪記錄在相關文書中得以評價并記載;另表明部分地區的檢察機關選擇在舉證質證環節援引未成年人犯罪記錄,而法院不會將犯罪記錄作為從重處罰情節,僅作為背景材料對未成年人進行法庭教育。也有部分地區僅以封存的犯罪記錄審查羈押必要性。此外,封存持續有效。
4.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適用展望
“在2013年至2015年,全國檢察機關針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進行犯罪記錄封存的有12萬余人。”而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的統計數據,2013年至2015年全國法院審理的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總計有15-20萬人,因此,實施犯罪記錄封存的未成年人數大致占所有未成年被告人人數的80%。目前已有江蘇、廣東高院、北京、浙江檢察院等都已出臺相關配套實施細則。其中浙江新出臺的規定對封存適用條件、封存范圍和操作步驟、查詢程序及履行附隨保密義務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定,具有較強指導性,堪稱明燈。
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仍然存在“五年”標準過于機械化的問題,實行實效堪憂。實踐中往往出現犯罪嚴重程度以及社會危險性更低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反而不被封存,無法契合立法原意。另一方面封存記錄查詢主體過于寬泛,且對于已經予以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查詢申請及審批程序均未作出詳細的規定,亦未規定違反保密規定應承擔的責任及處罰。因此導致即使犯罪記錄已經封存,有前科的未成年人仍可能面臨嚴重的教育就業歧視,因用人單位獲知已封存的犯罪記錄而遭辭退的事件并不鮮見。
所以,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首先應當統一相關法律法規,通過相關司法解釋或專門性法律法規對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實施作出統一的具體規制,同時統一立法明確封存查詢主體,規范查詢程序,建立泄密追責機制;設立嚴格的查詢、審批、保密程序及泄密追責程序。實現有法可依,違法必究,改變各地實施細則各異的情形。
其次應該建立規范嚴格的實質性審查流程,擬定更為科學合理的適用標準。現行“五年”標準并不能較為準確的契合立法初衷,應封存主觀惡性小、社會危害性低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但綜合案情衡量后,確實主觀惡性大、社會危害嚴重、再犯幾率較大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也不應一律予以封存。
最后應在不斷探索中實現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和社會幫教制度、社區矯正制度的完美銜接,運用全社會力量配合互動防止交叉感染和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幫助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正常健康生活,從而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體現法治文明。
參考文獻:
[1]王貞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會支持機制研究[M].北京市: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7.
[2]計為民.低齡化犯罪倒逼立法與時俱進[J].人民之聲,2019(11).
[3]王新.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之核心概念及其功能[J].中國青年研究,2015(06).
[4]林維.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適用:基于檢察權的研究[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4(03).
[5]宋英輝,楊雯清.我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研究[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27(04).
作者簡介:劉義(1999.5—),女,四川省成都人,成都市雙流區四川大學訴訟法學專業 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