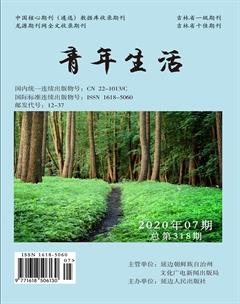中日民法對(duì)人格權(quán)保護(hù)的比較研究
吳天
摘要:人格權(quán)包含人格尊嚴(yán)、人格平等、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隱私權(quán)等權(quán)利,是人所享有的維護(hù)生存和發(fā)展的基本權(quán)利。人格權(quán)從羅馬法中萌芽,在法國(guó)、德國(guó)、日本瑞士等國(guó)民事立法中都有一些規(guī)定,而在人格權(quán)實(shí)際保護(hù)方面,法律實(shí)踐中的判例更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本文針對(duì)人格權(quán)的民法保護(hù)這一課題,結(jié)合目前民法學(xué)界的討論,試圖盡可能系統(tǒng)地考察日本民法對(duì)人格權(quán)保護(hù)的歷史、現(xiàn)狀、判例以及救濟(jì)途徑,在梳理我國(guó)現(xiàn)行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的基礎(chǔ)上,從中日比較的角度,嘗試性地提出改進(jìn)我國(guó)民法制度對(duì)人格權(quán)保護(hù)的構(gòu)建建議。
關(guān)鍵詞:人格權(quán);民法保護(hù);一般人格權(quán);立法體系
1.前言
人格權(quán)普遍被認(rèn)為起源于羅馬法。從歷史上看,人格權(quán)的概念是與自然權(quán)相連的,是人的根本權(quán)利,其他所有的權(quán)利都可看作由此派生的,羅馬法學(xué)家將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獨(dú)立的地位和形態(tài)概括為人格權(quán)。然而,羅馬法時(shí)期的人格權(quán)具有明顯的等級(jí)、歧視色彩,在文藝復(fù)興和啟蒙思潮之后逐漸被摒棄,格勞休斯的論述“人應(yīng)該享有特定的權(quán)利,這是源自人本身固有的屬性”被奉為近代民法上人格平等的依據(jù)。19世紀(jì)之后,各國(guó)民法向現(xiàn)代民法轉(zhuǎn)變,此時(shí),人格權(quán)的內(nèi)涵轉(zhuǎn)而側(cè)重于“法律人格的形式上的平等”。
2.人格權(quán)的概念和性質(zhì)
2.1人格權(quán)的概念
德國(guó)學(xué)者基爾克在《德國(guó)私法》中對(duì)人格權(quán)做出的定義為——“保障一個(gè)主體能夠支配自己人格必要組成部分的權(quán)利”,認(rèn)為具有多面性的人格權(quán)是包括身體權(quán)、名譽(yù)權(quán)、姓名權(quán)、個(gè)人形象權(quán)等多項(xiàng)權(quán)利的,這是人格權(quán)發(fā)展早期較為全面的論斷。我國(guó)民法同樣未對(duì)人格權(quán)做出定義,主要通過(guò)列舉的方式表述其包含的權(quán)利。對(duì)于人格權(quán)的定義,王利明教授認(rèn)為,人格權(quán)以保障主體的人身自由為重要目標(biāo),是主體本身依據(jù)法律所固有的,保護(hù)人格尊嚴(yán),維護(hù)人格平等,以人的各項(xiàng)利益為客體的權(quán)利。
綜上,本文認(rèn)為,人格權(quán)包括主體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名譽(yù)、隱私等多重利益,為民事主體所固有,與人、人格相始終,是主體自由發(fā)展的基本權(quán)利。
2.2人格權(quán)的性質(zhì)
人格權(quán)作為民事主體固有的權(quán)利,是絕對(duì)權(quán),具有排他性,效力及于不特定的任何人,在權(quán)利受到侵害時(shí),可以請(qǐng)求防止侵害或者排除侵害。人格權(quán)是專屬于某人的權(quán)利,人的人格權(quán)與自身的特點(diǎn)有緊密的聯(lián)系,該權(quán)利不依主體的意志而轉(zhuǎn)讓、繼承、拋棄。即使在商業(yè)行為中,權(quán)利主體“轉(zhuǎn)讓”部分人格權(quán),也只能是人格權(quán)的使用權(quán)而不是其所有權(quán)。
3.日本對(duì)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
日本初期的學(xué)說(shuō)、判例認(rèn)為,對(duì)于新出現(xiàn)的需要保護(hù)的人格利益,都應(yīng)該如
信用權(quán)、營(yíng)業(yè)權(quán)、貞操權(quán)一樣,確立具體的人格權(quán)法律條款來(lái)予以救濟(jì)。但是在1925年的“大學(xué)湯”案件以后,判例的立場(chǎng)發(fā)生變化,那就是侵權(quán)行為的成立,以有權(quán)利侵害發(fā)生為必要條件。而末川博的《權(quán)利侵害論》(1930年)之后,人格權(quán)概念遭到否定,以違法性取代權(quán)利侵害的學(xué)說(shuō)盛行,這對(duì)此后人格權(quán)的發(fā)展和保護(hù),確實(shí)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1964年,三島由紀(jì)夫在其作品《宴會(huì)之后》中塑造的小說(shuō)人物的原型,以隱私利益遭到侵犯為由向三島由紀(jì)夫及出版社提起訴訟,并得到支持和賠償。該判決肯定了隱私權(quán)是是一種可主張的人格利益,在受到侵犯時(shí)可主張法律救濟(jì)。即從該階段開始,人格權(quán)的概念已經(jīng)在判例中使用,以此為轉(zhuǎn)折點(diǎn),其后很多判例也都認(rèn)可了隱私權(quán)。
在當(dāng)前的日本,學(xué)界提出了《民法修正國(guó)民、司法界/學(xué)界有志案》和《債權(quán)法修正的基本方針》兩個(gè)具體的大幅度的民法修正提案,前者要求除了擔(dān)保法外,對(duì)財(cái)產(chǎn)法進(jìn)行全面修正,后者則提出對(duì)以合同為中心的債權(quán)法進(jìn)行修正。其中前者包含諸多人格權(quán)規(guī)定:“總則”篇第2條對(duì)規(guī)定了人格權(quán)相關(guān)的基本理論,于債權(quán)篇末尾的“不法行為”一章的“第1節(jié):損害賠償”、“第2節(jié):禁止等”中加入了幾條相關(guān)的規(guī)定。在損害賠償方面,也分別規(guī)定了針對(duì)生命和身體、身體自由、其他人格權(quán)三種不同級(jí)別的保護(hù),替換了過(guò)失證明,明確了過(guò)失責(zé)任。此外,其中還規(guī)定可以認(rèn)可賠償費(fèi)的相關(guān)請(qǐng)求,而對(duì)生命、身體以及身體自由進(jìn)行的侵害被明確禁止。
4.我國(guó)對(duì)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
目前,我國(guó)民事法律中對(duì)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體系包括法律及司法解釋,其中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等物質(zhì)性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始終處于核心地位,而具體人格權(quán)保護(hù)中所列舉的主要是與人的尊嚴(yán)相關(guān)的姓名權(quán)、榮譽(yù)權(quán)、名譽(yù)權(quán)等。人格權(quán)獨(dú)立成編進(jìn)一步完善了民法典的體系結(jié)構(gòu)。民法典體系是按照一定邏輯科學(xué)排列的制度和規(guī)則體系,它是成文法的典型形態(tài)。法典化就是體系化,大陸法系之所以稱為民法法系,就是因?yàn)樗悦穹ǖ錇榛緲?biāo)志。
民法典的體系包括形式體系(民法典的各編以及各編的制度、規(guī)則體系)和實(shí)質(zhì)體系(民法典的價(jià)值體系)。就形式體系而言,潘德克頓學(xué)派主張,以法律關(guān)系特別是以民事權(quán)利為中心來(lái)構(gòu)建民法體系,按照這一體例,人格權(quán)放在分則之中,也完全符合這個(gè)體系的內(nèi)在邏輯,但《德國(guó)民法典》的五編制體系并沒(méi)有規(guī)定人格權(quán),存在著“重物輕人”的體系缺陷。我國(guó)《民法總則》第2條在規(guī)定民法的調(diào)整對(duì)象時(shí),將民法的調(diào)整對(duì)象確定為人身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已經(jīng)在分則中分別獨(dú)立成編,表現(xiàn)為物權(quán)編、合同編;而人身關(guān)系主要分為兩大類,即人格關(guān)系和身份關(guān)系,身份關(guān)系將由婚姻編、繼承編予以調(diào)整。如果不設(shè)置獨(dú)立的人格權(quán)編,則民法典分則所調(diào)整的人身關(guān)系將僅限于身份關(guān)系,人格關(guān)系并未在分則中具體展開,這將導(dǎo)致民法典分編與民法總則規(guī)定之間的不協(xié)調(diào),也不符合民法典所應(yīng)調(diào)整的范圍。
人格權(quán)獨(dú)立成編是我國(guó)長(zhǎng)期以來(lái)民事立法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與《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的規(guī)定實(shí)質(zhì)上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基于對(duì)“文化大革命”期間嚴(yán)重侵害個(gè)人人格權(quán)、踐踏人格尊嚴(yán)現(xiàn)象的反思,《民法通則》以專章的形式規(guī)定民事權(quán)利,并明確規(guī)定了人身權(quán),具體列舉和規(guī)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各項(xiàng)人格權(quán),這是我國(guó)人權(quán)保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5.結(jié)語(yǔ)
人格權(quán)獨(dú)立成編是我國(guó)長(zhǎng)期以來(lái)民事立法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與《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的規(guī)定實(shí)質(zhì)上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基于對(duì)“文化大革命”期間嚴(yán)重侵害個(gè)人人格權(quán)、踐踏人格尊嚴(yán)現(xiàn)象的反思,《民法通則》以專章的形式規(guī)定民事權(quán)利,并明確規(guī)定了人身權(quán),具體列舉和規(guī)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各項(xiàng)人格權(quán),這是我國(guó)人權(quán)保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在當(dāng)前的日本,學(xué)界提出了《民法修正國(guó)民、司法界/學(xué)界有志案》和《債權(quán)法修正的基本方針》兩個(gè)具體的大幅度的民法修正提案,前者要求除了擔(dān)保法外,對(duì)財(cái)產(chǎn)法進(jìn)行全面修正,后者則提出對(duì)以合同為中心的債權(quán)法進(jìn)行修正。其中前者包含諸多人格權(quán)規(guī)定:“總則”篇第2條對(duì)規(guī)定了人格權(quán)相關(guān)的基本理論,于債權(quán)篇末尾的“不法行為”一章的“第1節(jié):損害賠償”、“第2節(jié):禁止等”中加入了幾條相關(guān)的規(guī)定。在損害賠償方面,也分別規(guī)定了針對(duì)生命和身體、身體自由、其他人格權(quán)三種不同級(jí)別的保護(hù),替換了過(guò)失證明,明確了過(guò)失責(zé)任。此外,其中還規(guī)定可以認(rèn)可賠償費(fèi)的相關(guān)請(qǐng)求,而對(duì)生命、身體以及身體自由進(jìn)行的侵害被明確禁止。
科技與社會(huì)文明進(jìn)步的同時(shí),人們關(guān)于人格權(quán)保護(hù)的意識(shí)不斷提高,尤其是伴隨著網(wǎng)絡(luò)和社會(huì)媒體的發(fā)展,人格權(quán)侵權(quán)案件增多,更是加強(qiáng)了人們對(duì)自身人格權(quán)益保護(hù)的要求。因此,完善人格權(quán)保護(hù)制度是時(shí)代的需要、社會(huì)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人格權(quán)保護(hù)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保護(hù)公民基本權(quán)益,使人格權(quán)侵犯案件的審判有法可依。其次,由于人格權(quán)在民事權(quán)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加強(qiáng)人格權(quán)保護(hù)有利于完善民事法律體系。
參考文獻(xiàn)
[1]五十嵐清著《人格權(quán)論》,一粒社,1989年版
[2]【德】漢斯·哈騰鮑爾著,孫憲忠譯《民法上的人》,載于《環(huán)球法律評(píng)論》,2001(4)
[3]曹險(xiǎn)峰,田園著《人格權(quán)法與中國(guó)民法典的制定》,載于《法制與社會(huì)發(fā)展》,2002(3)
[4]王澤鑒著《格權(quán)、慰撫金與法院造法》,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8版
[5]蘇長(zhǎng)江著《論人格權(quán)的三分法》,載于《經(jīng)濟(jì)研究導(dǎo)刊》,2009 (36)
[6]五十嵐清著《人格權(quán)法概說(shuō)》,有斐閣,2003年版
[7]王利明著《民法總則研究》,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
[8]王利明著《人格權(quán)法研究》,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