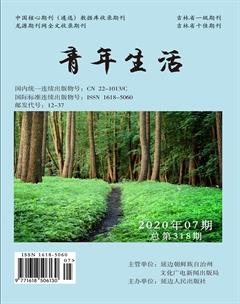淺析《海鷗》中烏托邦式的對
白江璐
契訶夫曾在一封書信中寫道:“人并不是每分鐘都在那兒談情說愛和開槍自殺的,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吃吃喝喝,來來去去,吊膀子,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蠢話。這一切應當在舞臺上表現出來,讓舞臺上的一切和生活里一樣復雜而又一樣簡單,人們吃飯,就是吃飯,可在這吃飯的檔兒,有些人走運了,有些人倒霉了。” 契訶夫善于用喜劇的外殼包裹悲劇的內核,使得高高在上的舞臺放大了人類的渺小與無助,很多時候幸福在形成而生活在斷裂,與瑣碎庸常的生活相對照的是人們沒事可做又沒完沒了的生存狀態,每個人都無所事事每個人又都高談闊論,日常生活的各種旁逸斜出導致了人們內心的焦慮與迷惘,表面上毫不相干無聊的對話實則蘊藏著無限的潛流。
眾人打牌,各說各話,像是獨立的個體懷揣各自心事臨時拼湊在一起。
阿爾卡基納:“在哈爾科夫我受到什么樣的歡迎啊!”
瑪莎:“三十四!”
阿爾卡基納:“那些大學生對我熱烈歡呼,三個花籃,兩個花環……當時我穿著一身漂亮得出奇的衣服。”
瑪莎:“五十!”
波琳娜:“科斯基在彈琴,他心里苦惱,這個可憐的人。”
瑪莎:“二十八!”
阿爾卡基娜旁若無人地夸耀自己當年在哈爾科夫演出受到熱烈歡迎的情景,回憶自己當年打扮得如何光鮮動人,意識完完全全沉浸在昔日的榮耀之中。瑪莎的生活依舊空虛痛苦,情感的無所寄托使得她一心一意玩牌消磨時光,所以她的話只有響亮而簡單的牌點數字。作為瑪莎的母親,波琳娜慈愛地關心著特里普列夫的心情變化,而索陵又如同以前一樣地睡著了,看來鄉間的生活的確讓他昏昏欲睡。特里果尼依舊表達著創作的痛苦和對創作的見解,表達著對自由美好的向往。多恩醫生評論特里普列夫的作品并加以贊賞,以出世的心態陪眾人做著入世的事。一切看似合理有序,卻在沉悶的氛圍里變得十分怪誕。人們彼此隔膜,缺乏順暢的交流,性格內化,因此他們的對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之為獨白,他們表達個人的心情和觀點,而其他人并不一定去接對方的話。當特里普列夫與特里果尼大談自己藝術創作的主張時,妮娜表達的是對作家的崇拜和追求成為杰出女演員的夢想,瑪莎被痛苦愛情拖累到失去生活的意義時,索陵則不忘嘮叨自己對鄉下生活的種種不滿和對生活的無限欲望。
德國文學理論家彼得·斯叢狄認為“這種自說自話的形式具有強烈的表現力,這一表現力的基礎在于,它與真實的對話之間存在著痛苦——戲仿式的對立,這種自說自話使得對白成為烏托邦。” 答非所問,自說自話,這使得契訶夫站在現代主義的門口,他筆下的人物又帶有那么一點點后現代派的味道,這使我們不禁想到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兩個流浪漢,還有尤內斯庫《禿頭歌女》中的史密斯夫婦,也是如此,只不過他們的形式與表現力更加突出而已。在《海鷗》中,每個人都講述著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不是講給別人聽而是講給自己聽。于是一群人聚會閑聊,吃飯打牌,他們總是那樣叨叨念念,只有小小的斗嘴而沒有嚴肅激烈的爭吵,沒有驚天動地扣人心弦的情節,也沒有高潮迭起令人拍案驚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經說過:“初讀《海鷗》常常令人失望,甚至覺得讀過以后,沒有什么可談的。故事?情節?只兩句話就可以概括了,角色呢,其中大多數是‘沒有線的小角色,一張紙便能寫完……。” 而且由于缺乏一個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識或者聲音的主導,每個角色的自我意識都居于主導地位,正是“這種自我意識的主導性使得人物具有了內在的自由和相對的獨立性。” [11]487 通過這樣的角色塑造,這樣的獨白呈現,契訶夫呈現了一種嶄新的敘述策略:“沒有所謂的沖突、危機和高潮,這無異提早實現了貝克特反戲劇的戲劇。” 美國著名劇作家尤金·奧尼爾曾指出:“沒有曲折的情節而又寫得最完美的劇本,是契訶夫的劇本”。
我們看到契訶夫接受生活是何等的糟糕并且跳出來,他讓筆下的人物來來去去吃吃喝喝,以一種熱鬧閑散的方式替代了呼天搶地的悲壯,通過自我暴露,獨白和諷刺等手法來塑造喜劇性角色,以烏托邦式對白營造了一種表面上的喜劇氛圍,這既是對悲痛的一種喜劇性表達,也是淡化悲劇性情節,有意制造的一種間離效果。對于特里普列夫的自殺,聽到一聲槍響后的多恩醫生只是故意輕描淡寫地說:“沒什么。一定是我藥箱子里什么東西爆炸了!” 這樣的嘲弄使特里普列夫的死變得毫無價值又帶有喜劇性質,緩解了悲傷的氣氛,讓我們覺得即使是死亡也沒什么大不了,死亡不再是最終解決方式和目的,不再是悲劇性的,但我們又會因為對死亡的輕描淡寫感到哀傷。情節的離奇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而對生活細節的真實刻畫和塑造各式各樣的典型角色,這才令我們著迷。所以我們看到《海鷗》中“喜劇性與諷刺性開始深入到作品的深處,與抒情性的、悲劇性的因素融合成一個強有力的藝術整體。”
在《海鷗》中,人物的烏托邦式對白在消解對話和溝通意義的同時,更多的是以這樣的一種形式展現現代主義區別于古典主義的悲喜相分,更多的是以喜劇的外殼包裹悲劇的內核,因為你無法判斷一個回憶往昔風采的半老徐娘是值得同情還是應遭唾棄,你也無法衡量一個斷送青春與純潔的苦情少婦當年選擇的對與錯。戲劇沖突內化,人物性格內化,獨白性展現為一種人與環境的沖突。生活不再是簡單的這個人物與那個人物過不去,而是一群人被環境和生活壓迫著,各說各話,各行各事。契訶夫面對沖突的態度與其說是調和,不如說是高談闊論地調侃,使得喜劇性獲得極大宣泄的同時悲劇性又在隱隱作痛。在面對慘淡人生的時候,是勇敢面對現實還是為自己建造一座理想的烏托邦,一個個人物生活和獨白的時刻為我們呈現出悲喜相融的微妙瞬間。
戲劇演出中心老百匯曾流行這樣一種說法:“戲劇就是有一個人要一樣東西。最后如果他要到了,就是喜劇,如果他要不到,就是悲劇。” 但在《海鷗》中得到者有時甚至比失去者更加痛苦,得不到特里普列夫的愛也許瑪莎還有一絲念想,得到特里果尼的愛卻讓阿爾卡基納患得患失。我們認為一個人極度高興和極度悲傷的狀態下所到達的那個程度是一致的,就是所謂忘我的狀態。《海鷗》中的人物是忘我的,所以對白變成了獨白,契訶夫也是忘我的,所以他用喜劇包裹了悲劇。悲劇性也好,喜劇性也罷,在契訶夫筆下都難以割裂開來,悲喜性就是真實忘我的狀態,就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對白和內化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