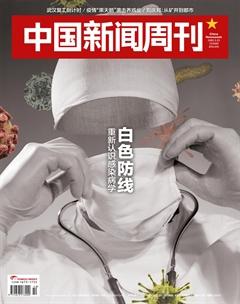埃里溫
曹然

“埃里溫階梯”頂層風光。近處是爛尾的階梯工程,左手邊可見衛國戰爭雕像,位于土耳其境內的亞拉拉特山在遠方若隱若現。
與其說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是一座都會,不如說這是一片分布在高低不等的小山坡上的居民點集合。
群山之間是呈標準圓形規劃的埃里溫老城。陽光明媚,綠樹成蔭,雕塑林立。三三兩兩的人們閑坐在長椅上,不時有鴿子踱過。除了舉目可見的以當地特有的火山巖為建材的紅磚大樓、波斯風格的立柱門廊以及遍布四處的十字架木雕外,這里的一切與西歐國家的古城無異。
老城周圍的山坡則是另一番圖景。有的密布現代化大樓和商超,有的是滿眼棚屋的貧民窟,最多的是典型的前蘇聯城區:寬闊的街道,實用主義和現代主義風格錯雜的破敗紅磚大樓。廢棄的蘇聯民航客機停在雪山映襯下的國際機場上,冒著黑煙、渾身顫抖的古董拉達小轎車擠滿街道。
從出租車司機到國會議員,我遇到的每一個埃里溫人都樂于向外來者介紹這座城市輝煌的過去與失落的近代。在老城集市,一位攤主看我專注挑選蘇聯時期的舊物,主動送上一枚埃里溫建城2500年時鑄造的紀念徽章——這座城市曾出現在人類文明最早的版圖上。
我跟著向導瑪麗探訪了埃里溫城郊的教堂群。這些教堂由火山巖壘成,內部陰森幽暗。作為一位虔誠的教徒,瑪麗每見到一位教士都要迎上去求賜福。

埃里溫西郊的教堂廢墟。在1988年的大地震后,人們突然發現了這片遺址。
公元301年,基督教圣徒格里高利說服當時的亞美尼亞國王特拉達三世,建立了世界第一個基督教國教會。今天,亞美尼亞教會依然是不屬于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的基督教獨立分支。
我們拜訪教堂時,國教會最高領袖大教長正在布道。儀式混亂而熱鬧。不大的中庭里,大教長穿梭于擁擠的人群中,信徒簇擁著他,撫摸他身體上下的所有裝飾物,據說這可以帶來好運。三三兩兩的外國游客夾雜其間,圍觀拍照,來去匆匆,沒有人阻攔,也沒有人覺得不禮貌。
長居埃里溫的伊朗記者帕沙告訴我,他曾在埃里溫國立大學選修歷史課,卻發現在這個國家最優秀的歷史學家的敘事里,多災多難的亞美尼亞似乎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帝國。
“我知道中華帝國、羅馬帝國,亞美尼亞怎么也是帝國了?”在反復提出質疑后,帕沙被告知最好不要再來旁聽了。后來他得知,在后來的課程里,同樣擁有古老文明的伊朗也被那位教授劃進了古亞美尼亞帝國的疆域。
我能理解當地人對帝國敘事的執著。這是一座雪山腳下的城市,抬頭可見的亞拉拉特山是亞美尼亞的國家象征。但山并不在國境之內。
16世紀,統一而廣袤的亞美尼亞被奧斯曼帝國征服,教堂被鑿毀,難民被遷徙,長期的壓迫最終在20世紀初升級為一場百萬人遇害的種族屠殺。
亞美尼亞種族屠殺紀念館外,幾位老人長年守在觀景平臺上,向游客指點亞拉拉特山,反復強調這座如今屬于土耳其的雪山依然是亞美尼亞的一部分。
“埃里溫好!十分好!”老人操著蹩腳的英語對我比劃著大拇指,隨即又指向紀念館的下沉式入口,做著流淚的姿勢,生怕我錯過那里的展覽:“歷史,故事,哭泣的故事。”
1920年,東亞美尼亞爆發蘇維埃革命,建立蘇維埃亞美尼亞共和國,并于兩年后成為蘇聯的一部分。這是今天亞美尼亞共和國的前身。
羅曼·羅蘭到訪蘇聯時,曾將這個外高加索小國譽為“蘇維埃的意大利”。埃里溫老城多少留存了紅色羅馬的氣質。這里書店密集,中央市場和周圍的市集上游蕩著不入流的青年畫家和書販。尋常工作日的午后,他們將油畫和舊書擺滿共和國廣場旁邊的小公園,向人們攤開這座城市的蘇聯記憶。
每本留有主人筆跡的書都是一段歷史。蘇聯時期,埃里溫匯集了一千多個科研機關、十多萬名科研人員,人均公共藏書量在所有加盟共和國中僅次于最發達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最讓我愛不釋手的是幾沓老照片和一本厚厚的前蘇聯集郵冊。雖然它們蓬頭垢面地出現在集市上,我依然能感受到前主人對它們的喜愛和呵護。那一定是一個熱愛藝術的讀書人。
相比波羅的海三國,這里的蘇聯舊物更廉價。一套24張的風光明信片開價折合人民幣不到10元,證件齊全的衛國戰爭勛章也僅開價40元,一番砍價之后我最終以60元買了兩枚勛章,但一看攤主的表情,又頗為后悔自己砍價不力。可能有些過意不去,年老的攤主連連道謝,還抓了一把蘇聯貨幣送給我留作紀念。

埃里溫老城集市上琳瑯滿目的蘇聯勛章。
埃里溫人著實是難形容的。他們對外來客似乎有著天然的友好,但有時又不免給人一種愛貪小便宜的感覺。與周邊國家一些旅游城市不同,這里沒有人滿大街追著游客乞討,他們別有一種方式:出租車司機和小商鋪普遍宣稱“不找零”。每每拿到這種“小費”,他們又會流露出害羞、不好意思和興奮交織的神情。
待了兩天后,我也學會了一招:主動告訴出租車司機“不用找零”,但要求他在此等我,負責我的下一趟行程。這種情況下,他們就不好意思收第二次“小費”了。
除去這點小小的狡黠,這可算一個天性開朗的民族。2018年4月,這座城市爆發大規模示威,全程在共和國廣場采寫報道的帕沙告訴我,那場沒有流血的游行如同一個盛大的節日。人們載歌載舞,還把烤肉攤搬到了廣場上。亞美尼亞人驕傲地將之稱為“快樂革命”。
但事實上,亞美尼亞人依然掙扎在貧困線上。蘇聯解體后,外高加索地區又一次發生種族仇殺,陰云尚未散去。埃里溫街頭的藝術裝置間總會錯落出現納卡戰爭(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爭奪納卡地區的戰爭)英雄的塑像,時刻提醒人們:這個三百萬人口的小國其實還與鄰國阿塞拜疆處于戰爭狀態。
在埃里溫的最后一晚,我登上了當地人所稱的“社會主義大階梯”。
1971年,這座城市展開了一次建筑狂想:把老城北側的一座山坡建成可供千人同登的階梯,中間是噴泉與博物館。最上層的平臺正對亞拉拉特山和主城中軸線,世界來賓可以飽覽“紅色羅馬”的全貌。
宏大而浪漫的階梯最終成了爛尾工程。今天,繞開鐵絲網和圍擋,踏上鋪著鋼板的小徑,走過未經裝飾、遍布涂鴉的通道,人們可以登頂,眺望雪山與古城。眼前的景象更像是這座城市和國家命運的隱喻:遙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最近的卻是一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