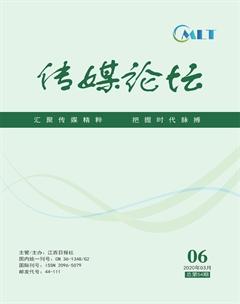探析社交媒體環境下新聞信息產品傳播的特征
李倩雯 李想
摘 要:隨著數字革命與新興媒體的快速發展,以推特、微博、貼吧等互動式社交為主的社交媒體滲入人們生活。區別于傳統媒體單向傳播為主,社交媒體以“病毒式蔓延”的傳播速度促使傳播環境向“人人皆媒,萬物皆媒”的時代轉變,本文通過對微博的新聞信息傳播模式和特點分析,探討在社交媒體環境下新聞信息產品傳播的特征。
關鍵詞:社交媒體;微博;新聞信息傳播;傳播特征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079 (2020) 06-00-02
一、引言
社交媒體是一種以互聯網為依托基于用戶關系的內容生產與交換平臺,社交平臺上的用戶都自動成為一個“自媒體”單位,以個人的形式成為信息的生產者。社交網絡傳播平臺的公共性與信息生產單位的個人化、平民化共同構成了社交媒體傳播環境。在該環境下,傳播信息的成本低廉化、傳播主體多元化,其新聞信息的傳播區別于傳統媒體環境下以單向傳播為主,呈現出“病毒式蔓延”傳播、即時雙向互動、交互性與信息不確定性等特點。而在討論其傳播環境個性化、精準化的同時,也引發對新聞信息真實性、傳播盲目性的探討和擔憂[1]。
二、微博的興起和發展現狀
微博是由新浪網于2009年下半年推出的提供微型博客服務類的社交網絡平臺,它以文字、圖片、音樂、視頻等方式為傳播媒介,集發布、轉發、評論、點贊為一體的多樣互動模式,吸引普通用戶注冊使用,打造網絡公共交流平臺。目前新浪微博已成為中國用戶數量最多的微博產品,在社交媒體中具有代表性。因而本文選取微博客戶端作為分析樣本,探討其新聞信息傳播的特征[2]。
三、微博的新聞信息傳播特征
(一)信息傳播交互性與時效性增強
依托于微博社交平臺的公共性和功能的多樣化,每一個微博用戶成為個性的信息生產者與信息接收者反饋者。不同于傳統主流媒體的新聞傳播形式,受信息流通渠道的有限和發布信息的高成本的影響,大眾處于接受者的位置,被動接受信息,傳播主體與受眾界限分明。反饋信息也需要經過一定的流程,整個傳播過程雖有序性強,但時效性差,不利于新聞信息的持續跟進。而微博平臺實現了傳播主體與受眾的隨時轉換,信息生產與接收也受個人喜好影響,選擇性大大增強。發布信息與接收信息的成本低廉化使得信息互動增多,每個微博用戶在發布信息的同時也在接受著其他用戶的信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傳播融合,信息傳播交互性增強;除此以外,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微博客戶端的便捷性,為反饋信息和再傳播提供可能,信息傳播的時效性增強。
(二)社交媒體環境下廣場式傳播的呈現
相較于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規律式的傳播,微博用戶作為個體的傳播主體,其編輯信息傳播內容的時間不受媒介本身的限制,而由傳播主體用戶自身決定。由于信息的傳播與接收受到用戶自身時間影響,因而形成了微博平臺信息發布的碎片化與信息接收的碎片化。與此同時,微博用戶在同一公共空間發布信息和接收信息,其對象不再是有針對性的、某一特殊需求的群眾,而是所有在這個空間的參與者。除此以外,傳統媒體所生產的信息經過一系列專業流程篩選、排序,可通過調整信息版面中的不同信息位置,賦予各類信息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即為公眾設置議程。而在社交媒體時代,其一對一的互動式傳播消解了傳統媒體新聞生產專業主義的議程設置功能,微博信息的傳播以順時編排、即時流動和同一呈現為主,不同程度的新聞信息產品占據同樣的傳播空間。例如新型冠狀病毒與奧斯卡獲獎名單同一時間呈現,占據同樣的傳播資源。因此,從生產者的多元化、接受者的隨機性以及信息生產的碎片化與占據空間的等量性可知,社交媒體環境下的傳播形態呈現廣場式傳播。
(三)意見領袖的影響凸顯
意見領袖是指人群中首先或較多接觸大眾傳媒信息,并將經過自己再加工的信息傳播給其他人的人。當某一新聞熱點事件引發眾多討論時,微博的隨時轉發和點贊功能使得討論中的優質內容出現在熱搜廣場上,進而引發更多關注和討論,而該內容的生產者便成為這一事件中的“意見領袖”。他們的觀點獲得認同,并被轉發進行二次傳播,引著輿論走向。但其是短暫性的,且一般只限于特定的某一事件中。在微博中,信息交換與討論的頻繁性促使意見領袖的作用明顯凸顯。但除了內容取勝成為意見領袖以外,部分公眾名人因其個人專業能力或人格魅力被部分群體認同且追捧,從而也在微博的信息傳播環境里扮演了長期性意見領袖的角色。這些長期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容易造成大眾盲目追隨,而失去自我判斷力。例如在蔣勁夫家暴事件中,某一線男星發布微博內容為懷念陽光大男孩,并引發輿論一邊倒戈,轉向陰謀論、指責受虐女方。意見領袖的傳播影響之大,如果不對其內容進行辨別和選取,則容易造成信息的盲目傳播[3]。而從意見領袖的“粉絲”即部分信息受眾的角度來看,容易由對該人物的思想認同上升至維護追隨層面,從而拒絕接受其他的聲音,造成個人思維層面的“繭房化”。
(四)社交媒介環境下謠言傳播及辟謠機制的轉變
社交媒體的主體多元化、交互性傳播與廣場式分布促成了信息平臺的信息爆炸性增長,部分接受者逐漸喪失信息辨別能力,而新技術下信息的傳播的速度及范圍得到提升與擴展,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在微博平臺,謠言傳播主要有兩種形態。一為民眾自發猜測討論而傳播的謠言,社交媒體平臺改變了信息傳播方式,由傳統的展示——觀看新聞信息模式向接受——討論的對話模式轉變。一則由普通民眾發的新奇的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信息能夠迅速占領廣場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該信息在其生產過程中未經過仔細核實,真假性難以界定。而后續的用戶對于該信息真假性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不確定信息的傳播,最終其中一部分信息成為謠言;二為官方媒體或長期性意見領袖等具有權威性的用戶發布不確實信息引發謠言的廣泛傳播。在民眾的認知中,官方媒體或長期性意見領袖具有較高的公信力和可靠性,尤其是官方媒體,在信息爆炸的時代里 ,其發布的信息具有辟謠和認證作用。例如央視新聞所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能在空氣中存活五天”這一則消息,擅自將某些冠狀病毒偷換為新型冠狀病毒概念,引發群眾恐慌。因此相較于前者民眾傳播的謠言而言,后者帶來的社會影響力和危害更大,其不僅會造成錯誤信息的泛濫引發群眾心理危機,更是對自身公信力的打擊。
伴隨著謠言傳播,其相應的辟謠機制也呈現出新的形態,逆火效應明顯與社會化辟謠是社交媒體環境下辟謠的新特征。逆火效應是指辟謠或說服常常會導致人們更加相信謠言或更加堅信原有觀點。在如今的微博平臺內,由于媒體和其他許多官方賬號一度消耗自身公信力,內容被后續“打臉”后,民眾對于其發布的聲明和辟謠信息失去信任,受動機誤解的誘因影響,從而更為相信謠言信息。以娛樂圈諸多官方工作室賬號為例,辟謠聲明所起到的真相證實作用大打折扣。官方與民眾的輿論場之間出現分裂,促進了社會化辟謠的興起,辟謠主體不再局限于官方一方,社會企業、名人及普通民眾也參與其中。微博為社會化辟謠提供了重要場所,其采用專門賬號隨時發布辟謠消息與每日各方辟謠信息匯總的模式,為公眾打造公正的信息求證平臺。這種社會化辟謠模式為抑制謠言開拓了新的路徑[4]。
四、結語
當今社交媒體環境下自媒體發展勢不可擋,以微博為代表的信息交互平臺以分享為傳播方式形成了新媒體技術下獨特的傳播形態和特征。信息的交互性與時效性增強構建了廣場式的對話傳播場景;意見領袖的作用突顯引導著民眾輿論走向,成為輿論廣場的中心支柱之一,但也引發民眾盲目跟隨觀點和其自身思維“繭房化”的擔憂;社交媒體公共空間為謠言的擴散營造了便捷條件,也塑造相應的新型的謠言應對機制。在此傳播環境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對于新聞信息的來源的追溯、信息真實性的辨別。官方媒體做到公正透明與權威可靠,公眾自身做到善辨真假、守法傳播,從而營造一個更好的社交傳播空間。
參考文獻:
[1]曾慶香,陸佳怡,吳曉虹.兩級與互補: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聞樣態與圖景[J].新聞記者,2018.
[2]周文揚.生成、影響與反思:聚合類新聞客戶端的信息繭房效應研究——以今日頭條為例[J].傳媒,2018.
[3]熊炎.謠言傳播逆火效應的成因解釋與抑制策略——基于實證研究的整合與推導[J].現代傳播,2019.
[4]李彪,喻國明.“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與傳播場域研究——基于朋友圈4160條謠言的分析[J].新聞大學,2018.
其他作者簡介:
李想,女,漢族,河南鄭州人。研究方向:網絡與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