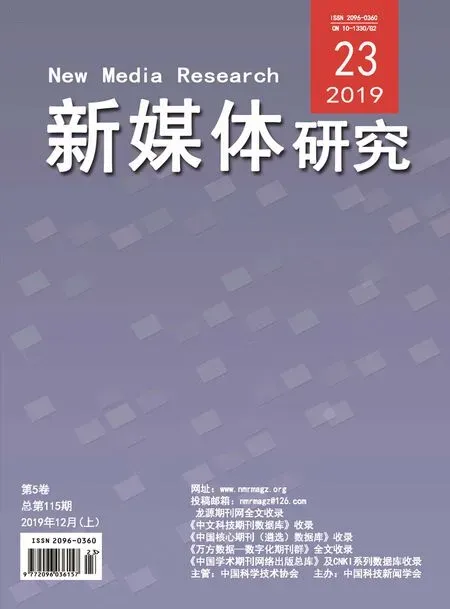沙龍復興與廣播續章:中文播客的熱度與冷性
吳思哲
摘 要 當美國播客產業如火如荼發展之際,中文播客在音頻市場始終沒有開辟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但隨著中國迎來“耳朵經濟”時代,播客這一稚嫩的舶來媒介在中國正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文章梳理了播客在中國的發展脈絡,發現了播客的沙龍屬性,并將播客與廣播進行區分,從媒介、內容、受眾、生產的角度分析了播客在中國的發展優勢。
關鍵詞 中文播客;沙龍聲音;媒介廣播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0)23-0081-04
1 中文播客的發展脈絡與生產特征
1.1 發展熱潮:舶來媒介的此岸新生
“播客(Podcast)”誕生于21世紀初的美國,其名由蘋果公司的便攜多媒體播放器“iPod”和“廣播(broadcast)”合成而來,是指一種基于互聯網、利用RSS等技術發布、可供用戶訂閱后自動接收的聚合數字音頻文件[ 1 ]。如今,距標志播客誕生的事件——2004年亞當·庫里(Adam Curry)開發首個可訂閱客戶端Podcatcher已有十六年[2],伴隨以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播客節目Serial為代表所引領的播客復興熱潮,播客這一新興的互聯網數字媒介正大跨步進入如火如荼的商業化發展時代。
與相對成熟的美國播客產業不同,中文播客的發展仍處在萌芽階段。但彼岸風生水起之時,此岸也有暗流涌動。雖然商業模式不甚明朗、普及程度尚屬小眾,中文播客正以隨風潛入夜的姿態迅速地浸潤注意力市場。2019年,中文播客見證了內容廣泛化、制作機構化、機構專業化和媒介商業化,更多群體開始將播客作為自己的內容消費 之選[3]。艾媒咨詢《2019—2020中國在線音頻專題研究報告》指出,2019年中國有4.89億在線音頻用戶,預計2020年該數字將達5.42億。中國在線音頻迎來“耳朵經濟”全場景高速發展期[4],數字音頻市場的發展前景一片廣闊。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催生了播客等文化內容產品發展創新的沃壤。迫于社交隔離的防疫要求,線下研討會、講座、論壇、課堂等文化活動紛紛停擺,而與之對應的是,人們獲取信息、新知的需求與交流、表達的渴望不減反增,拓展線上渠道成為必然之勢。得益于互聯網的普及與音視頻通訊技術的發展,學界與業界聯合自發組織的線上公益文化活動如講座、論壇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填補了特殊時期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空白。而播客作為文化傳播的新型媒介載體,也積極把握住了此次的發展機遇。2020年3月,國內首款基于RSS的中文播客App“小宇宙”上線,不僅俘獲了大量忠實聽眾,更吸引了部分潛在的草根生產者參與到節目制作中,實現從用戶到生產者的轉變。根據Listen Notes的統計數據,2020年4月平均每天出現的新中文播客超過10檔,中文播客的數量在5月已達1萬個,呈井噴之勢;截至2020年10月31日,在小宇宙App上有97檔新中文播客節目訂閱量破千[5]。在小宇宙的成功范本下,喜馬拉雅、蜻蜓FM、網易云音樂等平臺紛紛主動投身中文播客浪潮,針對播客內容調整產品,另外更有老牌互聯網公司開始研發獨立的播客產品,為加入播客賽道整裝待發,如快手也已正式發布新播客App“皮艇”。正如美國經濟學者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言,“人人成為制作者而不限于消費者”才是扁平世界里最具革命性的合作形式,隨著平臺拓展、更多的優質內容生產者入駐,平臺、創作者、聽眾形成上下聯動,播客這一稚嫩的舶來媒介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正煥發蓬勃的生命力。
1.2 生產特征:以聲為媒的沙龍復興
然而,盡管已經有生產者看見發展機遇與紅利,并將播客節目視為產品、摩拳擦掌準備一舉進軍播客市場,中文播客仍以UGC(User-generated Content)、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為主要生產模式。受到個人獨立播客的資源、水準等限制,對比美國播客兼具時事新聞、敘事、訪談、深度閱讀、紀實等豐富種類的節目,中文播客節目形態較為單一,目前以聊天訪談類為主,本文中筆者將重點討論這種節目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聊天式對談并不意味著嚴肅內容缺席。據蘋果發布的2019年度最佳播客榜單,包括大內密談、故事FM、頭號玩家、無業游民、忽左忽右、BYM職場系列、博物志、剩余價值等在內的14個播客,觸角延伸至文娛藝術、個人成長、社會科學、科技、新聞熱點等各大領域,內容體量豐富龐雜。就其生產形式、內容與影響的層面而言,聊天訪談類中文播客可以視作數字音頻版文化沙龍。沙龍誕生于17世紀的法國,復興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法國,是介于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文化社交場所,被哈貝馬斯視為“公共領域”的發端,曾為美國現代主義文化生產提供了隱秘的發展空間與孕育平臺[6]。而中文播客正是漂浮于主流大眾媒體、個人社交媒體之外的第三大陸,扮演了社會黏合劑與思想催化劑的角色。作為一款互聯網數字產品,播客不僅顯著突破了傳統沙龍對場地、共時性的要求,還在沙龍參與者之外允許了旁觀者的存在,把小型的家庭客廳拓展成為人數不設限的公共講堂。而評論區則是由聽眾組成的次級大型沙龍,聽眾在此交流收聽心得、補充討論,其中不乏精彩言談。僅在小宇宙App上,熱門播客“隨機波動”的單集播放量就可達3.4萬,評論留言達到302條①。
如果說傳統沙龍是“一塊獨特的飛地”[7],那么中文播客便形成了中文互聯網中一塊獨特的“虛擬飛地”。創作者將錄音設備放置于私人言談的沙發邊上,就開啟了公開場合的麥克風,消弭了私密與公共的邊界,把私人觀點凝聚成公共話語流向公眾,完成了從個體表達到多方互動、從自我體認到群體認同、從私人空間到公共領域、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的實踐探索。
緣于播客新式舶來品的屬性,現階段的中文主播大多是學歷較高(往往有海外留學背景)或在學界、業界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識分子與互聯網意見領袖,如青年學者、媒體/法律/文化/科普從業者等。其中一部分主播亦兼為美國早期播客聽眾,受到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思潮影響,思想較為前衛,在他們投身于播客制作實踐的過程中,常常從社會結構、文化、心理、女性視角解讀社會時事、長期熱點議題、公共領域文化現象,其中女性群體的困境、社會結構中的隱形暴力是經常出現的議題。以近期上海名媛拼單群的爆款文章為例,該文發布后在互聯網掀起議論熱潮,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沈奕斐與律師商建剛在“沈奕斐的播客”發布《談互聯網污名化:我為什么討厭對“上海名媛群”的嘲諷》,記者祝羽捷邀請作家侯虹斌做客“落選沙龍”,發布《“名媛”背后:階層焦慮、厭女與慕強》,“活字電波”發布《群嘲“拼單名媛”遮蔽了哪些真正的女性問題》等等,不同身份、文化背景的主播輸出了多元學科的理論解讀,為受眾提供了對單一事件進行全視角反思的可能。
2 中文播客的受眾心理與發展優勢
2.1 媒介冷性:廣播電臺的傳奇續章
不同于視頻和文字,播客更接近口語傳播這一最古老的傳播方式,以言語的形態介入人們的生活,與一百年前的廣播不謀而合。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將廣播電臺喻作“部落鼓”“有力量將心靈和社會合二為一的共鳴箱”,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只有言語能力能與之匹敵。“如果坐在黑暗的屋子里談話,話語就突然獲得新的意義和異常的質感。話語的質感甚至比建筑物的質感還要豐富。”[8]在麥克盧漢寫下這行文字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播客為聆聽者提供了另一個“黑暗屋子”的想象,自點擊播放選定的播客文件、戴上耳機的時刻起,我們便走進了這間黑暗的屋子,開始旁聽屋內的談話。作為一種單純的媒介,音頻在抓取聽覺感官的同時留下無數線索,從“在場”到“不在場”,聽眾收聽高清晰度的播客內容的同時,對錄制場景、主播其人的想象也在正在發生。
在數據極速傳輸的5G時代,享受視頻即時傳輸便捷性的同時,人們也承受著眼球信息過載的負擔。播客的出現可謂恰逢其時:一方面,播客解放了影像發達時代人們的視神經,使人們長期黏滯于電子屏幕上的目光得以暫時抽離,消解視覺與精神疲勞,原本單一媒介的“缺陷”現在反轉一躍成為優勢;另一方面,播客豐富、深度、垂直深耕的內容特征又緩解了人們的信息焦慮,滿足了人們汲取嚴肅內容的需求,成為文化充電的不二之選。面對大量視覺信息與人體生理局限的矛盾,它是近乎完美的解決方案。
聲音具有不可復制性,在播客時代,聲音即顏值。PodFest China《2020 中文播客聽眾與消費調研》報告指出,50.5%的播客聽眾幾乎每天都會收聽播客,28.5%的聽眾每周收聽時長在6小時以上,人們往往選擇在乘坐公共交通(53.9%)、閑暇休息(51.8%)、做家務(48.8%)、睡前(39.8%)時收聽播客[3]。播客成為日常活動的背景音,靜水流深地滲透進生活的縫隙,主播聲音的獨特性逐漸變為不可替代的感官氛圍建構,陪伴式收聽成為一種習慣。借助音頻媒介傳遞的話語因聲音的人格化而蘊含了更豐富的層次與面向,聲音通過耳膜激發觀點和情感的共振,與聽眾之間形成奇妙的情感聯結。
2.2 受眾心理:審慎克制的合理依賴
報告顯示,76.1%的聽眾具備一年以上的收聽史,33.3%的聽眾承認“粉絲效應”是他們追隨特定主播或嘉賓的重要原因[3]。但粉絲效應絕不足以解釋播客聽眾的依賴感與忠誠度。麥克盧漢對廣播媒介懷有敏銳的警惕,他直言“希特勒之所以能出現在政治舞臺,這與他利用廣播對公眾發表談話有直接的關系”[8]。但他同樣指出,廣播屬于熱媒介還是冷媒介,完全取決于一個條件:廣播引入的文化里,人們的文化素養高還是低。這就引出了當代中文播客在受眾端迥異于廣播之處:受眾在某種程度上屬于高知、高收入群體,中文播客就其目前的特性來看無疑是冷媒介。報告顯示,播客的大學本科學歷用戶占比達到60.1%,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用戶占比達到26.3%,41.2%的用戶月收入1萬元以上[3]。他們是卡茨“使用與滿足”理論中積極的受眾,對自己的需求有清晰的把握,踐行著以目標為導向的內容消費行為。在最初選擇信息源時,他們就已經主動地進行了一次嚴密的把關,對于未知的播客內容也往往保有批判的審視。在收聽節目的過程中,不少用戶在失去興趣時便會退出收聽,還有部分用戶會依據播客開頭的內容判斷是否聽完整期節目[3]。
不同于定時定點的收音機時代的廣播,移動互聯時代的播客具有靈活性與便捷性,允許了更多的使用場景,從而弱化了聲音對注意力的卷入;在播客App小宇宙、泛音頻平臺喜馬拉雅、蜻蜓FM、網易云音樂中,增加了評論功能,便于主播了解收聽效果、調整內容、更新創意話題庫,也形成了互動與反饋的良性循環。不少播客節目開設了聽眾群,在聽眾接觸播客、滿足媒介內容消費的需求之后,又提供了滿足社交需求的選項,實現了互聯網的跨平臺追隨,增強了主播與聽眾之間、聽眾內部的紐帶與聯結。聲音本身具備社群屬性,對同一播客的往期價值輸出持有普遍認同的聽眾,實際上處在興趣與觀念的同溫層,對彼此的存在有著更充分的體認,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聽眾社群也往往有更強的吸引力與向心力。
2.3 生產優勢:靈活流淌的臨場思想
從生產角度來說,播客節目錄制只需錄音、剪輯設備,在如今的移動互聯時代甚至僅憑一臺智能手機即可完成,非專業人士也能得心應手地制作出清晰流暢、觀賞性強的節目。由于制作成本低、流程高效便捷,創作者極大程度上突破了資金、技術、時間、場所等方面的桎梏,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優質內容的生產創作中。疫情期間,異地主播以線上連線的方式實現節目錄制,而通過后期調整音頻、音量,可以呈現出不亞于以往的聲音效果。這種靈活性還體現在節目更新的頻率上。現階段的中文播客往往沒有固定的更新頻率,而大部分聽眾對更新頻率也無太高預期,這有利于主播對一個話題進行長線準備、打造優質節目,也進一步降低了業余主播“入坑”的門檻。
此外,播客以單純的聲音為媒介,主播、嘉賓不再囿于鏡頭的凝視壓力,在節目中往往能夠回歸一種更質樸日常的說話狀態。而張弛有度的對話氛圍有利于邏輯事實梳理、思想觀念交流與個性情感表達,正如同為播客聽眾和受邀嘉賓的青年學者、作家淡豹在PodFest China2020年會上的發言,播客提供了很多“不是來自權威的結構化的設計”“臨場的不在提綱上的東西”[4]。這種自然流淌的特性也適應了聽眾的收聽場景,強化了播客的伴隨屬性。
由于目前中文主播的身份背景差異比較小且集中于文化領域,主播間存在的同溫層也增進了他們在線下線上交流的機會。不同節目的主播互相邀請對談的行為時有發生,聽眾也樂于旁觀自己喜愛的主播之間的互動、看到不同學科領域碰撞出的思維火花,從這一層面來說,內容創作者以強強聯合、攜手共進的真人社交方式,節約了邀請嘉賓的成本,提升了節目制作的效率也促進了學科、思想與文化的流動。
3 結語
中文播客從其聲音屬性而言具備了傳統廣播的優勢,又因受眾的自主性中和了后者一味輸出的隱患,既具備了較強的用戶黏度,又以低門檻的生產成本拓展了私人交談與公共言說的邊界,促進了思想的碰撞與文化的傳播。盡管目前還在摸索與實驗階段,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尚未明朗,但播客作為新時代新形式的文化媒介,其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注釋
①這是截至發稿前,節目《【隨機波動023】對話姜思達:除了底氣我們如今一無所有,不如干脆自由生活》】的播放量和評論條數。
參考文獻
[1]許惟一.中文播客市場有望進入快速發展期[N].國際出版周報,2020-10-19(007).
[2]宋青.播客:音頻媒介融合與“新聽覺文化”[J].中國廣播,2019(4):23-27.
[3]PodFest China:2020中文播客聽眾與消費調研[EB/OL].(2020-07-27)[2020-11-07].https://podfestchina. com/portfolio/podcast-audience-report/.
[4]艾媒報告中心(report.iimedia.cn).艾媒報告|2019-2020年中國在線音頻專題研究報告[EB/OL].[2019-12-16].https://report.iimedia.cn/download. jsp?reportId=38953.
[5]語境.刺猬公社|梁文道、姜思達跨界對談,一場“重要的少數人”的狂歡.[EB/OL].[2020-11-02].https://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66775995170 908&sudaref=s.weibo.com.
[6]劉英.女性與沙龍:現代主義文化生產與流動空間[J].婦女研究論叢,2019(6):110-118,125.
[7]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8]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北京:譯林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