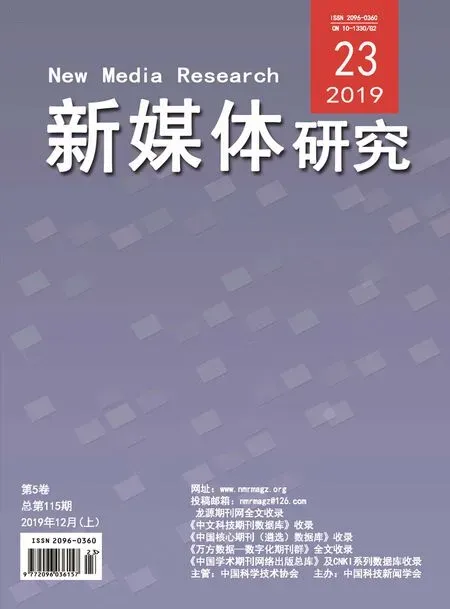網絡言語暴力事件中的群體情緒感染研究
楊詩涵 楊英新
摘 要 在互聯網時代,網絡暴力事件頻發,部分網民自以為代表正義在社交媒體中迅速集結,對新聞當事人進行口誅筆伐,尤其是明星等公眾人物,時常淪為被網暴的對象。文中選取“蔡徐坤B站事件”“申潔爭取中心位事件”等網絡言語暴力案例,分析得出網絡言語暴力事件中的群體情緒感染受譴責型情緒、主體性喪失和組織支持等因素影響,并對此提出提升公眾媒介素養,社交媒體平臺加強自治以及加強信息傳播監管,以預防網絡暴力事件的發生。
關鍵詞 網絡言語暴力;群體情緒;譴責性情緒;情緒感染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0)23-0088-03
基金項目:河北省社科聯2019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2019030503010)階段性成果。
1 相關概念簡述
根據相關文獻分析,“網絡暴力”具有以下特征:發生在網絡世界,以道德名義惡意制裁當事人并謀求網絡問題的現實解決;屬于群體性行為,網絡群體對當事人的個人信息進行追查公布,并進行語言攻擊;對當事人現實生活造成實質傷害[ 1 ]。李華君等將網絡暴力分為言語暴力、隱私泄露以及線下惡性群體性行為,其中言語暴力主要表現為話語攻擊、惡搞、道德審判等,所涉群體尤以明星等公眾人物居多[ 2 ]。在“蔡徐坤B站事件”“申潔爭取中心位事件”等案例中,當事人遭受的也主要為網絡言語暴力。
情緒是一種具有組織性且持續變化的心理狀態,埃克曼將其分為憤怒、厭惡、恐懼、快樂、悲傷和驚訝等六種基本情緒[3]。海特使用情緒簇的概念,將情緒分為基本情緒和道德情緒,道德情緒包括譴責他人(憤怒、厭惡、鄙視)、自我意識(內疚、羞愧)、他人遭遇(疫情、憐憫、惋惜)、贊美他人(崇敬、感激)以及其他情緒[4]。
人們通過捕捉他人的情緒來感知周邊人的情感變化的交互過程被稱為情緒感染[5]。大多網絡暴力事件中都涉及受爭議、觸犯倫理道德的因素,這時部分網民對當事人進行道德審判。網民受同一事件的影響在社交平臺發表言論,因情緒感染而迅速形成暫時的群體,學者將這種群體內部成員間的情緒感染交互過程稱為群體情緒感染。
2 網絡暴力事件中的群體情緒感染
2.1 群體情緒感染中的譴責性情緒
史密斯等人發現在群體或組織中存在情緒感染,并能在群體成員間形成交互作用的情緒循環,推動形成同質化的情緒狀態和社會認知[6]。在網絡言語暴力事件中,網民主要受譴責型情緒的感染,發表言論時充滿憤怒和鄙視。
網民在社交媒體中進行交流時,往往會按偏好形成趣味相投的群體,在這個過程中,網民不斷加深其刻板印象,如部分人會對東北人、富二代等存在固有成見。蔡徐坤作為偶像,身上也帶有“流量明星”“小鮮肉”等標簽,與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組織合作后,一些網友以其形象與籃球運動不符為由頭,創作惡搞視頻,并進行言語暴力,以抒發不滿。其他網友還未了解事情經過,見勢便也加入謾罵隊伍中。在B站有關蔡徐坤的視頻中,大多是通過換臉、重復等手段惡意剪輯,發布滿屏“雞你太美”彈幕的用戶中,跟風抹黑的人數不得而知。
同樣的網絡言語暴力多發生于年輕一代的藝人明星群體,如2020年3月播出的《青春有你2》節目中,參賽選手申潔及其姐妹四人因爭取中心位而遭全網嘲諷。豆瓣小組成為網民言語暴力的聚集地,網友不時在小組中發布申潔等人的惡搞圖,在評論中清一色地使用“鯰魚”“丑”等貶義詞語攻擊其長相。豆瓣小組的相關討論中充分體現了網民的厭惡和鄙視等譴責型情緒,在聚集于豆瓣的網友群體情緒感染下,對申潔姐妹的網暴也愈演愈烈。社交媒體是網民自由討論的重要平臺,但網絡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和網民參差不齊的媒介素養使得部分網友在發表意見時,常使用不理性和攻擊性的語言煽動形成群體譴責型情緒。
2.2 網民在群體情緒感染中喪失主體性
波諾和伊利斯發現在群體情緒感染過程中,群體領導者起著重要作用,領導者的情緒無論正面抑或負面都會感染群體成員。根據美國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的兩級傳播理論,在大眾傳播中,信息并不是直接流向受眾,而是要經過意見領袖這個中間環節,即大眾傳播——意見領袖——一般受眾[7]。這就使得網民更易受領導者的引導而喪失自身的主體性。
在社交媒體中,擁有上萬粉絲的博主都稱得上是意見領袖,他們對關注自己的粉絲有著極高的影響力,也極易煽動網民情緒。
蔡徐坤事件中,B站“五毛錢的宿命”“貓店”等多名用戶制作的惡搞視頻播放量達千萬,轉發也達數十萬。網民受意見領袖的引導集結成群,在沖動易變的群體情緒感染下,關注點集中于吐槽蔡徐坤打籃球的動作,沒有人在意蔡徐坤與美國職業籃球聯賽合作的初衷,只是借蔡徐坤作為新生代偶像的影響力,號召大家關注籃球運動。可以看出,部分自媒體為吸引受眾,搶奪輿論話語權而一味發布缺乏理性的內容帶節奏,受意見領袖的引導,網民集結成群,在沖動易變的群體情緒感染下,個人主體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體的沖動急躁,進而引發網絡暴力事件。
2.3 組織支持下的群體情緒感染
有學者指出群體成員的組織支持感顯著影響群體成員的情緒狀態,組織支持感是指成員對組織如何看待他們的貢獻并關心他們利益的一種總體知覺和信念。
在申潔爭取中心位以及蔡徐坤事件中,微博、豆瓣和B站等平臺的惡搞視頻和圖片明顯侵犯其肖像權,甚至在當事人提起訴訟后,相關視頻卻始終沒有下架,這一做法無疑于默許這些“主犯”的網絡暴力行為。截至2020年4月3日,在B站以“蔡徐坤”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得到的視頻達50頁,共1 000條,發布時間跨度從2019年3月到2020年4月,仍在不斷更新。其中大多數是作者惡意剪輯的鬼畜視頻,播放量最高的達1 558萬,彈幕也滿是對蔡徐坤籃球水平、舞蹈等的貶義評價。媒體平臺本該在信息傳播中承擔審核確認的作用,卻并沒有對相關視頻和傳播者進行下架或關閉賬號的處罰,其他創作者更無收手之意。
媒體組織的不作為,使得部分網友感知到一種變相的組織支持感,相關惡意視頻和圖片持續傳播,且更新不斷,甚至貶低相關明星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3 群體情緒感染下的網絡言語暴力規避對策
3.1 提升公眾媒介素養
在信息爆炸的互聯網時代,網民每天面對呈指數增長的信息,為免受群體情緒感染的影響,需要提升自身媒介素養,提高對信息的辨別能力,在全社會范圍提升媒介素養,需要學校教育的配合。據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我國19歲以下,也就是中小學階段的網民,占總數21.8%,他們也是社交平臺中最活躍的用戶。但處于這一年齡層的網民心智還未成熟,容易受外界干擾誘導,這就需要學校定期開展媒介素養教育課程,幫助中小學生正確使用社交軟件,培養辨別真偽的能力,拒絕對網絡信息盲信盲從。同時也應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軟件的時間,B站用戶發布彈幕前,首先要答100道題來學習彈幕禮儀,但很多視頻中仍然有惡意刷屏、發布侮辱性言論等現象。為規避這一現象,還需在學校開設相關課程,更大范圍地普及媒介素養教育,培養全民信息甄別能力,做到理性思考,避免受不良媒體或他人的操控誤導。
另外,由于網絡的虛擬性和治理滯后,部分用戶常在社交網絡中表現出有違現實生活倫理道德的一面。社交軟件可以設計使用規范并普及,根據用戶年齡及使用時間等信息,設置用戶等級,每升一級可以獲得更多使用權限,同時也需要回答更多使用規范測試題。一條攻擊性言論可能不足掛齒,但若人人不負責任地把謾罵他人當作消遣,網絡將是一片亂象,誰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中傷者。網絡行為也是社會行為的一部分,同樣受到現實法律道德的制約,公眾在網絡世界中也應保持客觀公正,尊重他人,自覺抵制低俗信息,提高道德修養。每個人都應為自己在網絡社交平臺中的言行擔負起責任,做到理性發言,不造謠不傳謠。媒體平臺應完善相關監管工作,確保用戶為自己在社交平臺中的言行擔負責任。
3.2 平臺加強自治
隨著媒介技術變遷,專業化的新聞生產受到自媒體、公民新聞等新聞生產形式的沖擊,因此社交媒體平臺必須承擔起把關人的角色,做好信息核查工作。當前各社交平臺仍需培養建立專業審核團隊,并開發相關程序屏蔽不良信息。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速度快、范圍廣,因此輿情監測在預防網絡暴力中尤為重要,監測部門應實時監督,及時發現互聯網中的侮辱誹謗、傷害他人權益的信息,并進行治理。在失真和侵犯他人權益的信息進一步傳播之前,媒體平臺應加強信息篩選和過濾,從源頭治理。另外,社交平臺應主動設置議程,在主頁、頭條等顯著位置加大宣傳正面報道,優先推送權威性媒體消息,遏制信息來源不明的內容的傳播。對平臺入駐的博主也應嚴格管理,我國于2000年9月25日公布施行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以及2020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中,明確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制作、復制、發布、傳播含有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信息,強調網絡信息內容服務使用者和生產者不得開展網絡暴力、人肉搜索等違法活動,各社交媒體平臺應積極響應并落實相關規定,對發布虛假有害信息的博主,依據嚴重程度,進行視頻下架、禁言、封號等處罰。
3.3 加強信息傳播監管
許多網絡暴力事件的發生源于網絡中存在大量失實信息,政府相關部門應搶奪網絡話語權,對引發公眾關注的輿情事件及時發聲,避免公眾受不良媒體的錯誤引導而喪失理性,充斥于網絡中一味宣泄譴責性情緒。共青團中央、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和相關部門應關注公眾訴求,重視正面報道,宣揚正能量,杜絕網絡暴力。另外還需依靠相關法律法規強制性管理,保證法律具體實施,我國互聯網信息監管制度在不斷完善,但網絡謠言、網絡暴力事件仍然不減,黨委宣傳部、新聞出版廣電局等部門還應落實各地監管。除公眾對明星群體的網絡言語暴力外,一些不良社會新聞如醫患矛盾、婆媳矛盾、偽科學信息等的傳播也容易造成整個社會的低俗化,降低民眾的判斷力,媒體應重視熱點事件的變化,制定階段性宣傳報道計劃,通過電視、廣播電臺、社交軟件等渠道大力進行正面報道,體現出人文關懷,緩和社會矛盾并倡導正確的價值觀,給公眾以正面引導,避免其陷入群體譴責性情緒的漩渦。
4 結語
近年來,網絡暴力事件不斷登上熱搜,對當事人造成或大或小的傷害,文章選取“蔡徐坤B站事件”“申潔爭取中心位事件”等網絡言語暴力案例,分析了網絡暴力事件中的參與者在組織支持下,受到群體情緒感染,進而形成譴責性情緒且主體性喪失,對此提出在學校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社交媒體平臺加強自治以及加強信息傳播監管的對策,對網絡暴力事件進行規避。在網絡時代,社交媒體平臺的互動性、隱匿性等特點給用戶提供了隨時成群的條件,但用戶更應保持理性,避免成為勒龐所說的無意識、情感極端的烏合之眾,在群體情緒感染中迷失自我。
參考文獻
[1]王浩宇.青少年.“網絡暴力”現象的形成原因和治理對策[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11,21(4):11-14.
[2]李華君,曾留馨,滕姍姍.網絡暴力的發展研究:內涵類型、現狀特征與治理對策——基于2012—2016年30起典型網絡暴力事件分析[J].情報雜志,2017,36(9):139-145.
[3]葉勇豪,許燕,朱一杰,等.網民對“人禍”事件的道德情緒特點——基于微博大數據研究[J].心理學報,2016,48(3):290-304.
[4]劉績宏,柯惠新.道德心理的輿論張力:網絡謠言向網絡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國際新聞界,2018,40(7):37-61.
[5]王瀟,李文忠,杜建剛.情緒感染理論研究述評[J].心理科學進展,2010,18(8):1236-1245.
[6]田維鋼.微博評論中的網民情緒傳播機制及策略[J].當代傳播,2019(1):66-69.
[7]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