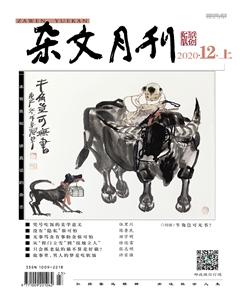尚可喜不只是想多得到一件錦袍
蔣勛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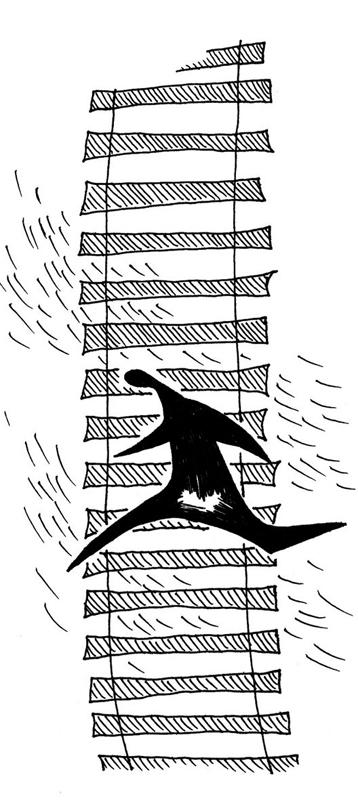
尚可喜,清代藩王,本為明廣鹿島守將。崇禎七年,渡海降清,授總兵官,太宗崇德間封智順王,隸漢軍鑲藍旗,順治間改封“平南王”。
一個傳聞很多,爭議很大的人物。
且不去評價這個人如何。而因為他發生的,且流傳至今的一個故事,卻耐人情味。
順治六年,身經百戰的尚可喜,憑借建立和鞏固清王朝立下的汗馬功勞,獲封“平南王”。皇上賜金印金冊。而皇太后還特別恩賜一件熏貂領花綢錦袍。什么意思呢?平南王優秀,但離不開尚母的養育之勞。
皇太后出于好心,考慮問題周到。
好事啊!子榮母貴。
殊不知,就是這件錦袍差點送出大問題來了。
皇太后就沒有想到這尚可喜會有兩個母親,他為二房所生,大房所養。這一件錦袍給誰呢?就算尚可喜精明,這事也左右為難,是燙手山竽。
果然,這兩位母親聽到風聲找上門來。
生母說:“我親生的兒子,這錦袍得歸我。”
養母說:“我養大的兒子,這錦袍不歸我歸誰?”
誰也不甘示弱,吵得烏煙瘴氣。
尚可喜誰也不敢得罪,思前想后,覺得一件錦袍既然分不開,還不如一退了之,誰也別得。于是草擬奏章,據實上奏,說自己有兩位母親,生母、養母對皇太后恩賜的錦袍“爭執不下”,都想要,又不好給誰,無奈之際只好送還。這時有幕僚看了,以為兩位母親為一件錦袍“爭執不下”,說出去成何體統?遂建議將“爭執不下”改為“禮讓不迭”。尚可喜對這樣改很認可。
改動的奏章就這樣報了上去。
皇太后看過奏章后,大發感慨:“兩位母親如此賢德,難怪尚可喜能出人頭地。”隨之又賜了一件同樣的錦袍。
這事原本怪不得皇太后,好心賜錦袍,哪里知道這尚可喜有兩個母親?一件不夠,禮讓不迭,互相謙讓,多么感人的場景,多么寬廣的胸襟,既然互相推,莫不如再加一件,簡單啊!一人一件,皇恩浩蕩,皆大歡喜。
結局是如此美好,傳為千古美談。
這事做得漂亮,真沒說的。
皇太后賜的錦袍很貴重,名氣遠遠大于實物。一件變兩件,憑空多得一件。
尚可喜當然高興。但他的出發點并不只是為了多得一件錦袍,盡管這錦袍很珍貴,很榮耀,很體面,很有價值。他為兩位母親平息紛爭,各有所得高興。都擁有了一模一樣的錦袍,沒有理由再爭執。他也為家丑變美談高興。兩位母親為一件錦袍“爭執不下”,說出去,尤其要是讓皇太后知道,面子往哪擱?沒教養,沒胸懷。丑啊!丟人啊!“爭”改“讓”。天壤之別,顛覆了過來。母親的形象一下高大無比,不感動不行,不佩服不行。他更為自己得到權威認可高興。你看,自己這么優秀,是因為母親的賢德。追根溯源,想不優秀還不行啊!皇上看準了!真是優秀!這同時為今后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一舉多得,全在一念之間。一句話,一輩子。
或上天堂,或下地獄,有時就在一念之間,一句話之間。
尚可喜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名譽、尊嚴、影響、口碑。
當然,這是個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
如果,皇太后得知真相,相信會后悔的。
本來,尚可喜的兩位母親為一件錦袍爭也是人之常情,不值得大驚小怪。很正常,都有理。生母可以要,養母可以得。
但是這種事如果是發生在普通百姓身上可以,發生在一般人身上可以,而發生在尚可喜母親身上萬萬不可。
為什么?是因為尚可喜的身份。
那時,他事業如日中天,形象高大。而他的兩位母親竟然會去爭一件錦袍。外人會怎么看?這是怎么回事。尚可喜的母親怎么會這樣?怎么會有這樣的母親?有其母,必有其子,尚可喜的形象會跟著受影響,威信大打折扣。要命的是,如果傳到皇上那里,尚可喜真夠喝一壺的,怎么解釋?如何自圓其說?
換個角度,換出了境界,換好了形象。
就這樣逆轉,因為一句謊言,厲害吧?這謊撒得真有水平。
騙得皇太后心花怒放,團團轉。
還好,這只是一件小小的錦袍,涉及到的也只是尚可喜個人的名譽,小兒科。假如撒的是另外的謊,更大的謊,涉及到全局性的、重要的、重大的事呢?
不敢想象后果和影響。
問題是這世界上如此撒謊的大有人在。
而撒謊的手段各有不同,無所不用其極,說得天花亂墜,天衣無縫,使你不得不信,不得不聽。撒謊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掩蓋事實真相就是另有所圖。就是要讓人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的確如此,如假包換。如果一旦相信,就會可能據此誘導作出錯誤的判斷,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這正是撒謊需要的效果。
撒謊巨大的欺騙性就這樣使人輕易上當,防不勝防。
碰上這種事,最好多問個為什么。
假如皇太后多了解一下尚可喜母親對所賜錦袍的情況,一下就會露餡。可惜她沒有,只憑奏章就輕易相信,匆促作了決定。
有很多的人也如皇太后一樣。只不過是有的不想問,有的不敢問,有的不去問。有的有自己的“小九九”,睜只眼,閉只眼,你好,我也好,樂得送順水人情,或者自己也可從中分一杯羹,各取所好。
撒謊能得逞,除開撒謊撒得有水平外,同樣也有適合其生存的土壤。
撒謊是可恥的,輕易相信撒謊的是可悲的,而慫恿放縱撒謊的是可恨的。
一個人能做到自己不撒謊很不容易。而要做到不上撒謊者的當更不容易。
童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