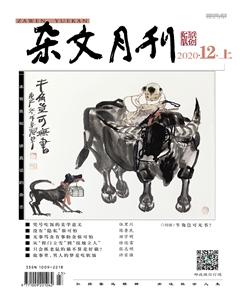學者能當官嗎?
楊建業(yè)

這好像是個假議題。倘其人不僅學術水平一流,管理才能也一流,且精力過人,為何不能當官?
如竺可楨、錢學森、錢三強等,均是這類“雙一流”人物。可以毫無夸張地說,倘沒有錢學森、錢三強這樣的“科技官”,今天我國的核事業(yè)和導彈發(fā)展會是一種什么狀況,都不好說。
但學者對于官,做,還是不做,有時還真成為一個問題。
有個故事流傳得很廣。早在民國時期的1928年,傅斯年受中研院院長朱家驊之托,力邀有著“非漢語語言之父”之譽的語言學家李芳桂先生出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一次,李對傅三番五次的游說和糾纏實在有些不耐煩了,干脆不客氣地對時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道:“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聽后十分尷尬,只好躬身長輯道“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遂告退。李芳桂的意思是,真正一流的學者誰肯把時間花在做官上面?這雖有些偏頗,但也說明了當時的學者把當官,至多看成是一種責任在身“不得不做”的事。譬如竺可楨,我國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人,一流的物候學家,在他的主持下,把戰(zhàn)火中的浙大,辦成當時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在他長校期間,群英薈萃。既有王淦昌、蘇步青、談家楨、貝時璋等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又有錢穆、馬一浮、熊十力、豐子愷等人文大師,以至于當年親赴浙大參觀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先生盛譽學校為‘東方劍橋,令人欽羨一時。”(見2010.3.29《中國青年報》)但另一方面,竺可楨對當浙大校長一事,又簡直是深惡痛絕。因為他一心向學,只想當好一個科學家。在日記里,他不無遺憾地寫道:“十年校長,已成落伍之氣象學家矣!”曾先后十次請辭校長職務,但有時是官方不允,有時是學校西遷離不開,有時又是學生苦留不讓走。可見竺可楨對于浙大長校,實在是有點不得不干的無奈。這說明,一個真正“志于學”的學者,即使精力再充沛,再有組織能力,也總會為分心于繁瑣蕪雜的行政工作而不爽。
那么,行政工作完全離開學者行不行呢?竊以為,很多時候也是不行的。譬如今日高校行政化之所以飽受詬病,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校者多不是遴選有巨大社會學術聲望的一流學者和教育家。有些地方的上級組織部門給高校委派校長或書記,往往很隨意。或在這兒弄一個企業(yè)領導人來學校當書記,或到那兒搞一個副市長當校長。只考慮級別的對等相稱,卻未認真思考過這些人是否真正懂教育,學問上是否對等,能否深孚眾望。如今,在某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許多人之熱衷于當官,無非是將之看成是一種個人飛黃騰達的象征而已。其實,就這類人而言,雖非一流學者那樣的天縱英才,但也大都聰明過人。我常常暗暗為之惋惜:倘能潛心搞研究,即便不能成為一流人才,在業(yè)內(nèi)也絕對會成為拔尖人物,而如今,不僅官當?shù)煤芷接梗芏嗳诉€當出了一身壞毛病: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樣樣俱全不說,還剛愎自用,目空一切,本事不大,架子不小,膚淺勢利,薄情寡義,一副權力暴發(fā)戶的嘴臉。
因此,學者能否當官,本不是問題。只要做啥像啥,且啥都能做成一流,就是好樣的。例如,沒有人會說丁文江不像市長,說竺可楨不像浙大校長,更沒人說錢學森不像科學院力學所所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而且有些人,即便官當?shù)臅r間很短,也留下了不凡的業(yè)績。如北大的首任校長嚴復,在北大不過五個月,就做了對北大影響深遠的三件事,一是主持了北大改革,歸并了科目;二是辦學方針上提出“兼收并蓄,廣納眾流”,開啟了蔡元培辦學思想之先河;三是頂住了舊教育部停辦北大的壓力,保住了北大。不似今天的某些人,當個什么長即便當了十年八年,也乏善可陳,沒給后人留下任何可圈可點的遺產(chǎn)。至于為何現(xiàn)今的“學者”熱衷于當官,卻當?shù)糜趾懿徽樱@應該是另一個大題目了。就此打住。
朱慧卿/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