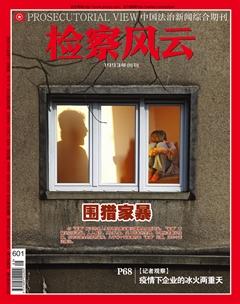做一片有溫度的雪花
王丹鳳

2019年上映的韓國電影《證人》,是一部將法律技術性和人文關懷結合得很好的律政電影,它講了一個殺人嫌犯的辯護律師與該案唯一的目擊證人之間的故事。“昨夜下了厚厚的雪,可能是覺得屋頂、路面、田間會冷,給他們蓋上了厚被吧,所以才會只在寒冷的冬天降臨”。在影片的開頭,15歲自閉癥少女林智宥在課堂上誦讀這段課文后說:“可是蓋上雪會冷的,因為,雪是冷的。”
律師楊淳浩少年立志成為做好事的律師,后來如愿以償成為優秀的民權律師,但是隨著在這殘酷的世界起起伏伏,為生計所迫的他加入了一家知名律所,成了他原來最看不上的商業律師。為了提升該所在刑事方面的聲譽,按照事務所上司的安排,他成了一起引起轟動的保姆殺人案中被告人吳美蘭的辯護人。在該案中,林智宥的庭外證言成為檢方指控被告人唯一、直接的有罪證據。
從法律上講,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但是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對于楊淳浩來說,雖然在與吳美蘭的交流中他還是能夠確定她有罪,但是辯護人角色決定他必須打贏這場官司。如果想打贏這場官司,必須拿掉智宥的庭前證言,而攻擊的方法只能是從其作證能力和證言可信度著手。楊淳浩想盡各種辦法接觸林智宥,并試圖說服其出庭。林智宥作為自閉癥患者,存在一定的語言和交流障礙,但有著高于常人的敏銳聽覺和強大的記憶力。楊淳浩在剛開始接觸她時也是處處碰壁,聽了智宥好友的話,從與她一起做智力題入手,逐漸與其成為了朋友,最終令智宥出庭作證。韓國刑事審判由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審理。雖然智宥在檢察官的詢問中陳述了案發時她看到的案發場景,但在交叉詢問環節,楊淳浩著力攻擊她這個“朋友”的證言可信度,利用自閉癥患者的某些認知和表達缺陷,用三張圖誤導了陪審團,讓他們認定智宥沒有正確的感知力與理解力,得出智宥系“精神病”,因此其證言不可采信的結論。智宥的有罪證言最終被法庭排除,被告人吳美蘭被無罪釋放。
但是故事并沒有結束,檢方對該案提起抗訴。吳美蘭釋放后詭異的笑容,宣判前后判若兩人的態度轉變,都讓楊淳浩心生懷疑。他也因在庭上傷害了一個本不該傷害的人,良心遭受譴責。“這世上沒有不會犯錯的人”,父親的話讓楊淳浩幡然悔悟,重新審視自己,并試圖在二審中再次申請智宥出庭,還原真相。飽受羞辱的智宥,雖然遭到釋放后的吳美蘭的恐嚇,以及母親的百般勸阻,但還是選擇相信楊淳浩,毅然再次出庭作證。在二審庭審中,楊淳浩在法庭上引導智宥展示其超強的聽覺和記憶力,尤其是讓她一字不漏地說出在幾十米之外聽到的吳美蘭施暴當晚說的108個字,完美再現了犯罪現場,迫使被告人吳美蘭在庭審中承認了罪行,最終被定罪。
從電影《證人》來看,韓國的刑事司法引入了美國陪審團的一些要素,尤其是庭審的證人出庭和交叉詢問環節,十分緊張和精彩。陪審團審判給了律師在普通人面前攻擊證人可信度的機會,陪審制使得庭審的不確定性增強,給辯護人險中求勝的機會。本案一審即是如此,但是辯護人出于維護當事人利益,不當地利用證人的弱點,這一切都是對的嗎?楊淳浩在面對良心的譴責的時候,選擇了站在良知的一面。本案中的自閉癥少女智宥也沖破了生理上約束、克服了惶恐,哪怕別人傷害了她,她也愿意相信人性本善,就像一片“有溫度”的雪花,努力地捍衛了法律的尊嚴和司法公正。
雖然電影的結局很圓滿和溫馨,但是它所呈現的法律人職業角色倫理與普通人的良知、正義感的沖突,卻是一個永恒的難題。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