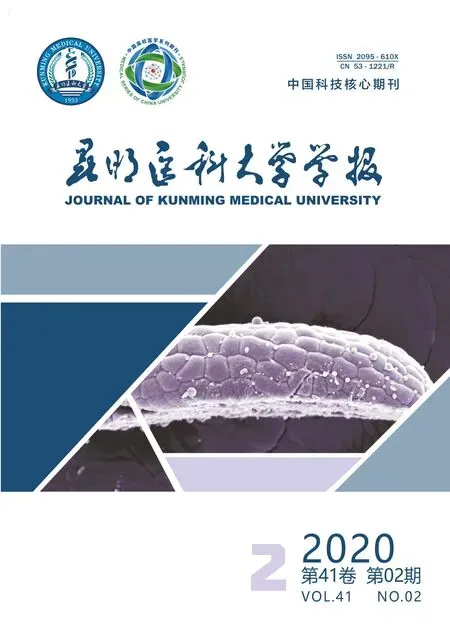不同鎮痛模式在幼兒疝氣修補術后早期鎮痛的臨床效果
劉少星,謝先豐,曹德鈞
(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麻醉科,四川成都 610017)
小兒腹股溝疝氣修補術是小兒外科最常見下腹部手術之一且手術時間短,創傷小,周轉快[1],研究發現,該類手術術后0~24 h 疼痛明顯,因小兒表述能力差及部分麻醉醫生對該類患兒術后的鎮痛不夠重視致使該類小兒腹股溝疝氣修補術后鎮痛效果不夠理想。有文獻報道[2]應用骶管阻滯、髂腹下/髂腹股溝神經阻滯能為該類患兒提供較好的術后鎮痛療效,但骶管阻滯操作過程中擺放特殊體位可導致喉罩移位,穿刺損傷神經等問題;同時髂腹下/髂腹股溝神經阻滯接近手術切口,注射局麻藥物后易導致手術部位組織移位、腫脹、解剖層次不清晰等,干擾手術操作,故臨床上對這類患兒的鎮痛尚需一個簡單易行的方法。隨著超聲引導下神經阻滯的發展,超聲引導下TAP 阻滯在腹部手術中的應用取得較好效果[3-4],但目前未見這些不同鎮痛模式對幼兒腹股溝區手術的術后早期鎮痛效果比較的文獻報道。因此,本研究采用超聲引導下TAP 阻滯、骶管阻滯、切口局麻藥物浸潤、靜脈控制鎮痛四種鎮痛模式在腹股溝斜疝修補術的患兒進行早期鎮痛療效的觀察,為臨床具體應用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經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醫院倫理會批準,所有患兒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選擇2017 年6 月至2018 年6 月在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擇期行單側腹股溝斜疝手術的患兒,性別不限,年齡2~4 歲,ASAⅠ級。受試者均無凝血功能障礙,無局麻藥物過敏史,無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病史,無擬手術及麻醉穿刺部位感染。排除標準:智力發育障礙,先天性心臟病史,哮喘病史,鹵族吸入麻醉藥物過敏者,唇腭裂患兒,患兒家屬學歷低于高中學歷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四組:超聲引導下TAP 阻滯組(T 組)、骶管阻滯組(C 組)、切口局麻藥物浸潤組(I 組)和靜脈控制鎮痛組(P 組)。
1.2 方法
所有患兒術前均不使用鎮靜藥,常規禁食6 h、禁飲4 h。由患兒家屬陪伴進入手術室后,持續監測ECG、BP、SpO2。面罩吸入6%~8%七氟烷,氧流量6~8 L/min 進行麻醉誘導,待患兒睫毛反射消失,患兒家屬離開手術間,開放外周靜脈通道,待患兒下頜松弛后置入相應型號喉罩,確認喉罩位置正確后接麻醉機,術中全憑吸入七氟烷維持麻醉,呼氣末七氟烷濃度調至2.5%~3.0%,保留患兒自主呼吸,間斷輔助通氣,維持呼氣末二氧化碳分壓(PETCO2)于35~40 mmHg 之間。所有患兒手術縫合皮膚時給予芬太尼1 μg/kg,停止吸入七氟烷,以吸入純氧6~8 L/min 排除殘余麻醉氣體后,待呼吸平穩時送往麻醉恢復室監護2 h,達到對應的拔管指針時拔除喉罩。所有患兒在喉罩放置成功后,T 組患兒由同1 名資深麻醉醫師使用Sonoscape 便攜式超聲儀、6~13 MHZ 線陣探頭實施靠近髂前上嵴的TAP 阻滯。將探頭橫軸放置于手術側髂前上嵴偏頭側部位,分清腹外斜肌、腹內斜肌、腹橫肌層次,采用平面內法進針,待穿刺針進入腹內斜肌與腹橫肌之間,回抽無血,給予0.25%羅哌卡因0.5 mL/kg。C 組患兒由同一名麻醉醫師實施單次骶管阻滯。放置喉罩成功后,患兒擺放側臥胸膝位,消毒鋪巾,穿刺成功后回抽無血液及腦脊液后,骶管腔內緩慢注射0.25%羅哌卡因1 mL/kg。I 組患兒由固定的兒外科醫師在縫合切口前行切口周圍0.25%羅哌卡因0.5 mL/kg 浸潤阻滯。P組患兒在手術縫皮時連接靜脈鎮痛泵,配方為曲馬多8 mg/(kg·d),背景劑量3 mL/h,無追加劑量,鎖定時間為24 h。固定一名兒科護士根據患兒的主訴和哭鬧程度進行判定是否給予追加曲馬多2 mg/kg 作為補救措施。靜脈鎮痛泵和神經阻滯藥物固定由同一麻醉醫師根據患兒體重和所在組別配置。由專人評估和記錄四組患兒如下指標:(1)記錄患兒術后1、2、4、6、8、12 及24 h 的疼痛評分和HR 和MAP。疼痛評分采用FLACC 評分法[5]根據患兒有無哭鬧、面部表情、軀體姿態、腿部姿態、有無多動等行為進行數字估分:0 分(完全不痛),1~3 分(輕微疼痛),4~5 分(中度疼痛),6~10 分(重度疼痛)。如果幼兒術后FLACC 評分≥5 分,則給予曲馬多2 mg/kg 靜脈滴注進行鎮痛補救;(2)記錄患兒術后有效鎮痛時間,其定義為:從手術結束后到患兒追加曲馬多的時間;(3)記錄下肢運動阻滯時間和首次肛門排氣時間:患兒清醒后采用改良Bromage 評分(0 分,無阻滯;1 分,不能做直腿抬起;2 分,不能屈膝;3分,不能活動腳踝),Bromage 評分≥1 分則認為存在運動阻滯,記錄其阻滯時間;(4)記錄患兒家屬的滿意度和患兒無惡心嘔吐、尿潴留等不良反應。所有指標均固定同1 位不知患兒分組情況的麻醉醫師進行評估和記錄。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統計學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組內比較采用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計數資料比較采用X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80 例患兒。四組患兒在性別比例、年齡、體重、手術時間、麻醉時間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l;四組患兒術畢各時間點疼痛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四組患兒術畢各時間點HR、MAP 與術前比較無統計學意義,見表3;T 組、I 組、P 組術后有效鎮痛持續時間較C 組明顯延長(P<0.05),下肢運動阻滯發生率均低于C 組(P<0.05),追加曲馬多的次數少于C 組(P<0.05),首次肛門排氣時間均低于C組(P<0.05),三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 組、C 組、I 組患兒家屬滿意度明顯高于P 組(P<0.05),見表4;手術后24 h 內,C 組患兒有1 例發生惡心嘔吐和2 例患兒發生尿儲留。P 組有4 例患兒發生惡心嘔吐和1 例尿儲留,T 組、C 組、I組的惡心嘔吐發生率明顯低于P 組(P<0.05),見表5。
表1 四組患兒一般情況比較()Tab.1 Comparisons of general data among the four groups()

表1 四組患兒一般情況比較()Tab.1 Comparisons of general data among the four groups()
表2 四組患兒術后各時間點FLACC 評分()Tab.2 Comparisons of FLACC among the four groups()

表2 四組患兒術后各時間點FLACC 評分()Tab.2 Comparisons of FLACC among the four groups()
表3 四組患兒間術前、術后HR、MAP 比較()Tab.3 Comparisons of HR、MAP among the four groups()

表3 四組患兒間術前、術后HR、MAP 比較()Tab.3 Comparisons of HR、MAP among the four groups()
表4 四組患兒間其它指標比較()Tab.4 Comparisons of other indicators among the four groups of children()

表4 四組患兒間其它指標比較()Tab.4 Comparisons of other indicators among the four groups of children()
與C 組比較,*P<0.05;與P 組比較,△P<0.05。

表5 四組患兒間不良反應比較[n(%)]Tab.5 Comparisons of adverse reactions among the four groups of children [n(%)]
3 討論
術后疼痛經歷會對患兒產生不良影響,如行為學改變和疼痛閾值降低,這將不利于患兒情感及活動能力的成長。因此,臨床醫師應該積極提供良好的術后鎮痛,抑制應激反應,又不影響患兒的其它生理功能[6]。目前小兒腹股溝疝修補術術后鎮痛常用靜脈控制鎮痛,可提供持續鎮痛[7],但在使用過程中,存在需要與患兒家屬和護士進行反復溝通培訓,并且存在對疼痛的判斷失誤,出現鎮痛藥物不足或過量的情況。因此有必要觀察不同鎮痛模式對這類短小手術術后的鎮痛效能和不良反應。
患兒下腹部疝氣修補術的腹壁切口疼痛是術后疼痛的主要原因。王文凱等[8]報道TAP 和骶管阻滯在腹腔鏡下的下腹部手術鎮痛觀察,均能提供良好的術后鎮痛,而骶管阻滯能減輕患者靜息和活動時的疼痛,TAP 阻滯只能減輕患者靜息狀態下的疼痛。筆者觀察到本研究中超聲引導下的TAP 阻滯、骶管阻滯、切口局麻藥物浸潤和靜脈控制鎮痛術后鎮痛效果確切,可能這與研究所選擇的手術種類不用進入腹腔,不影響腹壁神經叢有關。在術后有效鎮痛持續時間方面,超聲引導下的TAP 阻滯術后有效鎮痛持續時間最長,為18.5 h,骶管阻滯術后有效鎮痛持續時間為9.2 h,這也和文獻報道基本一致[9]。骶管阻滯患兒術后首次肛門排氣時間延長,這與骶管阻滯對腸道功能有一定抑制作用有關;同時骶叢神經被阻滯,導致膀胱內括約肌收縮及膀胱逼尿肌松弛有關,患兒出現尿儲留癥狀。TAP 阻滯、切口局麻藥物浸潤對患兒胃腸道影響小,未觀察到尿儲留現象。靜脈控制鎮痛患兒家屬滿意度最差,分析原因主要如下:患兒靜脈留置針需長時間保留,不利于患兒活動,并且存在脫落、管道堵塞情況,增加患兒重新穿刺等風險;患兒使用鎮痛泵后發生惡心嘔吐等藥物不良反應。
腹壁肌肉由腹外斜肌、腹內斜肌和腹橫肌及其腱鞘組成。腹部皮膚、肌肉和壁腹膜的感覺神經主要來自T6~L1感覺神經前支。TAP 阻滯能夠有效阻斷走行于側腹壁腹內斜肌與腹橫肌之間的感覺神經前支,提供良好的下腹壁鎮痛效果,該方法已經成功應用于不同年齡段患者下腹部手術鎮痛[9]。但臨床上不同入路的TAP 阻滯可以滿足不同手術部位的需求[10]。本研究借助超聲引導選擇靠近髂前上嵴的TAP 阻滯入路,能在直視情況下看清楚穿刺針的行進路線及局部麻醉藥注射后藥液的擴散和分布情況,能夠完全阻斷手術區域的感覺神經前支,相對腹股溝/髂腹下神經阻滯,并不影響手術切口的解剖層次,能提供更好的手術視野,便于外科操作。手術切口行局麻藥物浸潤能在神經末梢阻斷疼痛信號的傳導[11],對這類不用進腹腔手術能提供良好的術后鎮痛,但在臨床操作過程中,鎮痛效果和外科醫生在行局部浸潤阻滯時進針深度和寬度的操作技巧上有一定關系。
綜上所述,超聲引導下行TAP 阻滯和切口局麻藥浸潤阻滯均可明顯減輕腹壁切口痛,提供較長的鎮痛時間和效能,對胃腸道和泌尿系統功能的影響小,可作為腹股溝斜疝患兒手術術后鎮痛效果的較佳鎮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