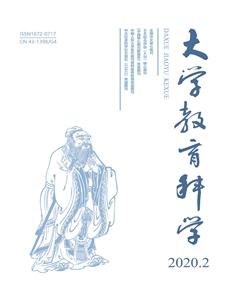大學評教“共謀”行為及其治理路徑
蔣貴友 郭麗君
摘要: 隨著高校教學評價的管理主義傾向不斷強化,基層教學單位與教師在執行上級組織的評教政策時共同謀劃,以應對各項教學檢查與突發狀況,這種共謀行為并不鮮見。大學評教共謀行為根植于復雜的組織制度環境,它的出現與重復再生是高校制度環境與評教實施之間的不兼容所導致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校集權決策、教學懲治機制強化以及組織制度理性化所導致的非預期結果。然而,這一非正式行為在周期性生發過程中逐漸合法化與制度化,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教學評價的各個環節。為此,高校應從外部規范的管理制度與內部平衡的發展機制兩個層面來共同構建大學評教運行的有序局面。
關鍵詞:教學評價;共謀現象;制度分析;教學發展;治理路徑
中圖分類號:G6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0)02-0105-06
一、問題的提出
在高校教學評價活動中,基層學院不僅作為教務管理部門與一線教師之間的紐帶,還扮演著教師教學活動的監督者與管理者角色。除了評教組織外,高校科層化的內部教學組織均被視作理性的單元,高校通過組織間的有效互動確保教學秩序的穩定。但是,現代學校作為開放系統中的一個動態組織難免受到政策制度、文化觀念以及經濟政治的影響,這便導致教學活動中出現了諸多與政策不一致的靈活做法[1]。然而,這類變通行為早已成為教學評價制度運行過程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也即,基層教學單位常與教師共同謀劃應對更上一級組織的政策規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措施聯合應付評價過程的各項檢查[2]。因此,這便導致評教實踐活動嚴重偏離了制度設計的初衷。
高校教學評價在提供學生、同行以及督導評教之意見并改進教學質量的同時,也為不同評教組織與主體之間的共謀互動構筑了組織基礎與制度環境。具體而言,教師之間的聯合變通主要發生在同行評教中,表現為互評高分[3];在學生評教中,教師評學與學生評教的共謀催生了彼此的分數膨脹[4];而教師與基層教學組織間的非正式互動卻存在于任何評教場景中,主要表現為對教學丑聞和教學事故的相互遮掩與消息封鎖[5]。但對教學事故的遮掩、包庇抑或化解,均與高校教學管理制度的正式規定相違背。與正式評教相比,這類行為都是通過非正式手段與方式予以落實的,具有隱蔽性與非常規性特征。周雪光早已觀察到基層政府間存在的非正式行為,并用“共謀”一詞來概括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變通現象[6]。對此,本文亦將教學評價過程中出現的、與制度期待不一致的非正式行為稱之為大學評教的共謀行為。
教師、學生與基層教學組織間的共謀是高校不愿意看到甚至是厲行禁止的,但這類行為仍然反復發生。這意味著,教師與組織間的共謀已經牢牢建筑在高校內部的制度基礎與組織環境中,并逐漸演變為常態化的非正式行為。在實際過程中,區分度較低的同行評教、走向分數高位的學生評教以及基層教學組織虛報評教等情況均已被教務處與各教學單位所默認與接受。由于高校內部長期存在教學活動的利益協調問題,這一共謀行為逐漸在組織環境中具備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礎。隨著評教共謀行為屢試不爽,它慢慢反復發生、穩定存在,并不斷催生出評教制度內的“共享常識”(Common Knowledge)牢牢融入教師與組織的觀念體系與行為邏輯中。因此,本文主要著眼于大學評教過程中與正式規則相悖的非正式行為,試圖剖析這一行為的具體表現以及發生動因,探尋該現象為何合法地存在于大學場域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治理路徑。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文采取質性研究的方法,對20位高校教師與8位學生進行訪談。受訪的高校教師中既有從事教學的教授與青年教師,也有參與教學質量監測與評價的教務管理者。此外,研究還抽取了受訪教師所在高校的學生樣本,旨在對教師為主的訪談進行補充。由于單一方法收集資料有限,本文采用半結構化訪談與敘述的方法策略。受訪教師的敘述涉及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屬于本體論敘述,主要涉及教學評價制度運行與教師教學過程等內容;第二個層次屬于分析層面的敘述,主要將教師個人的敘述放置于高校制度環境與組織變遷中予以考察,這有助于理解不同教師與基層院系的評教互動情況。
除了敘述與訪談外,本文還通過課堂觀察、制度文本分析與訪談資料進行三角互證,進一步核準研究資料的真實性。在資料搜集中,本研究通過三種策略以確保分析資料符合研究所指向的問題。首先,研究進行了歷時較長且反復多輪的訪談與觀察,這不僅強化了教師的評教經驗,還促進了雙方對于評教共謀內涵的理解。其次,為了獲取訪談資料的最大飽和信息,研究選取不同地區、院校層次以及教齡職稱的教師進行深度訪談,直到多名教師的訪談資料沒有呈現新的信息特征時才結束訪談工作。最后,本研究不斷進行反思與比較,從受訪者的回答出發進一步反思訪談過程中的突發情況以及失誤,確保資料處理過程客觀有效。總之,本文圍繞問題展開調查,將訪談資料進行處理并轉化為概念工具與分析框架,力爭回答大學評教共謀行為發生的深層原因。
三、大學評教共謀行為的組織制度分析
“共謀行為”研究早先出現在經濟學領域,意指幾個大公司通過非正式手段瓜分市場,謀求壟斷地位的經濟行為[7]。在評教過程中的共謀行為主要是指高校教師與不同評教主體相互聯合,采取各種對策應對更上級部門的教學評價或教學檢查以達成個人或組織目標。基于組織制度的分析,這種非正式的評教共謀主要是由于高校組織環境與評教制度實施間的不兼容及其矛盾所導致的。
(一)制度統一性與執行靈活性的矛盾
高校教學評價制度具有統一的制度效力與規制權威。教務處作為評教活動的組織者與實施者,通過多主體評教對各教學單位以及教師教學進行標準化考核。但由于實施統一的評教制度成本過大,教務處可能會將部分評教權限委托給基層教學組織,讓學院自主開展內部教學質量評價與監控工作。于是,在評教任務的發包過程中,權力分配、內部控制與經濟刺激成為組織內部有效治理與穩定互動的主要措施[8]。除了賦予評教自主權外,高校還通過設置校院兩級教務管理的垂直化組織以及將評教實施效果與教學單位的目標考核掛鉤,以便通過內部控制與利益刺激維系教學評價制度效力與實施效果的統一性。但是,評教制度的統一性也給予了基層學院更大的執行空間。由于校、院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基層院系擁有對評教形式與數據采集等內容的決定權與解釋權。對于教務處而言,囿于有限的制度激勵效應與不完善的制度設計,他們只能將基層數據作為正式的教學質量評估結果予以采納。
評教制度執行靈活性存在多種形式。一是制度運行本身存在靈活空間。在行政發包過程中,評教權限被交付給基層學院的同時,也拓寬了學院靈活處理的制度空間。二是基層學院運用不同手段“拼湊應對”以完成評教任務。在制度性的教學檢查中,基層院系存在諸多成果替換、信息造假的拼湊行為,這是教學管理與運行中的效率機制所決定的。三是即使評教制度是合理的,但是一旦嵌入到多元制度背景中,不管組織還是個人都可能會圍繞利益這個核心點靈活操作。由于教務處有限度的督查范圍與多層次的評教范圍之間的矛盾對立,導致了評教徇私舞弊以及結果虛報等現象層出不窮。隨著基層組織靈活性被不斷增大,教師與基層學院間的共謀行為將被賦予更多的合法性基礎,也即制度統一性與執行靈活性之間的矛盾成就了評教共謀的組織基礎與制度環境。
(二)教學懲治強度與組織目標替代的沖突
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下,大學評教中“評”的工具理性不斷被強化,而“教”的價值理性被逐漸遮蔽、異化甚至是集體性失語。二者力量此消彼長的現象導致了評教的激勵與懲治失當[9]。通常而言,教學評價結果被用作獎優罰劣的依據,而這一制度性獎懲機制僅覆蓋少數教師群體,使得大多數教師絕緣于評教激勵。與此相反,高校為了維系教學質量的最后底線,通常建立了與激勵強度截然不同的懲治強度。一旦上級組織發現教師教學事故,基層組織與教師個人在考核中將會面臨一票否決。然而,這一懲治機制實際上很少在教學事故預防和發生時發揮作用,常常還適得其反。究其緣由,應在于教學事故的懲治目標與基層教學單位的組織目標相沖突。正是由于制度執行過程中矛盾與沖突的存在,不僅助推了作為懲治對象的組織與教師等利益相關者相互聯合,為二者間共謀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前提性條件,而且還進一步導致了上級組織的懲治目標被基層教學組織的其他目標所替代。
在教學事故或者評教結果產生后,基層學院的組織目標通常不是啟動審查以及啟動懲治程序,而是通過說服、作假以及脅迫等方式應付或者阻止相關人員將信息上報。具體而言,高校對基層教學單位以及教師有較強的懲治力度,其結果表現為扣除目標管理分、一票否決以及取消評優等。這一嚴厲的教學考核機制,迫使基層教學組織與教師發生非正式與隱蔽的共謀行為,以便替換掉上級組織的懲治目標而使其免于處罰。這一目標替代現象在評教活動中層出不窮且隨著教學懲治力度越大,組織內部的替代目標活動也越來越頻繁,這更進一步地催生教師與基層教學組織間的共謀行為。
(三)組織制度理性化與基層關系人情化的悖論
組織與制度是現代社會理性原則下的產物。高校通過評教內容條目化、管理層級化與保障體系化等方式,不僅幫助教師在學生評教、同行評教或督導評教中獲取不同立場的意見與反饋,還使教學活動在評教制度約束與規訓下朝著既定的目標發展。根據組織實施與制度設計的理性原則,正式的評教行為應該取代非正式的共謀行為。但是在實際評教中,教師與教學組織、教學組織與管理組織間的對話與互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通過非正式的特殊關系予以維持并且逐漸強化。這是因為科層化的行政部門與扁平化的學術機構相互交錯為行政人員與基層教師之間的對話、交往乃至建立社會關系提供了現實基礎,也為正式關系與非正式關系同時并存創造了條件。對于教師或者基層組織而言,即使評教活動是一項常規化的組織任務,但也需要防范伴隨著評教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風險。出于對風險的管控,教師與基層教學組織的非正式互動程度被逐漸強化,并演變為人情化了的基層關系。
評教過程中的共謀行為建立在非正式關系基礎上,而這種關系牢牢嵌入基層關系人情化的社會網絡中。這就意味著社會關系網絡與共謀行為之間已經形成了相互轉化的效應遞增機制。一方面,評教任務執行過程中產生的非正式行為需求滋生了人情化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牢固的基層關系為評教任務過程中的共謀行為賦予了更多的確定性因素。從更深層次來看,正是由于制度悖論空間的存在,共謀行為才會由制度化的管理機制所生產并憑借社會關系反復出現[10]。因此,無論組織制度如何理性,教師或基層學院可能會通過經營社會關系網絡來共同抵御評教政策執行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最終達成組織或個人利益的共贏。
四、大學評教過程中的多元共謀行為
大學評教的共謀行為不是制度運行過程中的隨機化產物,它在周期性生發過程中具備了合法性基礎的同時,還以多種形式滲透到教學的各個環節。因此,高校組織與教師的行為邏輯會隨著制度環境的變化而轉換。這意味著,不同共謀利益群體在評教主體、標準與環境的變化下,隨時發生解體或者擴容。即使教學評價是定時發生與偶然性排查的常規活動,但是在實際過程中無處不存在著更廣義的多元共謀行為。
(一)信息控制下的包庇行為
相較于教學評價制度,科研評價制度會產生更大的激勵與聲譽效應,誘發高校教師主動地參與學術活動。談及教學與科研關系時,多數受訪教師表示難以保障充足的教學投入,而且還存在調課、遲到或壓縮課時等情況。為了獲取更多的學術資本,教師將教學時間逐漸讓渡于學術活動,并通過非正式手段為教學“減負”。一旦發生教師無故調課或遲到導致學生不滿的情況時,基層院系常常會對該類事故進行調解與控制,旨在預防學生及教師將組織內部的問題轉變為組織外部的危機。當教學事故發生后,學院會為教師利益進行隱性辯護,表面上努力消解學生的不公情緒并想方設法解決問題,但實際上是對相關事故進行包庇與控制,防止信息的逐級擴散。因此,學院或教師作為被考核檢查的一方總會蟄伏在現實場景與虛擬空間中,或通過控制學生與教師群體中的關鍵性人物,以完成對教學環節的信息控制。
如果信息控制難以發揮作用,那么基層包庇與作假行為便會應運而生。教務處與學院教務辦公室處于一種上下級關系,學院教務秘書理所應當極力配合甚至服從上級教務部門的工作要求。但在現實中,即便教務處控制與監督著評教的各個環節,卻因為評教信息的不對稱性與模糊性,基層教學組織總是能夠策略性地化解教學檢查與考核過程中的隨機性危機,且擁有對問題解釋信息的加工、美化以及策略性回應的優勢。這就意味著,無論評教過程中發現何種問題,基層教學組織總是占據信息優勢與主動權,并通過包庇、作弊策略影響上級管理部門的檢查結果甚至是扭轉問題的評判。
(二)共享常識下的身份認同
越上層的行政部門,其教學質量檢查頻率越低,但所對應的獎懲力度卻越大。盡管高校行政與教學呈現為管理與被管理的二元對立關系,但作為被管理者的教師與作為考核方的行政人員,他們共處于科層化的行政機構與扁平化的學術組織相互交叉的基層院系中,使二者之間的關系處于一種親密但又對立的張力中。通常而言,高校行政與教學人員之間的沖突主要集中在利益分配上,然而不同的身份歸屬更是加劇了關系間的緊張。基層學院為了緩和行政與教學人員的沖突與對立,常通過設置制度化的組織活動使行政與學術群體走向融合。這就可能改變了學術共同體與科層組織之間的物理距離,使二者共享一套經驗常識與文化規則,并逐步加深彼此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感還體現在組織身份的雙重屬性上,一旦充當考核教師教學的基層教務部門或行政人員面臨更高的評教組織時,他們的考核角色隨即轉變為被考核方。因此,各級評教組織便同時兼具“考核”與“被考核”的雙重身份。
這種雙重角色為組織中的個人或群體共享一套經驗、規則與文化并為上升到集體化的組織認同提供了身份基礎。自上而下的組織評教使下級教學單位、管理組織與教師間結成一種暫時性的契約關系,即共同策略性地降低與化解上級組織教學考核的風險。正是組織間的身份默契,原先互為對立與疏離的考核方與被考核方會迅速建立起基于經驗與常識的身份認同。而這種局內與局外的身份互換,代表著正式且理性的高校科層權力關系邁向了一種不穩定與非正式的合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組織制度的統一性與有效性,為評教活動的共謀行為提供了觀念認同與文化共享基礎。
(三)熟人關系下的制度軟約束
基層組織間通過一套認知與情感的共享機制完成身份認同并做出符合利益的共謀行為。這一共謀過程并非完全由身份認同機制所主導,還受到社會關系網絡的影響。熟人關系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以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而人們憑借關系的親疏遠近賦予彼此的權利與義務[11]。高校同樣作為熟人社會,這一組織特征使教師被置于立體化的社會網絡節點中,擁有了多重維度的人際關系[12]。盡管教學評價是基于組織理性與效率原則的制度安排,但是教師所嵌入的社會網絡會生成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以抵御組織制度的強制規范。面對評教制度的理性規約,基于利益需求的高校教師群體會形成非正式化的自然系統,并圍繞利益與人情關系而發生群體性共謀行為。基于此,教學評價的考核規則與監督程序逐漸被儀式化與空心化,并由教師群體中所默認的非正式運作手段所取代。
高校熟人社會中同樣充斥著人情與面子,此背后勾連出的不同權力源泉成為評教共謀的基本運作方式[13]。一是通過互惠機制達成觀念與行動上的默契。評教活動的封閉系統削弱了評教過程與結果的權威性、獨立性與公正性。譬如,學生與同行教師會依據與受評教師之間的關系遠近而決定教師教學效果的優劣。由于均衡互惠的人情規則,互評高分成為了教師間的資源互換,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就具有了不可讓渡性且要求接受者必須完成對等的義務與責任。因此,普遍的“教學優秀”成為不同教師群體間的共同選擇。二是通過關系網絡抵御評教過程中的不確定風險。當教師與評教主體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礎時,他們在既有的互惠交換中建立起更為長期與穩定的關系網絡,并逐漸演化為隱性且合法的利益共生體。特別是極強的懲治機制使教師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這也推動教師與組織內部彼此建立起合作型社會網絡,以弱化非人性化的評教規章制度。
四、大學評教共謀行為的治理路徑
大學評教共謀行為根植于復雜的組織制度環境,它的出現與重復再生是高校制度環境與評教實施之間的不兼容與矛盾所導致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校集權決策、教學懲治力度強化以及組織制度理性化所導致的非預期結果。為此,高校應從外部規范的管理制度與內部平衡的發展機制兩個層面來共同構建大學評教運行的有序局面。
(一)構建評教協同機制,提升評教組織化水平
由于評教制度實施范圍較大、參與主體較多以及評價反饋鏈條較長等因素,導致高校將部分的評教實施權與監督權委托給基層學院。這種權力上的讓渡形成了“委托-代理”組織間的信息不對稱,并導致偏離評教制度的靈活執行現象出現。面對評教共謀現象時,高校并未嚴格按照規章制度予以懲治,而是秉持不發生教學事故的底線原則進行處理。這一妥協與模糊的態度間接加劇了評教共謀行為的反復發生,最終造成了大學治理的困境。簡言之,評教決策與實施的不兼容程度和高校評教決策的集權程度成正比,而評教共謀行為正是高校實施統一制度所應付出的代價。對此,高校理應在評教制度設計與決策過程中將基層學院納入其中,以便賦予其更大的決策權與參與權,并促使傳統的科層化評教組織向扁平化的協商組織轉型。但是,高校扁平化的評教組織結構不是松散的聯結體,而是結構性的評教協同網絡。通過構建評教過程中的協同機制,高校不僅可以有效落實評教組織與主體的權責,還可以引入第三方評教監督機構以便進一步厘清評教決策、實施與監督三者間的職責邊界,更大程度地激發與釋放評教組織與制度的效能。為了解決評教制度決策與實施相分離的問題,高校有必要通過構建評教過程中的協同治理體系以解決層級分割式評教管理體制所帶來的失敗。其實,構建評教協同機制并不是為了去組織化,而是為了有效評教的再組織化。因此,高校構建評教協調機制,能夠通過協商與共治等方式使不同治理主體組成結構化的評教制度體系。
(二)轉變評教制度取向,推動教師教學發展
教學評價作為一種教學規范制度,既需要滿足作為評價工具的管理效率,又需要維系扎根在教學實踐中符合教學價值的合法性基礎。但如果基于行政制度上的教學評價逐漸轉變為以管理效率作為核心取向,并過度介入到教學活動中進行細密地管控的話,那么,身處管理環境中的基層學院與教師群體為了應對來自上級教學行政部門的管理與問責,便會在評教過程中達成共謀以消解隨機評教的不確定風險。當然,教學評價的管理規范功能有其存在價值,但是這種功能被放大到整個教學評價環節便會演化為應付評教的另一種管理困境。針對這一情況,高校有必要在管理規范與教學價值的兩種教學評價制度取向之間尋求平衡。一方面,高校應加強內部評教監督與獎懲力度。評教制度的執行靈活性以及組織目標替代的常態化意味著評教過程中的共謀行為的失敗代價很小,而教學評價的獎懲機制比較有限。高校除了強化第三方評教組織的監督力度外,還需要設置不同層次與范圍的評教激勵與懲治機制,以此突破評教共謀行為所形成的利益圈圍。另一方面,高校應轉變評教制度的管理主義取向。大學評教共謀現象足以說明,持續性的激勵或懲治只會為教學管理帶來更加僵化與失控的局面。為此,立足于管理規范的基礎上,高校還應凸顯教學評價制度的發展性功能[14]。這就意味著,教學評價既需要在分等的評教結果中繼續進行分類指導,還要求尊重教學差異與呵護教學個性。因此,高校唯有實施管理與培養聯動的評教運行機制,才能將教學評價與教師發展共置于教學質量的連續統一體中,最終實現有機融合,并改變教師與組織之間的對立或利益共生關系,從而消除評教共謀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三)培育評教制度環境,促進教學共識達成
即使正式制度改變了,但非正式約束并沒有隨之消失,且后者還會與新的正式制度之間產生一種持續的張力,這是由于它們在諸多方面都無法兼容所導致的[15]。同樣,高校教學評價雖然轉變了制度取向,但是舊有的文化慣習、地方性知識與社會規約仍在教學評價過程中透過非正式約束發揮作用,會使新生的評教制度逐漸儀式化、空心化。那么,除了變更教學評價的正式規則外,高校仍需要重塑適于發展性評教的制度環境,而這背后離不開學術共同體的支持與參與。從知識生產的學術觀分析,高校教學評價不僅是知識應用的實踐場所,也是不同主體通過評議、診斷與協商方式不斷生產新知識的制度土壤。因此,高校應該積極培育以合作與共享為核心的評教制度環境,推動教學層面的學術共同體建設,以此淡化高校熟人關系網絡所產生的影響效力。再者,高校學術共同體的培育會進一步促進教學共識的達成。教學共識是不同主體對于教學的一種共享理解,旨在規范與約束教學組織管理活動與教師教學行動。可以說,學術共同體所達成的教學共識不僅強調不同主體在評教制度決策與實施時所應遵循的默契,而且還通過觀念系統影響組織集體的行為邏輯,并以此維護教學秩序。那么,學術共同體的培育與教學共識的達成便會反向營造利于教學發展的評教制度環境,進而有效解決大學評教的共謀問題。
參考文獻
[1] 嚴玉萍.大學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基于組織文化和制度領導的視角——以北歐五所大學為例[J].大學教育科學,2018(04):78-83+90.
[2] 劉佳.第四代評價理論視閾下高校教學評價制度的反思與重建[J].教育發展研究,2015(17):56-61.
[3] 郭麗君,蔣貴友.高校教學同行評議的制度化困境研究——新制度主義視角的分析[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9(03):100-104.
[4] 哈巍,趙穎.教學相“漲”:高校學生成績和評教分數雙重膨脹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9(01):84-105+243-244.
[5] 孫鰲.分數膨脹的博弈分析[J].現代大學教育,2016 (05):23-27.
[6] 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8(06):1-21+243.
[7] 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196.
[8] 周黎安.行政發包制[J].社會,2014(06):1-38.
[9] 郭麗君.走向為教學的評價:地方高校教學評價制度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06):68-73.
[10] John W.Meyer,Brian Rowa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 (02):340-363.
[11]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12] 胡娟.熟人社會、科層制與大學治理[J].高等教育研究,2019(02):10-17.
[13] 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62-164.
[14] 張男星.以OBE理念推進高校專業教育質量提升[J].大學教育科學,2019(02):11-13+122.
[15] [美]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杭行,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125.
The Collusion Behavior of University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Path
JIANG Gui-you ?GUO Li-ju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tendency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rdinary teaching departments and teachers plan together when they implement the evaluation policies organized by their superior authorities, so as to cope with the endless collusion in various teaching inspections and emergencies. The collusion behavior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rooted in the complex organizational system environment. Its emergence and repeated regeneration are the result of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Significantly, it is also the unexpected result of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eaching punishment mechanism,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for teaching evaluation. However, this informal behavior is gradually leg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periodic development, and exists in various aspect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different form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llusion in evaluating teach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truct an orderly situ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wo aspects, the external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teaching evaluation; collusion behavior;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eaching development; governance path
(責任編輯 ?陳劍光)
收稿日期:2019-11-19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規劃教育學一般課題“大學教師發展視野下的高校教學評價制度研究”(BIA20170209)。
作者簡介:蔣貴友(1993-),男,湖南洪江人,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上海,200062;郭麗君,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沙,4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