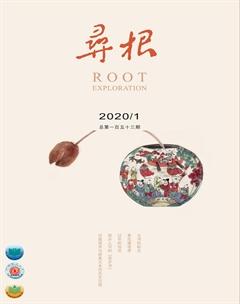出版技術與經典文本的歷史遷徙
耿相新
中國古代的學術傳統偏重于闡釋和整理,這一學風的養成也許源自孔子的“述而不作”,孔子在《論語》中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里的“作”指立論創說,是指前人所沒有的,作者最早發現、發明而書寫下來的;而“述”則是在前人創作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是闡述前人學說的。這一文明奠基時期的學術趨向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的發展方向。孔子之后的兩千年里,中國古代產生的述論類書籍遠遠超過創作類書籍,經部書籍尤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人皓首窮經,不斷地搜集、整理前人的經典著作,重新編輯、編纂、校勘、校注、解釋、輯佚、鉤沉、刊刻、印行,這一考據式的學術傳統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王鋼先生的《中原文獻整理史稿》正是從區域史的角度對這一文化傳統的進一步揭示。
以整理來闡發自己的學術主張,其發端者可追溯到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國語·魯語》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孔穎達《毛詩正義》解釋曰:“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正考父是春秋時期宋國的大夫,而宋國的立國者是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啟,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微子啟于商丘,特準其用天子禮樂奉商朝宗祀,因此才有正考父校正禮樂商之頌歌。正考父校正之名頌十二篇,到了孔子刪詩之后,今傳本《詩經》中的《商頌》僅剩五篇,即《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由此,也可以佐證,孔子的確是刪過《詩》的。《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也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孔子并沒有寫過《詩經》中的任何一首詩,但他是周詩的整理者之一,卻是毫無疑問的。
眾所周知,“六經”是中國文明的圣典,其地位相當于《圣經》之于西方。“六經”自身的文字都是原創的,但其成書卻經歷了漫長的整理過程。而孔子正是抱著“述而不作”的態度對“六經”進行了校勘式的編纂整理,可以說,孔子是“六經”成書的關鍵人物。對此,《史記·孔子世家》多有記述,如: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
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由以上記載可知,孔子的思想隱藏在他整理的典籍文字中,他是借古人以抒己懷,借諷古而喻今,借前事而啟來世。
如果站在出版史的角度去研究孔子的編輯經典行為,我們可以理解為孔子實際上是將口語材料和零亂零散的文字材料進行了內容分類式的重新排定,是將那些可能書寫在玉版、石頭、木牘、竹簡、縑帛,或者銘刻于青銅器物上的眾多單篇內容進行重新分類,以定本形式將其轉寫到竹簡上,將此定本作為材料以傳授學生。從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的記載可以得知,孔子時代的書籍材料主流已是竹簡。因此,我們可以說竹簡本“六經”是中國經典的最早書籍形式。
從書籍史的角度來觀察經典書籍的物質呈現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次文字載體材料的變化都造成了書籍形式的變化,而每一次書籍呈現方式的變化都需要將存儲于原載體材料上的內容進行一次再轉移。毫無疑問,每一次的內容轉換都需要重新審視以前的內容價值與意義,需要對內容重新整理、重新書寫或重新復制到新的載體材料上,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產生新的錯誤,以致不得不多次進行新的考據和考證。換句話說,知識內容遷徙的過程是一個文本的篩選過程,也是一個不斷修訂文本的過程,更是一個文本經典化的過程。
以書寫符號系統為特征的文字書面語傳播是一場巨大的傳播革命。從相信口頭語言到信任文字證明促成了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承,同時也更有利于傳播到更遠的地理空間。《詩》從歌唱傳播轉變為文字傳播,盡管丟失了很多情感的信息,但書面化讓《詩》傳播得更遠并且傳承到了今天。我們很難想象,如果孔子時代沒有將《詩》記錄在竹簡或縑帛上,我們今天還能不能見到《詩》的文本?《詩經》的文本經過秦朝的焚書,傳至漢初今文一派已分三個版本系統:一為魯人申培公所傳《魯詩》,二為齊人轅固生所傳《齊詩》,三為燕人韓嬰所傳《韓詩》。此三家皆為今文經學,文景之時就已立學官,設博士,是為官學系統。《漢書·藝文志》著錄詩類書籍,四百一十六卷中三百五十七卷為今文《詩經》。此后,與之相對應的是古文《詩經》,僅著錄《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詩》傳自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但未被列入漢朝廷所審定的漢學系統,一直作為私學流傳于民間。其余四經,《易》《書》《禮》《春秋》與《詩》也大抵類似,皆分為官學和私學,更分為古文與今文。所謂今古文之分,所指乃“今文用以書寫的是隸書,古文用以書寫的是一種與籀文、小篆都不同的古文字”,王國維認為古文經乃是在籀文之前的一種字體。以不同字體而傳抄下來的經典文本,在漢代形成嚴格的師法、家法,二者勢同水火不相容以至20世紀,有2000多年的紛爭。由此可見,文本遷徙過程并不是簡單的文字傳抄,實際上已上升為學術傳承的意識形態問題。
東漢時期,蔡倫于洛陽改良造紙術之后,中國進入簡帛與紙并用的書寫時代。中國的書籍文本至西晉時期而逐步完成了向紙的遷移,這一文字載體材料的革命不僅導致洛陽紙貴式的書籍傳播變革,而且也引發了學術傳承的動蕩。仍以《詩經》為例,西漢時期盛行的今文《詩》學,至東漢末年隨著鄭玄古文《詩》箋的興起而逐漸式微,《毛詩》《鄭箋》隨著紙材料的流行而開始獨行于世,以訓詁為特色的古文《詩》學開始占據《詩》學主流,至唐代《五經正義》之《毛詩正義》,古文《詩》學達到學術的至尊地位。自東漢末年到唐代,也正是中國紙寫本書籍從產生而至鼎盛的時期。《隋書·經籍志》記錄了這一學術演變過程。其《詩》類文獻著錄四百四十二卷,除《韓詩》三部四十二卷、《齊詩》二十卷外,其余三百八十卷全部是古文《毛詩》,其《詩》小序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從敦煌遺書所出之《詩經》卷子,或抄于六朝,或書寫于唐,但無一不是《毛詩》《鄭箋》。由此實物而可確證《詩經》進入紙之時代,《詩》之文本的遷移淘汰了今文三家《詩》,《詩》之學術潮流為之一變而轉向古文《詩》學。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改變了中國的學術面貌。自初唐以來,雕版印刷首先應用于佛教典籍,其后又應用于民間歷書、字書之類的書籍,晚唐又開始有文人借此技術刊印詩文集。至五代時期,朝廷刊刻“九經”,中國進入紙寫本與雕版印刷并行的歷史時期。自北宋開國,中國的經典文本開始向雕版印刷刊本書籍轉移,到北宋中后期,刊本已經可以與紙寫本書籍平分天下,逐步成為書籍形式的主流。蘇軾曾經說過:“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如此。”以此可知,北宋中期諸子百家之書籍文本已經完成了向刊本的轉換。刊本以身化萬千的優勢,提高了文本傳播的速度,擴大了文本傳播的地理空間,同時也大大延長了書籍的生命力,為研究和誦讀經典文本的個人化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為文本傳播的變化,學術傳承和學術研究為之一大變。
仍以《詩經》學術傳承與學術研究為例,自五代時期《詩經》進入刊本時代。《詩經》的第一個刻本是五代國子監在開封雕版的“九經”版,此刊本的底本是依據唐國子監《開成石經》和《九經字樣》,所刻為鄭玄箋《毛詩》。《詩經》的第二個刊本,其版本是北宋景德至天禧年間國子監據五代監本重刻之“九經”本。此本被廣泛頒賜宗室諸王、朝廷輔臣、各地學校,并允許民間士民納錢刷印,成為北宋時期國家標準教科書,是當時科舉考試重要的參考書。單經注本以外還有南宋國子監重刻之“九經”本,南宋撫州公使庫刻“九經”本和南宋興國軍刻“六經”本等。北宋中期之后,雕版印刷之刊本刻本逐漸成為書籍流傳之主流。尤其是經典著作,不斷地以各種形式闡釋與解說,在白文本之外又涌現出多種更適應市場和閱讀習慣的版本,在官刻之外,坊刻與家刻多家并行,呈現出迥異于手寫本傳播的繁榮景象。兩宋期間,《詩經》刊本舉其要者還有:建本白文本“八經”之一《毛詩》一卷,單疏本紹興府刻本《毛詩正義》四十卷,經注附釋文本廖瑩中世彩堂刻“九經”之《毛詩》二十卷,經注附釋文巾箱本《毛詩》二十卷,“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十二行《纂圖互注毛詩》二十卷圖一卷、十行《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二十卷圖一卷等。眾多刻本《詩經》及闡釋之作的流行,對宋代《詩》學的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概論而言,至少有幾點是別開生面的。一是每一刻本必據底本并參校其他版本互校互勘,這一過程導致了宋代疑經改經活動,疑經辨偽蔚然成為北宋一代學風。如歐陽修懷疑《詩序》的作者,他在《詩本義》中公然提出《詩序》的作者不是子夏,受此影響,《詩》學革新形成潮流。二是從疑經走向訂誤、改經,成為社會思潮。據葉國良《宋代疑經改經考》統計:“兩宋曾疑經改經者一百三十人,若分別南北宋,北宋得四十四人,南宋得八十六人,是南宋疑經改經繼北宋而烈于北宋。”此活動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場質疑經典的大規模的學術運動。自然,此改經風習也造成了更多的舛誤。三是宋代《詩》學革新還體現在釋經方法的變革上,從六朝隋唐以來的注重訓詁而轉為重視闡述義理,此既與重視義理闡發的理學家鼓吹相呼應,同時也可以看出《詩》學受到了理學的浸染。四是宋代說《詩》各家,“務求新義”,破立相并,邊破邊立,這種各求新聲的學術氣氛,造成了大量新角度的研究《詩》學的著作涌現,如歐陽修《毛詩本義》、王安石《詩經新義》、蘇轍《詩集傳》、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朱熹《詩集傳》《詩序辨說》等,尤其朱熹之《詩集傳》是其集大成者,在宋元間執《詩》學牛耳。以上宋代詩學的創新,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雕版印刷術的發達和出版業的繁榮,毫無疑問,學術與出版已經成為一種互相推動的互動關系。
兩宋時期,中國的經典文本已經完成了從寫本到刻本的遷移,它開創并奠定了雕版書籍時期的出版格局,確立并完善了雕版印刷的官刻、坊刻、家刻、書院刻書、寺觀刻書五大系統,明晰并確認了雕版印刷與科舉、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雕版印刷術讓朝廷看到了利用國家定本和國家政府刊本以一統思想的希望,成為了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它可以通過廣泛和快捷的傳播而有效控制帝國的各個角落,尤其是邊疆地區。自孔子編纂、整理“六經”,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再到東漢《熹平石經》、曹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北宋《汴學石經》等儒家經典文本刻石,其目標無一不是企圖借標準文本以統一思想、消弭歧義。但因刻石只能立于京師,傳播效果頗為有限。而雕版印刷術正可彌補不便傳播的缺陷,通過朝廷認定和監造的統一刻本傳播到全國以達到控制思想和統一思想的目的。因此,自五代、北宋以來的各王朝,無一不高度重視雕版印刷的應用,官修大量書籍并將之刊刻以頒賜天下,這一統治術經元、明至清代而達到頂峰。與西方的印刷術造成了拉丁語帝國的分裂正相反,雕版印刷術鞏固了宋、元、明、清帝國的穩定與統治地位。
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尤其是石印技術和輪轉膠印技術在晚清的廣泛應用,瓦解了雕版印刷的統治。隨印刷機而來的是西方的各種思想、自然科學技術和新的學術體系,經學隨著科舉考試制度的廢止而迅速衰落。在新的印刷技術面前,中國傳統的以儒家經典為代表的文本再次面臨新的遷移。中國的文本自清末開始,逐步由線裝刻本轉向洋裝印本,這一過程淘汰了大量的過時內容,中國的經典文本經歷了新的洗禮,這一波技術的沖擊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但在20世紀末期,內容復制技術產生了功能更為強大的新發明,數字技術成為新的拐點。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忽視貫穿整個20世紀的各種動力印刷機的力量。隨著清朝的滅亡,中國的學術從經、史、子、集、佛、道轉向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而傳統的經典不得不在來自西方的分科之學中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仍以《詩經》為例,當退下學術神壇之后,它被視為七科中的文科文學專業之詩歌作品集,而學術研究也隨之而完成從經學研究到文學研究的轉變,現代《詩》學由此而確立新的學術規范。作為文學經典的文本,在向現代印本的轉移過程中,對《詩經》內容的整理,較多地采用了標點、點校、校勘、白話今譯、注釋、鑒賞、選編等形式進行研究和文本再現。《詩》學研究著作體例從漢至清的注疏、經解、集注、集釋、匯編、評論等書籍體裁而轉向今注、今譯、概論、鑒賞集、專題研究等論著形式。研究《詩經》的方法也完全不同于古代,現代《詩》學多以《詩經》內容為史實,將其納入歷史學、文字學、語言學、音韻學、民俗學、史料學、植物學、輯佚學、天文學等范疇,從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學科的不同研究方法重新審視《詩經》文本,對傳統經典進行再闡釋、再解讀、再觀察。
基于計算機的數字信息技術,在20世紀下半葉逐步成長為基礎引領性技術。隨著數據庫和互聯網的普及,文字內容復制技術引發了傳播的革命性變革。文字、圖像、聲頻、視頻等均可以通過數字技術而在互聯網上傳播,數字復制和傳播已深入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經典文本復制和學術研究也不例外。目前,人類經典文本的數字化轉移基本完成,那些有價值的值得保存的文本基本上都轉移到了數據庫、數字圖書館、互聯網上,電子化文檔已成為新的存儲形式。這一次文本的轉移,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徹底。它將徹底刷新文本的存在和呈現形式、文本的使用和檢索方式、文本的復制和傳播方式。互聯網傳播技術是一種全覆蓋的技術,它可以覆蓋以往任何的文本形式,可以以紙質書、電子書、有聲書、視頻書同步呈現的方式復制和傳播文本。這一技術讓經典文本再次獲得新生,其內容的遷徙仍在方興未艾中。
王鋼兄的著作,重點研究和敘述了明清以來600年的中原文獻文本的遷移和出版過程,其資料搜集之廣泛、考據論證之充分、方法觀點之新穎都令我屢屢心生敬佩。這本書是為了論證大型出版工程《中原文庫》出版之必要性,從600年文獻文本整理史的角度揭示了文化傳承的路徑和意義,我完全贊同。他囑我在書前寫幾段話,我便從中國經典文本的歷史遷徙和出版技術之關系,來佐證其書的主題,借此以致敬。希望在書的世界里看到《中原文庫》的書影,這是一代出版人的理想。
(本文系作者為《中原文獻整理史稿》一書所寫的序言,題目為編者所加)
作者單位:中原大地傳媒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