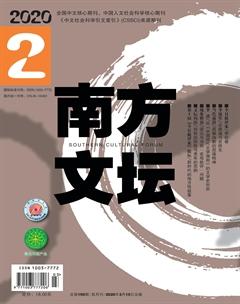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鄉土題材電影研究
徐兆壽 劉強祖
電影是西方工業時代的產物,或許從法國人盧米埃爾兄弟以《工廠大門》《火車進站》等短片翻開世界電影史的第一頁開始,電影就與現代都市有著天然的親近關系。在中國電影史的早期,鄉土電影幾乎處于缺席狀態。當然,這也是與中國文藝思潮的發展相關。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鄉土題材的開掘者乃魯迅先生,沈從文等對鄉土的書寫已經時隔很久,真正進入有意識的鄉土敘事是在左翼文學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是劉再復說的人的第二次解放,即對工農尤其是對農民的解放開始的,這是鄉土文學敘事的自覺時期。從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直到上個世紀末,鄉土敘事則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流敘事。新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和農民工的產生,以及工業社會的發展,鄉土敘事才減弱了其壯闊的聲音,城市敘事開始慢慢崛起。
中國的電影也一樣。第一代導演和第二代導演的作品里鄉土題材比較罕見,直到第三代導演開始,鄉土電影才開始大量涌現。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典型的農耕文明來說,記錄鄉土、書寫鄉土可謂是中國電影繞不開的主題。梳理電影史,我們發現,中國的鄉土電影從新中國成立開始興盛,而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內蓬勃發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四十年間,鄉土電影用影像記錄了鄉土中國的歷史變遷和發展軌跡,成功塑造了變革中的農民群像,展現了時代變遷中鄉土社會的精神蛻變。
一、土地、農民、反思、解放:
計劃經濟時代的鄉土電影(1978—1992)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開始,隨著國內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全面變革和國際電影思潮的涌入,中國電影進入了一個新的變革時期,直到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的確定,這期間,中國電影迎來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電影創作者開始逐漸掙脫“三突出”的文藝創作路線,走出政治一元化和影戲模式的中國電影,向著多元化藝術電影的創作路子不斷前進,呈現出多元發展的繁榮景象,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電影開始匯入壯闊的世界電影海洋。
(一)反思歷史,謳歌新時代
新時期文藝思潮基本是由文學領域最先開始的,復旦大學一年級學生盧新華的《傷痕》從班上的墻報拿到《文匯報》甫一發表,立刻引燃了全社會對剛剛過去時代的反思,緊接著,“傷痕文學”風起云涌。與此相應,與文學緊密相關的電影界也開始將一些小說改編成電影,一時之間,傾訴傷痕、控訴悲劇成了時代的精神主題。《芙蓉鎮》(謝晉導演,1986)、《天云山傳奇》(謝晉執導,1981)、《牧馬人》(謝晉執導,1982)、《月亮灣的笑聲》(徐蘇靈執導,1981)、《柳暗花明》(郭維導演,1979)、《春眠不覺曉》(蘇里執導,1980)、《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李俊執導,1981)等這些由文學改編的電影走街串巷、翻山越嶺,其影像幾乎抵達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上,可以想象這些電影在當時引發的社會反響何等之大。它們異口同聲地揭露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肅反”“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對人的迫害和個體的苦難人生,控訴了政治運動對個人的迫害及對家庭倫理、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破壞,謳歌了新時代的美好生活。《芙蓉鎮》(謝晉導演,1986)、《春眠不覺曉》(蘇里執導,1980)、《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李俊執導,1981)、《張鐵匠的羅曼史》(齊興家執導,1982)、《黃河之濱》(李前寬執導,1984)、《沒有航標的河流》(吳天明執導,1983)、《趙錢孫李》(劉子農執導,1982)等電影還表達了對“文革”等政治運動造成各種人間悲劇的控訴,發出對新時代來臨的渴望和欣喜。當然,《天云山傳奇》(謝晉執導,1981)、《牧馬人》(謝晉執導,1982)、《青春祭》(張暖忻執導,1985)等電影還講述了“文革”等政治運動中鄉土社會對于被迫害者的接納和尊重,謳歌了鄉土社會尚未磨滅的人性之美之善。這令人不能不聯想到張賢亮的電影《綠化樹》,主人公章永麟因為遭遇迫害被下放到偏遠的農村,那里的農民接納了他,而農民婦女馬纓花不僅對他未產生一絲的階級仇恨,相反還對他產生了愛情,最終治愈了他的精神和肉體。不幸的是,“小資知識分子”章永麟只是一時寄寓于鄉村,等到有機會回到城市時還是毅然放棄了曾經醫好他的鄉土世界與女人,這與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異曲同聲,是那個時代城鄉之間文明二元對立的一種顯現。這些思想和人物形象也不時地出現在熒幕上,成為那個時代的人性之痛。
(二)展示新時期農村變革和發展的新收獲。這類電影大致分兩類
一類是歌頌新時代,展示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這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比較明顯。對于農耕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來講,土地制度自古以來就決定著社會的發展。這在歷史上每有體現。一旦土地集中在少數奴隸主或大地主手上時,社會就會形成兩極分化,社會的各種矛盾就急劇上升,最終就會引發社會動亂和革命。據研究土地史的資料顯示,土地制度每隔四百年左右就會有一次大的調整,而這也正好與一個朝代的滅亡相一致。它說明土地制度在根本上決定著歷史的興衰。毛澤東是最早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革命家,在他對湖南農民的調查之后,結合大革命的失敗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里出政權”和武裝農民、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等一系列思想。這是因為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由工人階級完成的命題在以工業社會為主的西方是符合實際的,但在農業社會的中國就不切實際了,要想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與中國的實際問題相結合,這就是要廣泛發動農民,而這一點也是中國的歷史經驗。緊接著,他又提出土地改革的方略,這是因為他發現,要想解放全人類,要想取得社會主義革命,要想推翻封建制度,就必須動員全體農民,而要使農民真正有信心鬧革命并實現與地主階級的平等就必須均貧富,就必須從土地財富這一根本問題入手。所以說,土地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國的實際以及歷史經驗的結合。土地改革革掉了地主的財富,農民得到了土地,極大地激起了廣大的農民反抗地主、反抗封建社會的勇氣和信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這里得到了有力的實踐,中國革命最終取得了勝利。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土地歸國家所有,一切財富皆歸國家所有,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現。均貧富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應當說,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帶著強烈的烏托邦理想,它把人民想象為已經脫離了私欲的君子人格群體,想象為毫無分別的個體,它忽略了人在精神層面的差異性,也忽視了個體之間的千差萬別,而最大的問題則是國家權利對個體自由的剝奪,它最終走向了人性與社會的反面。實事是求、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正是要扭轉這一歷史性的問題,而改革開放則是重新分配土地、重新敞開人性、重建人的自由與尊嚴,發展經濟,尊重和鼓勵人的自由發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共同富裕”。按照《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是社會財富的極大富裕與精神的極大自由,社會主義是通向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過去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不但沒有發展社會財富,使很多人瀕臨死亡的邊緣,而且精神極大地不自由。正是認識到這個實際,鄧小平等第二代國家領導人才確立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也是從這個現實出發,才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農民有了生產收獲的自由權和人身自由,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精神松綁,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得到了強有力的激發與鼓動。這是馬克思主義在實踐遭遇挫折后的快速轉向,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實踐。它承認了個體的差異性,認可了人的自由發展,并用土地激發農民的內在發展動力。1980年代初期思想戰線上的真理大討論不但掃清了社會發展的思想障礙,同時也為文藝創作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動力。電影在這一時期與文學一樣,共同承擔著時代賦予的精神使命,一方面揭示問題,鞭撻丑惡,為時代的發展承擔記錄者的史家責任,另一方面又頌揚時代的美好形象,為時代的發展鼓與呼,承擔精神使者的責任。
《月亮灣的笑聲》《姑娘寨》《咱們的牛百歲》《黃土坡的婆姨們》講述了農村脫貧致富的故事。《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初春》講述的是在新時代的感召下農村青年勇敢追求愛情走向美好婚姻和精神自由的故事。《偷來的愛》《荒雪》《桃園喜》講述農民物質上走向富裕精神上走向自由的幸福歷程。《杏花村》講述了生產責任制政策在農村推行過程中農民由徘徊到欣然接受的心路歷程。
一類是揭示發展中的矛盾沖突和問題。《月亮灣的風波》(中叔皇執導,1984)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迅速富裕的“萬元戶”遭受村里人集體“吃富戶”揩油借錢的困擾。《陳奐生上城》講述了在新時代擺脫窮困的農民陳奐生,被村辦企業選為采購員辦理采購過程中目睹各種不正之風的故事。《野山》(顏學恕導演,1985)、《月月》(琪琴高娃執導,1986)反映了改革時代農民新舊觀念的激烈碰撞及其在此背景之下農民感情和家庭的矛盾、分離和重組。《秋菊打官司》(張藝謀執導,1992)表達了農村社會人情與法制的矛盾沖突。《失信的村莊》(王好為執導,1986)反映了農民們的小農意識和淡薄的法制觀念。《哦,香雪》(王好為執導,1989)表達了城鄉貧富差距,教育不均衡,鄉村對城市的向往,鄉土中國對現代化的渴望。《人生》(吳天明導演,1984),表達了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人進城的渴望和在這種心態之下人性的撕裂和矛盾。《媳婦們的心事》(賈士纮執導,1983)講述了富裕起來的農村忽視計劃生育的問題。《相思女子客店》(董克娜執導,1985)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改革受到舊勢力的重重圍困和遭遇的矛盾沖突。《嫁不出去的姑娘》(陳方千執導,1983)批判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社會過度追求物質利益的婚配觀導致的歪風邪氣。
(三)反思民族歷史和文化
新時期是繼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啟蒙,是對歷史和現實的又一次反思與構建。《黃土地》(陳凱歌導演,1984)反映了抗戰時期舊時代家長的愚昧守舊和青年女性對自由的向往。《老井》(吳天明導演,1987)中對于傳統文化中堅韌不拔代代相傳的與自然抗爭的“老井”精神與傳統“孝道”思想與自由戀愛的矛盾沖突,生存與新思想矛盾的呈現很有力道。《紅高粱》(張藝謀導演,1987)借助抗日戰爭的軀殼張揚了中華民族頑強、充滿血性的生命力和民族精神。《黃河謠》(滕文驥,1989)對于舊時代民族苦難命運的書寫尤為激烈,講述了黃土高原上的民眾生存的苦難和奮斗不息的精神。《菊豆》(張藝謀執導,1990)揭露了儒家封建倫理秩序之下,傳統秩序對于愛情和家庭的損傷,突出了這種家庭悲劇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大紅燈籠高高掛》(張藝謀執導,1991)對于封建禮教對舊時代女性的殘酷迫害的歷史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良家婦女》(黃健中執導,1985)講述了一個嫁給六歲兒童的山村少女陷入“童養媳”這種畸形婚姻的泥潭又努力掙脫的故事,強烈批判了舊時代反人性的畸形婚俗。
(四)講述普通人家的素常日子,展示鄉土社會的風土人情
《百合花》(錢學恪,張昕執導,1981)、《湘女蕭蕭》(謝飛執導,1986)、《邊城》(凌子風執導,1984)分別講述了民國時期鄉土社會溫情又暖心的幾個故事,歌頌了鄉土社會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山道彎彎》(郭陽庭執導,1982)、《飛來的女婿》(中叔皇執導,1982)、《酸辣姻緣》(張寧、宋杰執導,1985)集中講述了農村青年經歷坎坷曲折終于走在一起的情感故事。《鄉情》(胡炳榴、王進執導,1981)、《鄉音》(胡炳榴執導,1983)、《鄉思》(齊士龍、吳安萍執導,1985)、《嫁不出去的姑娘》(陳方千執導,1983)則講述了鄉村男女之間的情感糾葛。《喜盈門》(趙煥章執導,1981)講述了鄉村普通人家的兄弟妯娌之間的矛盾糾葛和走向和睦的故事。以上皆是這一時期鄉村社會的日常書寫。
綜合起來看,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現實主義的回歸。隨著文藝界極左路線“毒瘤”的清除和“雙百”方針的回歸,電影界開始擯棄“假大空”的創作流弊,轉向如實反映現實的軌道上來。這一時期現實主義的理論多依據盧卡契的論述,而在文學實踐上的標尺則以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為高度,中期隨著魔幻現實主義的涌入,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則成為一個時期的文學標高。電影界也基本上遵循著這一理論。故而,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開始關注普通人的生活,人物開始走出“高大全”的英雄窠臼從而走向真實的普通人,開始講述普通人的新的社會轉型時期的命運和日常生活,反映真實的農村風貌和生活狀態。在影像手段方面,大量采用實景拍攝,強調生活化,反對修飾和造景,以保持生活的原生態,并且較多使用長鏡頭來展示鄉村的環境和風貌。在表演方面,重視演員的本色,要求符合農民氣質,甚至起用農民本色出演。第二,新聞性特征明顯,時代氣息濃厚。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不管是控訴政治運動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和人性的迫害,還是謳歌新時代,反映新時代農村生活各方面的發展變化,都強烈凸顯了政治大環境的變革,與社會變革幾乎同步,清晰記錄了國家政策在鄉村社會的變革歷程,時效性強,新聞性特征明顯,這一時期大量的鄉土電影在題材和內容上,可以說是新聞的延伸和細化。正是這種明顯的與現實保持幾乎同步的特征以及現實主義思潮之下強調實景以及生活化的影像特征,使得這一時期的大多數鄉土電影帶有改革開放最初十年的特有的符號,因而辨識度極高。第三,民族化本土化。這一時期,與文學界的“尋根文學”思潮幾乎同步,電影界也開始思考和挖掘民族傳統和文化的意義和營養。以崛起的第五代導演為主力的電影人將視角轉向鄉土和傳統,拍攝了一批優秀的鄉土電影。《黃土地》《紅高粱》《老井》《黃河謠》《野山》等一大批帶有文化尋根色彩的電影大放異彩。這些電影將著力點放在了民族長期以來的生活狀態的呈現、民族性格與民族精神的揭示、民族文化根脈的探尋之上,不僅在主題上反思傳統和文化,同時,也在形式和造型上大量凸顯民俗和民間藝術,“祈雨”“顛轎”“野合”“祭酒”等民俗和嗩吶、民歌等民間藝術在電影中大量出現。正是這種民族化本土化的挖掘,使得鄉土電影帶有了一種深厚性和歷史感,同時也具有了獵奇性,對于本土以外的電影觀眾來說,有了奇觀化的效果,這也是第五代導演一登上影壇就迅速在西方國家電影節上迅速走紅的因素之一。
二、市場、物質、人性、復雜化:
市場經濟時代的鄉土電影(1992—2002)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經濟的復蘇階段,那90年代則是中國經濟開始繁榮發展的階段,標志性和轉折性的事件是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電影的創作環境和觀眾需求發生了很大變化,使得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呈現出了新的變化。社會的每一個轉型時期都是文學藝術發展的黃金時期,它的轉身帶著整個社會的神經陣痛和歡愉,社會思想在發生轉變,各階層人的命運在發生轉折,人的靈魂在面對復雜的社會變化而發出各種聲音,同時,社會也需要重構價值體系,這就為藝術家提供了豐富的在場體驗,為藝術創作提供了激情和理想。作為最具傳播力的電影,更是成為藝術創作的先鋒,而鄉土電影和鄉土文學一樣,還是那個時代的主力軍。
總體來看,隨著改革的深入,90年代的鄉村不再是歡欣鼓舞萬眾祥和的面貌,開始出現走向縱深式發展以后各種矛盾沖突凸顯的現象,出現了繁榮與滯后并存,欣喜與憂患同在的復雜局面,鄉土電影也隨之出現了更加多樣化的形態。在藝術層面上,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則更加深入地思考鄉土社會在新的發展時期的問題。
綜合起來看,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再現鄉村建設和農村發展的新氣象
《荔枝紅了》(周勇、杜云萍執導,2002)、《吳二哥請神》(范元執導,1995)、《巧鳳》(孫沙執導,2001)、《村官李天成》(路振隆執導,2006)講述了村干部帶領村民發家致富的故事。《山鄉情悠悠》(黃喬執導,2000)、《香香鬧油坊》(滕文驥執導,1994)、《喜蓮》(孫沙執導,1996)、《媳婦你當家》(于杰執導,1998)講述了有為青年農民用勤勞和智慧克服重重困難從貧窮走向富裕的發展之路。《二十五個孩子一個爹》講述了發家致富的村民趙光收養孤兒積德行善的故事。《光榮的憤怒》(曹保平執導,2007)講述了村干部用謀略制服村霸肅清鄉村社會環境的故事。《男婦女主任》(張惠中執導,1998)講述了機緣巧合之下村民劉一本當上婦女主任為村民解決實際困難引發一系列笑話的喜劇故事。
(二)探討發展中的社會問題
首先是農村教育落后問題。《鳳凰琴》(何群執導,1994)、《一個都不能少》(張藝謀執導,1999)、《美麗的大腳》(楊亞洲執導,2002)從不同層面反映出鄉村教育的落后,贊揚了鄉村教師在教育環境差、師資短缺的艱苦環境下,憑著一腔熱情苦苦支撐、無私奉獻的美麗心靈。其次是情與法的糾纏。《被告山杠爺》(范元執導,1994)通過一個沒有原告的鄉村殺人案,探討了農村在國家法律與鄉村道德規約之間、法治與人治之間含混而復雜的沖突。《秋菊打官司》(張藝謀執導,1992)探討了90年代法制觀念淡薄的鄉土社會在人情和法律之間難以融合的尷尬現實。再次是物質化觀念的滋生。《二嫫》(周曉文執導,1994)講述了村婦二嫫為了贏回在村里的地位,買一臺連縣長都買不起的大電視拼命掙錢甚至不惜賣血最終勞累過度身體虛脫的故事。
(三)展示鄉土社會的浪漫風情
《那山 那人 那狗》(霍建起執導,1999)通過即將退休的鄉郵員陪著接班鄉郵員的兒子走郵路的所見所聞及其父子從隔膜到親近的過程,展示了鄉村的親情美與人情美。《我的父親母親》(張藝謀執導,1999)講述了善良美麗的農村姑娘愛上鄉村教師并勇敢追求,自由戀愛的故事。
(四)反映鄉村道德倫理和鄉村生活的苦難
《香魂女》(謝飛執導,1993)中農村婦女香二嫂從小被賣作童養媳嫁給了瘸腿的酒鬼丈夫,最后她又想方設法為自己的傻兒子買了美麗賢惠的姑娘環環為媳婦,復制了另一個悲劇。《五魁》(黃建新執導,1994)講述了窮漢子五魁作為長工與主家一過門就死了丈夫的少奶奶偷情并最終以土匪身份劫走受到夫家虐待的少奶奶的另類故事。《九香》(孫沙執導,1994)講述了農村寡婦九香獨自一人撫養幾個子女長大成人,得了不治之癥臨死前返回農村的苦難故事。
這一時期鄉土電影的特點比較明顯:第一,對現實的反映更加深入,更見人性的復雜。進入90年代,經過十來年的發展,農民的溫飽問題得到徹底解決,物質生活有了大幅度改善,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推行、依法治國方略的實行,對外開放逐步深入,使得農村社會處在動態變化的過程之中,經濟發展與道德、法律、人情、傳統風俗、宗法制度之間,城鄉之間,地域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更加錯綜復雜,社會的變革也更加劇烈。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深刻反映出了這一時期鄉村的現實生活。在題材方面,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對于現實的反映更加深入和細化,對于社會、人心、變革、矛盾的反映更加深入到位,叩擊時代脈搏的能力更為強大。相比80年代,故事更為復雜曲折,技法也更為純熟和多樣。第二,浪漫主義的涌現。《我的父親母親》《那山 那人 那狗》以詩意化的視覺語言營造了唯美純情的愛情故事,展示了純真、善良、友善的鄉村生活中的人情美。這些電影的時代感比較模糊,弱化了對于物質生活的展現,抽離了龐雜的矛盾沖突,集中表現了鄉村社會烏托邦式的唯美和純真。這種浪漫主義與抒情性緊密相連,影片在緊湊集中的故事線索之上,以抒情性的散漫節奏充分表達了人物的內心情感,同時也使主題的表達得到了升華。另外,影片的畫面十分考究,精心營造了鄉村唯美的風景圖畫。通過大量的景物刻畫,襯托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和鄉土社會的優美人性,營造出了影片的意境之美。第三,國際化商業化融合明顯。進入90年代,鄉土電影開始在國際電影節頻頻獲獎,《秋菊打官司》《香魂女》《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那山 那人 那狗》等先后在國際上獲得大獎并在多個國家上映。事實上,這些大獎的獲得與前期導演們國際化和商業化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電影開始積極融入國際電影市場,在投資、發行、評獎等領域都在努力嘗試。與這種訴求相適應,電影導演們開始在藝術性與商業性、民族化與國際化的多種訴求中探尋融合的可能性。在此種訴求之下,鄉土電影在題材上大幅增加了商業化和國際化元素,通過各種手段增加電影的奇觀性。其一,欲望和倫理的矛盾更加突出。《香魂女》《五魁》《美麗的大腳》等影片中的亂倫、偷情等關涉欲望的情節和畫面開始大量涌現。其二,民俗、民間技藝的引入。《我的父親母親》里的鋦碗、織布等傳統技藝,《五魁》里的背媳婦的習俗,《那山 那人 那狗》里的篝火晚會,都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電影在營造奇觀化的影像效果上所做的努力。
三、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娛樂化:
全球化時代的鄉土電影(2002—2011)
市場經濟運行十年間,中國社會固有的一些價值遭遇尷尬或沖擊。比如1993年左右發生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就是原有的幾代人的人道主義觀念和精英立場遭遇大眾文化的沖擊,此后,大眾文化像海水一樣涌入中國,精英立場一次次退潮。中國傳統社會所固守的價值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所固守的價值在此時被松動、沖擊并破壁。在文學界,先有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引發的欲望描寫討論和林白、陳染的私人寫作爭論,后有衛慧等美女寫作和身體寫作現象的出現,到新世紀初網絡興起后出現了木子美的性愛日記,欲望化書寫和女性主義達到極端。它們說明中國人原有的道德倫理的底線一次次被突破,而大眾的、市場的、欲望的一切都被鼓吹,這正好是好萊塢大眾電影和各種商業電影所喜歡的。
恰好,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年12月18日國家廣電總局和文化部聯合頒發了《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試行)》,在電影界,這種劃時代的意義在于,中國本土電影將“走向世界”,電影將交給市場,讓民間資本來為電影提供動力,同時,在藝術形式上,它為中國電影開辟了與好萊塢聯姻和平等競爭的道路。一方面,政府對電影市場開始松綁并提供廣闊的發展動力,使中國電影不僅面向國內,而且也開始面向世界;另一方面,外國電影也進入中國市場,面對巨大的外來競爭壓力,中國電影被迫轉型,向著市場化和國際化方向改道前行。以張藝謀的《英雄》為起點,陳凱歌、馮小剛、姜文、吳宇森等導演合力開啟了“中國式大片”的商業大道,在表演、拍攝、投資、發行等領域的國際化合作日益普遍,資本和市場成為左右電影創作的主要因素。
此種形勢之下,難以融合于市場化和國際化潮流的鄉土題材逐漸淡出主流電影的行列,逐漸成為游離于商業大片核心以外的邊緣角色。整體來看,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不管是在數量上還是藝術成就上都處于整體下滑的趨勢。
從題材來看,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大致可劃分以下類型:
(一)反映新農村的發展建設
一類是展示新農村發展新貌。這一類型的電影往往把視角放在國家政策給農村帶來的積極變化上,如《十八個手印》(高峰執導,2008)、《砸掉你的牙》(孟奇執導,2008)展現了國家的農業政策在農村落實后美好圖景;《另類村姑》(陸江執導,2010)、《了不起的村莊》(盛林,陳健執導,2003)、《辣嫂》(方軍亮執導,2010)、《公雞打鳴,母雞下蛋》(白玉、高希希執導,2000)、《永遠是春天》(曾劍鋒執導,2007)講述了農村的先進人物帶領村民奔向富裕的故事;《沉默的遠山》(鄭克洪執導,2005)《香巴拉信使》(俞鐘執導,2007)、《索道醫生》(雷獻禾、王菁執導,2012)、《馬背上的法庭》(劉杰執導,2006)講述了鄉鎮基層干部默默奉獻,不辭辛勞的感人故事。
(二)反映農村凸顯的現實社會問題
首先是政治問題。《好大一對羊》批判了貧困山區的“官本位”和“形象工程”,揭示了官僚作風不但沒能讓貧困農民脫貧反而對農民造成精神傷害的現實。《曲別針》(張元龍執導,2009)反映了農村基層村干部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李睿珺執導,2012)揭示了政府土葬政策與農民傳統和愿望之間的矛盾。其次是貧富差距和教育問題。《Hello!樹先生》(韓杰執導,2011)表達了貧苦農民在貧富懸殊的農村的尊嚴和發展之困。《美麗的大腳》(楊亞洲執導,2002)、《上學路上》(方剛亮執導,2004)、《走路上學》(彭家煌、彭臣執導2008)、《云上學堂》(孫沙執導,2008)反映了鄉村教育的困苦和辛酸。再次是性和婚姻問題。《盲山》(李楊執導,2007)反映了中國偏僻農村拐賣婦女的可怕現實。《光棍兒》(郝杰執導,2011)反映了農村光棍兒群體的性苦悶。《最愛》(顧長衛執導,2011)、《兩個人的教室》(董玲執導,2007)講述了艾滋病感染者在農村的邊緣化遭遇。
(三)反思鄉土社會的苦難
《白鹿原》(王全安執導,2012)以白鹿村五十年的歷史演進為縮影,講述了20世紀前五十年北方農村的苦難史和斗爭史。《斗牛》(管虎執導,2009)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戰區老百姓的另類苦難經歷。《天上的戀人》(蔣欽民執導,2006)、《櫻桃》(張加貝執導,2007)講述了鄉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殘疾人的苦難和愛情。《暖》(霍建起執導,2003)、《驚蟄》(王全安執導,2004)《圖雅的婚事》(王全安執導,2007)《芳香之旅》(章家瑞執導,2006)、《北方一片蒼茫》(蔡成杰執導,2018)展現了農村婦女在貧困的經濟環境和不幸的婚姻生活中的苦難和女性不屈不撓的精神。
(四)道德倫理、家庭倫理、日常生活
《證書》(夏詠執導,2005)講述了村民見義勇為在道德模范評選中被有關部門無理取消,為了找回尊嚴不斷上訪的故事。《春娥》(強小陸執導,2004)講述了一個喪夫寡婦與本村正直青年戀愛結婚及其婚后徘徊于兩個家庭之間的矛盾故事。《俊俏媳婦開明婆》(薛彥東執導,2000)講述一對婆媳從爭執到和睦,從自私到為對方相互關懷的生活故事。
(五)展示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
《婼瑪的十七歲》(章家瑞執導,2003)、《花腰新娘》(章家瑞執導,2005)、《等郎妹》(鄭華執導,2007)、《天上草原》(塞夫、麥麗絲執導,2002)展現了少數民族獨特的風俗和秀美的田園風光。
(六)關注農民進城問題
《泥鰍也是魚》講述了離婚婦女帶著孩子從農村到北京打工,遭遇一系列挫折,最后不得已離開的故事。《高興》(阿甘執導,2009)《葉落歸根》(張揚執導,2007)講述了農民工跟伙伴進城打工,最后帶領因工傷死亡的工友的尸體返回農村的故事。《山里的女人》(梁征執導,2005)講述了農村姑娘在城市受到傷害又回到農村的故事。《農民工》(陳軍執導,2008)、《天堂凹》(安戰軍執導,2009)講述了農民工在城市打拼走向成功的創業故事。
綜合起來看,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更加關注個體。跟改革開放初期的鄉土電影相比,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大多把視角放在農村個體,反映農民個人的命運和心靈世界,更加關注鄉土社會的內里和人的精神。《證書》反映了農民對于個人榮譽和個體價值的追求。《暖》《驚蟄》《圖雅的婚事》《美麗的大腳》《上學路上》《北方一片蒼茫》是對女性命運的觀照。《天上的戀人》《櫻桃》則關注到了農村弱勢群體——殘疾人。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的鄉土電影塑造的是一個個類型化的農民群像,那么,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則樹立了一個個個性鮮明又命運迥異的農民形象。第二,式微與實化。新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進程,鄉土題材似乎很難制造出“視覺奇觀”來走商業大道,知名導演幾乎整體缺席鄉土電影的創作,創作主體轉向以青年導演為核心。在市場方面,受眾的流失導致鄉土電影走向院線阻礙重重,即便上院線也是很難走俏。在藝術水準上,制作精良又藝術上乘的作品并不多見。在數量上,也是呈現出了下滑的趨勢。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失去了90年代的那種浪漫氣息和對鄉土社會人性人情的贊美和謳歌,而是更加貼近現實,更多將鏡頭指向了現實生活,尤其是鄉土生活的陰暗面和疼痛處,以緊貼地面的手法展示鄉村社會在走向沒落的大時代背景下的無奈和悲涼。《好大一對羊》《光棍兒》《盲山》《最愛》幾乎將血淋淋的現實展示在了人們面前。《斗牛》《高興》《葉落歸根》雖不那么殘忍,但也足夠沉重和骨感。第三,實驗精神和探索意識。新生代年輕導演的加入,推動了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向著更深處探索,在觀念、技術、題材、視角等方面涌現出新的氣象,《Hello!樹先生》中魔幻主義的融入,《光棍兒》《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心迷宮》等大量起用群眾演員和方言對白的嘗試,都是具有開拓意義的探索和嘗試。
四、城市化、新農村、邊緣化、碎片化:新時代的鄉土電影(2012至今)
在市場經濟主導下,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一方面使國內經濟得到振興,另一方面也得到歐美主導的國際社會的認可,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異常迅猛。在新世紀以來的十年間,中國人買房子,買車,出外旅游,過去未曾想過的夢想都實現了。然而,物極必反,全球化帶給中國人福祉的同時,也在解構著原有的社會理想,公平、正義、共同富裕逐漸在被拋棄,官場腐敗,資本開始主宰社會,兩極分化現象突現。這就是2012年新時代之后開始全面治理社會的原因所在。
同時,新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城市化的進程變得異常迅猛,農業的收入越來越微薄,而城市里正好需要大量民工去做粗活,于是,大量農民開始涌入城市,并徘徊在城市的邊緣,使得農民工問題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最大的話題。每年春運開始時,農民工的工資和返鄉成為新聞的焦點。“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①2011之后,城鎮人口超過農村人口,徹底改變了幾千年來鄉土中國的人口格局,鄉土中國變為城鄉中國,開始向城鄉中國轉型。
文學中有大量描寫農民工的中短篇小說,也有不少長篇小說,“底層敘事”成為這一時期文學中的重要現象。但是,在以色相為主的電影中,因這一時期以娛樂化、市場化、國際化為導向,而且計劃經濟時代的鄉村放映員的消失、電視的興起和城市里小型影院的建設,使得電影成為城市的專利,鄉村也開始依附于城市的鏡像而存在,這就使得鄉村題材的電影越來越少,鄉土題材電影開始走向低谷。
從題材來看,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主要有這樣幾類:
1.謳歌農村的發展新貌。《卒跡》(魯堅執導,2014)、《開工大“急”》(高力強執導,2015)、《華僑村官》(陳健執導,2014)、《十八洞村》(苗月執導,2017)講述了農村扶貧脫貧和發財致富的故事。2.反映鄉村的問題和困境。《老家新家》(方剛亮執導,2011)、《親愛的》(陳可辛執導,2014)、《深情約定》(大飛執導,2014)、《桔子的天空》(徐鴻鈞、高欣生執導,2015)、《哺乳期的女人》(楊亞洲執導,2015)分別反映了移民、拐賣兒童、鄉村教育、農村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等問題。3.農民工進城的遭遇。《同路人》(高林執導,2012)講述了農民工進城創業走向成功的故事。《路過未來》(李睿珺執導,2018)講述了農民工子女在城市的生存奮斗故事。4.反思鄉土文化的沒落。《百鳥朝鳳》(吳天明執導,2016)揭示了傳統技藝在商業化和城鎮化大潮中失去尊嚴和后繼乏人的可悲現實。《一個勺子》(陳建斌執導,2015)反映了弱勢的鄉土在強大的城市的暴力和陰謀面前無力抵抗而蒙受災難和冤屈的悲劇現實。5.生態和環保。《狼圖騰》(讓·雅克·阿諾執導,2015)反映了草原牧民與狼和諧共處的主題。《消失的村莊》(林黎勝執導,2011)講述了為保護野生動物村莊搬離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移民”故事。6.鄉村奇談怪事。《心迷宮》(忻鈺坤執導,2015)講述了由一個無名尸體引發的鄉村各色人物糾纏在一起的另類故事。
綜合起來看,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有這樣一些特點:
(一)破碎化與邊緣化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鄉土社會不再封閉自足,變成了被城市沖擊和擠壓的弱勢一方。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顯示出了城鄉穿插和結合的特征,所展示的鄉土是破碎的和邊緣化的。在城市化進程中,傳統的鄉土社會土崩瓦解,現存的鄉村變得凋敝、空心化,在城市文明的威脅和侵擾之下,倫理破碎,道德崩塌,走向沒落。《一個勺子》里鄉村的仁愛和溫暖深陷于城市的陰險套路,《百鳥朝鳳》里嗩吶習俗所代表的鄉村倫理秩序不得不遭遇資本的玷污。這一時期,邊緣群體成為鄉土電影關注的主要對象,電影的主人公一類是農民工,另一類是留守人員。比如《哺乳期的女人》里的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百鳥朝鳳》里的老嗩吶藝人和進城打工的眾師兄弟。
(二)懷舊情結與哀婉基調
面對鄉土社會的衰敗、破碎與瓦解,鄉土電影懷有一種懷舊的傷感氣息。《百鳥朝鳳》傳達出了傳統文化在破碎化邊緣化的鄉村找不到出路和保不住尊嚴的沒落氣息。《哺乳期的女人》表達了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生活的凄苦和精神的落寞。《一個勺子》表達了淳樸善良的農村善待傻子換來的卻是來自城市陰險的敲詐勒索。我們發現,這一時期鄉土電影的主基調不再是歡欣鼓舞,也不再是浪漫詩意,而是在整體上帶有一種懷舊和鄉愁的情調,帶有一種挽歌式的哀婉色彩。
(三)大眾化與民間化
這一時期的鄉土電影雖然塑造得最多的是日益邊緣化的農民形象,但是,大眾化和民間化特征也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于影片不再是從精英的立場或者從外來的視角來反觀鄉土社會的傳統和現實,而是開始真正體察農村邊緣人群的生活感受,平凡個體的日常經驗和困境成為電影的關注重點,愛情、啟蒙、文化、習俗、風土人情等諸多宏大元素被消解,鄉土的詩意和浪漫逐漸消退。與此同時,新生代青年導演的加入,鄉土電影開始從懸疑、推理等類型電影汲取經驗,從敘事手法上給鄉土電影增加了可看性和趣味性,《心迷宮》就是采用多線條敘事手法講述了一個懸疑的故事。
結語
電影是時代的鏡像,時代生活是電影創作的源泉。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中國翻天覆地的四十年,使中國從“站起來”變得“富起來”,有人說走過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雖然離“強起來”還有不小的距離,但這種快速發展的“中國模式”是世界的奇跡。宏觀上說,這是不容懷疑的,但是,在這種大江大河的洪流中,就微小的個人來講,這種飛速發展必將帶來生命的巨大陣痛與變化,有喜悅也會有痛苦,有巨大的收獲也會有無言的失去,“一陰一陽謂之道”,事物的發展總是復雜的、多層面的。從新時期以來,文學與電影一直在反映大時代變化中的個體之變,從小人物入手既以點帶面地記錄和反映著大時代的精神面向,又細致入微地表現他們作為個體的喜怒哀樂,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精神與中國故事。中國是一個鄉土文明為傳統的國家,鄉土的變遷標志著國家的變遷,在城市化的進程中,鄉土變得越來越脆弱,鄉土文明越來越式微,這是不是好的圖景呢?是不是我們真正追求的愿景呢?這同樣也成為近年來思想界和文學影視界所討論的大問題。在大力復興中華文明的今天,鄉土題材電影擔負著重要使命。這可能是未來鄉土題材電影的轉向。
【注釋】
①《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政府網,2012年08月14日http://www.gov.cn/jrzg/2012-08/14/content_2204179.htm.
(徐兆壽,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劉強祖,寧夏理工學院藝術學院。本文系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百年中國影視的文學改編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8ZDA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