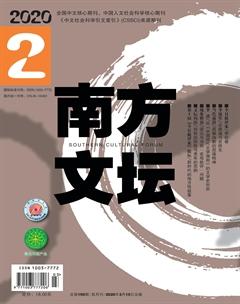經典改編與IP策略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新時期文學在三十多年后終于迎來了影視經典化改編的一個重要節點。文學自身的經典化漸進過程恰逢影視新一輪大發展的兩大背景:一是長篇電視劇文化日臻成熟、漸成主流敘事;二是由“IP熱”形成的IP改編與IP運營的文化產業背景。所謂“IP”,是2010年后興起于網絡小說影視改編中的一個流行概念:“指那些具有高關注度、大影響力并且可以被再生產、再創造的創意性知識產權。”①由于網絡文學作為影視改編資源價值的被發現和重視,一大批影視機構爭相從數量巨大的網絡小說中尋找、評估、購買、貯存那些具有眾多粉絲讀者流量的大影響力的作品,并采取大流量明星、充分類型化和戲劇化等積極的改編策略,形成了所謂網絡文學IP改編熱。
IP觀念也深度影響了新時期文學經典改編。IP改編和經典改編具有某種同質性,因為后者的經典性和巨大影響力其實與IP改編的要求是一致的,不過是沒像網絡IP那樣擁有明確的粉絲流量數據罷了。也正是在2010年后,新時期文學的一批經典作品如《白鹿原》《紅高粱》《平凡的世界》等長篇名著,均實現了長篇電視劇的改編,應該說這和IP改編熱是有因果關系的。本文將考察《紅高粱》在IP熱的背景下進行電視劇改編的狀況,尤其聚焦在對小說母本所體現的作為新時期文學精神標志之一的“紅高粱精神”的改編。
一、“紅高粱精神”的經典改編
對新時期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應聚焦于小說母本的經典意義,將新時期文學的精神實質影像化地呈現出來。對于莫言小說《紅高粱》而言,就是要將作品的核心內容即“紅高粱精神”最大化地改編呈現出來。小說《紅高粱》(1986)和電影《紅高粱》(1988),雙雙成為“經典”之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都深刻地把握并藝術地表現了“紅高粱精神”。
關于“紅高粱精神”,最早來自小說作者莫言和電影導演張藝謀的表述。莫言說:“我始終認為高粱是我小說里的不屈的精魂,我也希望張藝謀的片子里的高粱成為具有靈性的巨大的象征,使我爺爺我奶奶們的命運和高粱們緊密交織在一起,他基本做到了。”②張藝謀說“《紅高粱》實際上是我創造的一個理想的精神世界”,“影片所展示的,只是生命的一種自由舒展的精神狀態”,“生命的自由狂放,這本身就是生命的美”,“跟日本兵的抗爭,體現了生命本身不屈的精神”③。可以將這些話看成是對電影《紅高粱》改編小說母本提煉的“紅高粱精神”的一種綜合、概括。
“紅高粱精神”還是對民族民間原初和野性的“生命力”和“生命意識”的詮釋,體現為以紅高粱為基本意象的象征體系,由四個意象性的情節、情感板塊構成。
1.婚禮娶親路上的顛轎。小說是在高粱地中野徑路上,濃彩重墨地幾乎用了整整一節兩千多字來描述;電影將場景搬演到大西北的黃土地上,而且放在片頭足足用了一個小時二十七分鐘全片時間中的十一分鐘。
2.高粱地野合。這是高粱意象與天地背景融合為一疊印出的男歡女愛的天地儀禮,小說中,以最為激情酣暢的文字將此作為九兒臨終為抗日捐軀時候的生命回憶,而與血灑戰地的崇高生命體驗疊印在一起,乃是隱喻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啟動生命欲望的最直率表達;而電影里,也不吝于影像時間足足用了六分鐘,特寫鏡頭與天空俯瞰鏡頭交叉,贊美生命的嗩吶奏樂之后萬籟俱寂映襯九兒的永恒生命之美。
3.酒作坊祭酒儀式。酒歌雄壯,高粱傳奇,男性雄遒之強音。
4.高粱地打鬼子,槍炮齊鳴,血灑田野,民族民間抗戰的悲壯犧牲儀式與國民“紅高粱精神”的成人禮。對此小說在開頭和結尾兩處均有整整一節的渲染,也是意象的沸點。電影則于此民族危亡犧牲時刻以影像儀式肯定了英雄,復活了中華酒神精神,一舉而在沈從文式、蕭紅式的原始生命野力的某些陰柔體質之外,開辟出民族民間的陽剛崇高美學。
作為“經典改編”,電影《紅高粱》舍棄了小說中其他情節,而只將上述四個“紅高粱精神”經典意象段落重點予以影像化表現,無疑接續了從《黃土地》開始的詩化影像敘事的探索電影方向,可以說是莫言詩化意象化小說的影像再詩化再意象化,是一種提純式的經典化改編。張暖忻曾評價道:這些段落在“對情懷、心緒、氣勢和力量的表現上,達到了與原小說異曲同工的境地”④。
二、電視劇的“紅高粱精神”
再現與IP劇改編策略
正是在《紅高粱》小說和電影的經典化基礎上,2014年播出的長篇電視劇《紅高粱》,其改編即應該是“經典改編”而非一般“IP改編”。一是理應對準小說和電影的經典內核對“紅高粱精神”加以改編;二是在長劇黏性強韌的電視劇主流文化潮流下,實現純文學經典的影視化,將意象化和詩化的小說內容體量改編為長篇電視劇;三是在“IP熱”的背景下,保證《紅高粱》內容價值與產業價值均得到實現,處理好經典改編與IP策略的關系。
首先,改編者當然意識到這是一個經典改編。改編者將《紅高粱》小說及其改編電影中有關“紅高粱精神”的經典意義,以及其意象體系的四大意象橋段都橫移到了電視劇中,以保持在經典內核上的一致。電視劇將《紅高粱》的地域背景從電影版中的西北黃土地挪回至山東半島,顛轎技術層次更為精準,電視劇主題曲《九兒》的高邁深情,所有這些有關《紅高粱》基本意象橋段的植入再現,看似復現了“紅高粱精神”。
而問題在于,這樣只是孤立地看問題,如果把這些段落復現到整部電視長劇敘事中,便會造成某種經典IP橫移過來后的敘事斷線。
中篇小說原作的第一節,莫言即從殘酷而崇高的戰地美學入手,在鮮血淋漓的高粱地輝煌與苦難的戰場回敘吾爺吾奶的風流事跡。到中間第五節更用一整節來寫狂野生命的娶親顛轎。電影改編版則是影片一開始就是娶親路上長達十一分鐘的顛轎過程,完全是抒情性表現性的。而電視劇版《紅高粱》,寫顛轎則自第五集開始,原來因考慮到六十集長劇的容量的“設定”,需要設計更加宏大繁復的故事情節,需要引入更多的人物場景及其關系等,所以顛轎的重頭戲延宕至第五集才出場,已不算慢。然而,敘事斷線的破綻也就出在這第五集。第五集由于追慕小說或電影版的濃烈張揚之風,也用了十分鐘左右,也就是單集五分之一的篇幅來詳細展現顛轎的過程,但我們發現,由于電視劇從一開始選擇的緊湊敘事節奏,每一集的“情節點”都起碼在十二個以上,而第五集的“情節點”設定只有6個,這是因為這一集有細致煽情的民俗展示內容“顛轎”加入。這樣,前后的敘事節奏在此處不免頓生斷裂感。而斷線再續則徒生接受障礙,況且由于敘事全局的邏輯所致,顛轎等橋段的生命表現性不免流失一些,而民俗性的展示味道卻似乎多了一些,整體感受下來,原來的經典意義的格局就塌落下來。
其次,這的確是電視劇作為主流文化的時代,而且長劇的黏性越來越強,經典改編也不免被吸附過去。電影《紅高粱》標明改編自莫言的小說《紅高粱》《高粱酒》,而這正是莫言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的第一、二兩章。電視劇版《紅高粱》直接標明由《紅高粱家族》改編,意在說明電視劇敘事將擴充內容至整個長篇小說。我們知道,《紅高粱家族》共五章,是由五部獨立的中篇小說組合而成,各章從不同側面書寫“紅高粱家族”,而在寫作風格上各章都是一致的,即以寫意表現為主的方法,高揚主觀性敘述的調子,重點并不在于“講故事”,因此小說文本在“故事”“情節”方面是處于一種風格化統攝下的碎片化狀態。況且該書中的《狗道》《奇死》兩章內容并不太容易改編進去,可改編的除了原來的《紅高粱》《高粱酒》再增添的也就只有《高粱殯》一章內容了。對這些情況,電視劇編劇趙冬苓是有基本認知的,她說:“電影藝術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細地編排故事,主要用意象表現精神,但對電視劇來說遠遠不夠,我們要把人物放在一個很煙火氣的環境。”“電視劇要把精神性的東西改成一個富有煙火氣的故事。”⑤所以諸般考量后,她便按照“鴻篇巨制”的目標,在小說給定的內容之外增添人物和情節,圍繞九兒來設計復雜豐富的社會關系,最后人物總共達到五十八個。結果是以寫意和意象為主的敘事風格“改編”成為以戲劇性故事為主的抗日故事劇風格。其間對他們不能改也改不了的經典“硬核”的橋段,只好投放到六十集大劇的故事長河中,任其沉浮。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一種“擴展式”改編,不是“豐富些內容”那么簡單,它不是在我們欲表現的“紅高粱精神”經典意義基礎上的“擴展”,它是在原有的經典內核之外又圍裹上、包裹上厚厚的一層抗日故事劇,原本的“紅高粱精神”,在六十集的長度中被消解和淹沒。這是一種包圍式的改編、包裹式的改編。
再次,需要專門考察一下“IP改編熱”背景對電視劇《紅高粱》的影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莫言小說《紅高粱》無疑是個大IP,尤其需要六十集或比六十集更多的集數長度來播出。雖然大IP級的文學作品可以是短篇小說或中篇小說,但此時此刻的電視劇必須是長篇敘事的。因為這是IP運營IP改編的必然要求。所謂IP就是建立在保全必贏的前提下的效果“設定”。莫言、諾獎、《紅高粱》經典,“流量”上無疑是大IP,卻仍須流量+明星才是必勝模式,全明星陣容才撐得起“經典”。根據《紅高粱家族》提供的內容量,二十集上下可能更合理,而啟用周迅、黃軒、秦海璐等片酬不菲的一眾明星則增加了制作成本,而影視發行是以集數為單位計算的,沒有六十集左右的集數保證不了投資回本及贏利,所以六十集左右應該是如《紅高粱》這樣的大IP劇的一個集數的規模下限了。
必須說電視劇版《紅高粱》比較好地實現了IP價值,但它只是在所謂內容生產的比較泛泛的意義上是如此。如果我們不僅僅照顧到所謂內容生產的泛泛之得,還惦記著“內容生產”這個IP核心術語的某些高級的層面,比如經典性,比如文學史意義或影視史價值,比如對“紅高粱精神”的生命哲學闡釋,對民間英雄與俠義風流的反思,等等,就會感覺到對該劇的抱憾。
對于那些對小說和電影《紅高粱》的美學奇觀與生命思想的意象寫意橋段念茲在茲的人來說,“在這些橋段的用力上,電視劇版稍顯遜色。余占鰲顛轎還算著墨較多的地方,但是鏡頭的重點是程序和搭建人物關系,而不是美學表達,導演借此在搭建人物關系上比較奏效,卻丟掉了對原著原始生命精神的把握。他在不斷放棄原著的美學特色,代之以故事化的、敘事性的章節,在這一點來說,是導演的最大敗筆”⑥。這樣的有關“敗筆”的批評言辭有些過激,卻著實情有可原。我們須承認電視劇改編者對于作為中國新時期文學經典作品的重視與理解,他們對經典精神的把握也是準確的,趙冬苓就說:“電視劇和莫言在精神內核上保持一致,那就是人性的張揚、強悍的生命力和狂野的精神。”⑦改編者在電視劇中也是照此去做的,幾乎忠實地復制了小說與電影中顛轎、野合、祭酒神、戰場英雄灑血犧牲等橋段的寫意表現,至于其中細處的差異與誤解是難免的,這可以給予理解。只是這部分意象的精神的“內核”置于漫長的民間抗日武裝的合縱聯橫的劇情中間,仿佛“兩層皮”,各說各話。
三、從男性視角到女主戲
電視劇版《紅高粱》改編的重要方面,除了改編者增加了大部分的故事情節,還有就是將劇情由以余占鰲為主的男主戲模式,改成了以九兒為主的女主戲模式。這樣就意味著對原作做出很艱難的調整,意味著將“紅高粱精神”的男性雄遒內涵轉換為女性剛強性質,難度系數不可謂不大;雖然“大女主”是一種當下流行的IP改編策略與方法,但對具體作品《紅高粱》而言,若想改變“紅高粱精神”的男性精神主色調,也是很難做到的,反而造成女性主角與全劇內在精神氣質的不協調。對此,總編劇趙冬苓承認她受到了熱播的“大女主”戲《甄環傳》的影響,她還認真地研究過美劇《傲骨賢妻》。由于IP改編主要是方法層面的,而不是內在精神的,所以她一直強調對原著精神的堅守不變,顯得不無矛盾。
小說《紅高粱》的敘述人以我的口吻來講述吾爺吾奶的事跡,無疑是男性視角的。隔代的我,自我認知有“種的退化”,也就是說已丟失了祖輩的生命力、原始野性和血性欲望。《狗道》中寫父親被狗咬成生殖器殘缺,象征父輩已經開始生命力退化。因此《紅高粱》主旨即在講述我爺爺奶奶輩的英雄氣概,即紅高粱所象征的鮮紅與挺立的生命精神。小說用很大篇幅除了寫爺爺余司令的野性、匪性,大義滅親槍斃叔叔,還寫了羅漢大爺面對日寇的視死如歸,最后寫爺爺率眾民間武裝而在抗日戰場上血拼,全篇小說更多的是男性文本雄性話語。
電影《紅高粱》延續了小說的男性話語,但與小說比舍棄了羅漢大爺抗日血性行為的直接描寫,以及余占鰲帶領民間武裝內部管束中的俠義硬漢形狀,而只取他與奶奶戴九蓮的生命之戀,最后雙雙走上了民間抗日的戰場,奶奶及全部村民勇士壯烈犧牲。奶奶經營酒作坊的成功,以及對余占鰲具有男人成人禮式的考驗,幫助余占鰲抗擊日本侵略者等,拉升女主“我奶奶”的地位,但是電影的敘述話語總體來說還是男性話語方式和色彩的。如三個重要意象性橋段“顛轎”“高粱地野合”“祭酒儀式”所唱的三首民風歌曲《顛轎曲》、《妹妹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酒神曲》,均由余占鰲(姜文)嘴巴唱出或領唱,充滿男人的粗獷、野蠻、豪橫的狂歡性,流傳廣泛。在小說原著中,“我爺爺”余占鰲的身份本來是一個土匪,如果按照這一身份設定,“觀眾對土匪的概念化認識會妨礙與這個人物的情感和心靈的溝通,從而沖淡我們通過這個人物要表達的贊頌生命的主題”⑧。因此電影選擇了將余占鰲的身份轉換為抬轎的轎夫,把與其相關的地方武裝背景等全部隱去,這樣,“我爺爺”在影片中的一系列狂野不羈的行動,如吼歌、野合、醉酒、癲狂、當眾對著酒缸撒尿等,都只剩有民間性質而減弱了土匪民間性質,更容易成為一種人性隱喻,即“那種構成人的本質的熱烈狂放的生命態度”,都呈現強烈的男性特征。“我爺爺”和“我奶奶”在人物關系中,占據主動的是“我爺爺”。按照張藝謀的說法,在影片的人物關系中,“我爺爺”是屬于“進攻型的”,這個人物形象在演員姜文的演繹下,活靈活現地詮釋了陽剛、奔放、自由的生命精神。由是,這部電影又可以說是一部男主戲了。
電視劇編劇趙冬苓談道:“余占鰲是土匪,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時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斷社會關系,而九兒卻一直生活在民間。電視劇要鋪排各種社會關系,無疑,九兒這種有豐富社會關系的人物更適合我們這樣的鴻篇巨制。”⑨這是電視劇設九兒為“大女主”的一個真實理由。同時也應看到時下“IP熱”中有關“大女主”的IP改編策略所提供的資源,也促使擁有經驗的改編者執意于此。一是以“大女主”九兒的人物成長為主要故事脈絡。二是以“大女主”為中心定義她與所有各方的關系,形成中心向外張開的復雜關系網。三是原小說中沒有,改編時為九兒新設了一些關系人物,如初戀情人張俊杰,單家大少奶奶淑賢等。四是九兒與余占鰲關系的調整,變得復雜。如九兒和余占鰲,本來是男歡女愛驚天動地的情愛纏綿悱惻,現在則定位成“男人和女人的戰爭”關系,雙方互相征服、又愛又恨,“幾乎每次見面都是一次戰斗”⑩。為“大女主”讓九兒顛覆了與余占鰲從前的主被動關系。總之,上述以九兒為中心的復雜關系設定,只能在IP策略等操作層面發揮作用,而無助于精神境界的開拓,誠如編劇的自我剖白:這種人物設置,“一方面使得故事節奏更為緊湊,另一方面也迎合了現代觀眾對三角戀、鉤心斗角、戰爭等戲劇元素的審美需求”11。
劇版的改編豐富了九兒的形象,給九兒設定了更加復雜的社會關系,加上足夠長的時間,九兒身置于極度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一方面九兒性格是豐富了、立體了,另一方面九兒性格又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局部紊亂,因此引發了一些爭議和討論。九兒要面對兩個青年人的愛戀,更多一點學生腔的張俊杰和更多一點霸氣與情欲的余占鰲;要面對兩個土匪頭子的爭奪;有情義與霸道的余占鰲和搶劫做壓寨夫人的花脖子;要面對兩個父親型人物,縣長干爹朱豪三和親爹戴老三;要面對兩個身邊親人,大少奶奶淑賢和親哥戴大牙,等等。這些改編后建立起來的關系框架之復雜,完全可以建構一個復雜、立體的扁形人物和圓形人物兼具的畫廊。而僅就九兒的圓形人物建構而言,復雜性格處境和表現是齊備的,但性格系統中因素太多,還沒有做到協調有致。例如:剛剛與俊杰模仿西式教堂婚禮程式,天真爛漫像極新文藝青年,卻即刻又出入匪窩被搶壓寨及進入單家大院,老練果斷如久經滄桑;剛剛與綠林好漢暗通款曲馬上又聲明絕不嫁土匪,所有這些,九兒總是予取予奪,不需過程,轉得太快,直奔結果。新時期文學的精神氣質,在這種快的節奏中,靈魂似無處安放。
四、空間轉換:從高粱地到宅斗戲
在《紅高粱》小說中,作為整個作品核心空間背景的是“高密東北鄉”的“紅高粱地”,在電影《紅高粱》中雖然導演已將其置換到中國大西北黃土地上,但其作為核心背景的象征隱喻地位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在電影的意象性烘托的空間中得到了強化。以電影的“野合”空間為例,那片被“我爺爺”踏平的圓形空間,它像一個祭壇,上面擺放著“我奶奶”,而“我爺爺”則雙膝跪地,隱喻了對不可遏抑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沖動的崇拜;此后則是一系列疊化處理的中景、近景和全景視角的在風中快速搖曳的高粱鏡頭,它們似乎是以自己狂熱的舞姿,向象征著“天地之大德”的生命交媾與創化行為致敬。這樣的鏡頭語言和空間呈現方式,既凸顯了傳奇性,又超越了單純的傳奇性,人性原初偉力與自由精神于其中升華出來,正如王一川所言,它“讓觀眾不僅像在《黃土地》中那樣旁觀地‘凝視和反思,而是在對奇觀鏡頭的凝視中情不自禁、設身處地地體驗或沉醉,并在體驗或沉醉中觸發對于人的生命的更深沉的反思”12。電影版的這一“經典性”的空間成為影片的核心景觀,盡管也有其他場景,但是這一經典性景觀卻奇崛傲立在劇情中、刻印在觀眾的腦海中,也必定為電視劇的改編所采用。
但除此之外,電視劇《紅高粱》所凸顯的是故事性的IP策略目標,又與這種既定的抒情性寫意性目標,產生疏離,并不一致,就會為了鋪陳人物劇情而淡化、忘卻、丟失原有的經典性空間意義。電視劇改編確立了以九兒的傳奇一生為線索來講述其與余占鰲、張俊杰的愛情糾葛,以及與朱豪三等人的抗日故事,敘事策略以推動劇情、塑造鮮活人物形象為要義。其中,設置與人物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的場景,突出生活氣息和現場感,便成為電視劇的著力點之一。而這些以九兒為中心的復雜人物關系結構,若想講清楚,必然涉及更加豐富和多樣的空間場景,配以足夠的時間,才能還原生活的煙火氣和場景的真實性。劇中值得稱道的是單家酒窖、單家大院、三十里坡等場景,設計十分逼真,如單家大院取景地為“十幾座古色古香的青磚民宅,有前宅后宅,偏房廂屋,構建起一個小規模的建筑群。……由一磚一瓦實景打造,每間房屋都由青磚建成,青瓦為頂,做舊工作結束后,斑駁的墻面、木質的門框、窗框顯得古意盎然,韻味十足,讓人仿佛瞬間穿越,置身于民國時期的院落當中”13。一系列塑造女主角九兒性格特征和形象發展演變的重要情節,就在這一場景中上演。為此改編中格外增加了一個象征封建傳統倫理的人物形象,單家大少奶奶淑賢。她抱著牌位嫁入單家,為了虛無的“名節”而活著。九兒的境遇與其相似,剛嫁入單家三天丈夫便一命嗚呼。后來,九兒產下她和余占鰲的兒子后,淑賢為了爭奪繼承權、維護自己在單家搖搖欲墜的地位,便一心想將九兒的兒子據為己有,并且用盡各種手段暗算九兒。洞察真相后的九兒以退為進,奮起反擊……兩個守活寡的女人在單家大院鉤心斗角的故事,圍繞著爭奪子嗣和新舊倫理觀念的沖突兩個焦點展開。兩個女人被置于單家大院的東、西兩個小院,形成內部空間對峙,構成兩個女性性格的鮮明對比,一方面強化了九兒敢愛敢恨、有勇有謀的形象特征,另一方面也使得淑賢這一舊道德的象征人物形象留給觀眾深刻的印象。這一深宅大院的戲份,加上縣長朱豪三的府第,以及九兒男友張俊杰家的豪宅和余占鰲、花脖子等的土匪山寨,大部分戲份都被裝入到封閉空間之中,野地意象及其開放張揚的情緒形態不免受到擠壓。
由此,電視劇《紅高粱》這一空間和場景的轉換,表征著寫意性、抒情性和形而上意味的消散,以及“宅斗戲”與民間武裝派系合縱爭斗戲的上演。這對于致力于“經典改編”無疑是自相矛盾的,改編者對經典性意義空間與IP策略性鋪展的故事意義空間的態度,也是一方面強調要原汁原味地表現原著的精神性,另一面又強調煙火氣甚至直接表明“沒有商業元素的電視劇沒人看”,最后同樣不能走出對經典改編內核的“包裹式改編”的命運。從收視效果看,這樣的改編保證了IP策略的實現,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對文學經典原著的擴大影響也有價值;但從新時期文學精神的經典改編角度看,我們仍然需要致力于其精神性價值的改編,在這個意義上,電影版《紅高粱》的經典價值不可取代,去閱讀文學原著融入原創的文學境界更是走進經典的必由之路。而《紅高粱》的小說原著、電影版、電視劇版三者可能會構成一個全面的關系來對接實際的需求,并取決于我們以什么樣的方式感知經典及其經典改編。
【注釋】
①尹鴻、王旭東、陳洪偉:《IP轉換興起的原因、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當代電影》2015年第9期。
②莫言:《也叫“紅高粱家族”備忘錄》,見《中國電影藝術家研究叢書·論張藝謀》,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第193頁。
③羅雪瑩:《贊頌生命、崇尚創造——張藝謀談〈紅高粱〉創作體會》,見《中國電影藝術家研究叢書·論張藝謀》,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第158-181頁。
④張曖忻:《紅了高粱》,《電影藝術》1988年第2期。
⑤《〈紅高粱〉編劇趙冬苓:沒有商業元素的電視劇沒人看》,《瞭望東方周刊》2014年12月8日。
⑥黃舒婷:《劇版〈紅高粱〉收視率飄高、經典場景遜色于電影》,《都市時報》2014年11月18日。
⑦⑩11《編劇趙冬苓談電視劇〈紅高粱〉如何與經典“過招”》,《深圳特區報》2014年11月2日。
⑧張藝謀、羅雪瑩:《贊頌生命崇尚創造——〈紅高粱〉的創作體會》,見丁亞平主編《百年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第265頁。
⑨《〈紅高粱〉改編下刀狠,編劇趙冬苓:60萬字無水分》,網易娛樂,2014年11月30日。
12王一川:《革命式改革——改革開放時代的電影文化修辭》,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第202頁。
13《揭秘電視劇〈紅高粱〉的幾個重要拍攝場景》,http://gd.sina.com.cn/qy/travel/2014-11-19/151310149.html.
(張貝思,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