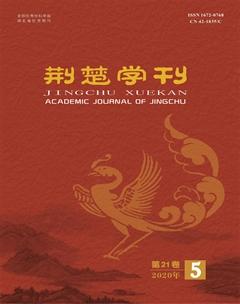晚清對赴華內地游歷外人的管理述論
付超
摘要:晚清時期,隨著中外條約關系的發展及列強在華條約特權的不斷擴大,愈來愈多的外國人進入中國內地開展游歷、傳教、經商等活動。為避免或減少由此引發的中外糾紛和交涉,清政府制定并頒行了一系列管理政策,對來華游歷者加以約束和限制。同時,依據相關約章和國際法對外交涉。這在一定程度上捍衛了國家主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但由于時代的拘囿,清政府仍難以沖破條約的藩籬,從而影響了游歷政策的執行和對外交涉的成效。
關鍵詞:條約體系;晚清政府;內地游歷;管理政策;外交交涉
中圖分類號:K254.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0768(2020)05-0031-07
鴉片戰爭后,中外條約關系開始確立,西方列強憑借不平等條約,逐步取得進入中國內地游歷的特權。隨之,形形色色的外國人大量進入中國內地,從事各種正當和非正當的活動。為了加強對外來游歷者的管理,避免或減少中外紛爭和外交交涉,維護國家主權和利權,清政府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游歷管理政策,并根據時勢的發展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這些政策作為晚清國內法和對外政策的一部分,體現了清政府主權意識的增強和對外理念的轉變。
一、構筑條約體系,赴華內地游歷
鴉片戰爭暨《南京條約》簽訂后,中外傳統的朝貢關系逐漸走向瓦解,一種以不平等為主導的新型中外關系模式——條約關系(也稱為“條約體系”或“條約制度”)逐步確立下來。在這種關系模式下,西方列強憑借條約特權和強權政治攫取了中國大量利權,外國人赴中國內地游歷即是在此背景下興起的。
(一)外人赴華內地游歷“條約化”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私自進入中國內地,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 [1]。1840年,英國發動侵華戰爭,戰敗的清政府被迫與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首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了列強脅迫中國“約開商埠”(亦稱“條約口岸”、“通商口岸”)的先河。根據條約規定,清政府向英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并規定“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時來往”,但“均不可妄到鄉間任意游行,更不可遠入內地貿易” [2]35。為了保證游歷者的人身安全,減少外交交涉,清政府還與英國、法國、挪威、瑞典等國簽訂《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規定該國人民可以在五口貿易、居住、游歷,但“商民、水手人等止準在近地行走,不準遠赴內地鄉村,任意閑游,尤不得赴市鎮私行貿易;應由五港口地方官,各就民情地勢,與領事官議定界址,不許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2]74就此劃定了外國人在華居留、貿易、活動的區域,后來的“租界”即濫觴于此。
由于列強在華的活動范圍被限定在五口之內,其商人難以獲取預期的貿易利潤,洋商們強烈要求拓展中國內地市場。同時,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也認為清政府對外人來華游歷的限制,“比任何事情都更其流于付給中國統治者以一種權力,讓他好對外國人繼續保持敵對的傲慢的態度,讓他用最最有害的苛征暴斂和留難的手段鉗制我們的商務”,為此,他強烈要求:“廢除一切可恥的內地旅行上的限制。”[3]在此情勢下,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悍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戰后,清政府被迫與英、法、俄、美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按照條約規定,“英國民人準聽持照前往內地各處游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2]97;法國人得往內地游歷,但“務必與本國欽差大臣或領事等官預領中、法合寫蓋印執照”[2]106;外籍東正教教士、耶穌教教士、天主教教士等,均得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此后,中國又與葡、丹、西、比、意等國簽署了一系列包含外國人赴華內地游歷條款的約章。從而,列強“依靠條約、法規使各種權利成為制度” [4]。在這種制度下,外國人得以深入中國內地從事游歷、通商、傳教等活動。
綜上可見,外國人深入中國內地游歷經了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從最初的五口游歷到可以游歷更多的條約口岸;從條約口岸游歷逐漸延伸至內地游歷;從被嚴格禁止到被動應允,并最終以條約的形式將其合法化。
(二)外國人赴華內地游歷活動概況
鴉片戰爭后,隨著條約口岸的增開及外人在華條約特權的擴大,各國商民旅居中國各口岸者其數日增。據統計,光緒二十二年(1895年),各國商民共計9 755人,人數居前三位者分別為:英國4 084人,美國1 325人,法國875人。另外,無條約諸國共149人[5]。1899年旅華總人數增至17 193人,其中,英、日、美三國人數最多,分別為5 562人、2 440人、2 335人[6]。及至1902年9月,各國旅華人數已達19 119人,排名前三者依次為:英國5 410人,日本4170人,美國2 292人。人數最少者韓國計18人[7]。一時間,“外人游歷內地,日有所聞。”[8]這些外來游歷者身份各異,其中以傳教士居多。他們到中國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多數人從事著與其職業、身份相吻合的工作,但也不乏滋擾生事、搜集情報、刺探軍情的不法分子。
中國東北地區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資源優勢,向來就是列強尤其是俄、日等國覬覦的要地。他們經常借游歷之名到要隘、要港秘密偵探、測繪,盜伐林木。自各國有游歷內地條約之日起,日本就“遣人數百輩,分布京外,交游縉紳,偵察政俗” [9]。1884年,總署奏稱:“各國洋人來東三省游歷各城,多方窺伺。本年夏間,在吉林地方,有日本人隱匿真名、薙發易服等事。現又有法教士二人欲往沈陽等處游歷。竊思東三省現在嚴辦邊防,該洋人等屢往邊界,難保不窺我虛實。”[10]1048這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警惕。1908年,由于“近來各國人員游歷,往往分赴各要地私行測繪,實屬存心叵測”,為此,外務部要求:“嗣后凡關于形勢險要處所,一概不準測繪,或有可以測繪之處,亦應令報由地方官轉稟該省大吏咨部核辦。”[11]否則,清政府將給予嚴厲打擊。同時,清政府還加強了對無照游歷、盜用他人游歷護照等行為的管理。1910年,葡萄牙人金士未按約領取護照,擅自越界闖入南屏鄉彈雀,槍傷農民曾允,鄉人上前救護,愈聚愈多,險些釀成群體事件。對此,中國地方當局指出:“洋人持槍過界打雀最易滋生事端”,葡人近常聚眾越境,“藉打雀為名闖進各鄉恣意滋擾,幸鄉紳等隨時彈壓、勸導,鄉人不致釀成事變” [12]484-485,嗣后“各國洋人前往中國內地,照約應領護照,且系只準游歷,并非準其游獵”,金士的行為已屬違約,且又槍傷曾允,為了以儆效尤,“無論是否有心,均屬罪有應得”,應“照律懲辦,以昭公允” [12]491-492。清政府還進一步重申:“游獵與游歷顯然判為兩事,條約內既未載有游獵字樣,自確有所據,不妨與之力辯” [13],并照會外國駐京大臣照章查核,勿再將游歷與游獵混為一談。當然,此事也有例外。1908年,美國博士維洛森擬游歷中國內地西方各省,尋獲各類鳥羽毛作動物標本,需用鳥槍及子彈四千粒。美使來照“請準其運入”,外務部調查后認為:“該博士系為研究學業起見,所帶槍彈自與商販暨尋常打獵所用者不同,應即通融,準其帶運” [14]315,凸顯了清政府處理此類事件的謹慎態度和靈活性。1911年,日人松田亮太郎持游歷護照,協同日人山本喜十郎到二岔子地方砍伐樹木,“伏查該日人所執系松田亮太郎游歷護照,照內并無山本喜十郎姓名,亦未注明準其入內地采辦樹木字樣。”[15]605顯然,這是盜用他人護照私自采伐中國林木的不法行為。清政府飭令暫停砍伐,聽候處理。另外,隨著外國勢力向中國內地的不斷滲透,“各國兵輪水手暨各洋人往往擅至內地游歷,輒與民人細故起釁互相爭執,或被毆傷,或釀命案,似此漫無法紀,實與華洋交涉關系匪淺。”[16]外務部認為此舉有悖于公法,有損于國家主權,特“照請駐京各國公使轉飭禁阻”,幾經交涉,各國公使應允:“嗣后各該國軍艦均不準隨意游歷中國內地” [17]。隨后,清政府命各省督撫查照遵辦。1908年,英國兩艘兵艦由湖口鼓輪晉省游歷,停泊河干,洋務局查詢“因違約章,勸令出口”,西人“語多反對”,據約力爭,“彼此口舌相爭”。洋務局遂照會上海英國總領事,要求其“照約章嚴行阻止,以后不得藉口有失邦交。”[18]并進一步加強了對內河行輪的限制。
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游歷過程中的種種不軌行為,也引起了國內一些有識之士的警覺和憂慮。維新思想家陳熾不無擔憂地指出:“西人之游歷內地者,自攜儀器,所至繪圖。山川道里、高深遠近,生長其地者尚或茫然,而彼族轉計里開方,瞭如指掌。隱憂深患,行道皆知。”[19]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權實屬不利,應加強防范和管理。駐外公使許景澄對部分外國官員私帶兵丁游歷的行為深表不安,他在致總署的信函中強調說:“俄員游歷,屢次帶挈兵丁,前歲游藏道死之員,聞帶兵十數名。雖其意只為自衛,無關他故,然準以泰西他國兵無故不得入境之例,究非事體所宜。”為此,他從國際法的角度指出:“竊維目前事勢,游歷之風已難禁阻,保護為主國之權,在我不能不任,方可杜其以兵自衛之漸” [20]。可見,許景澄已認識到外人游歷中國內地勢在必行,主張對其提供保護,以杜絕其帶兵自衛之風。按照近代國際法規定,“雖然外國人在進入一國的領土時立即從屬于該國的屬地最高權,但是,他們仍然受他們本國的保護。依據一個普遍承認的國際法的習慣規則,每一個國家對于在國外的本國公民享有保護的權利。與這權利相適應的,就是每一個國家對其領土內的外國人有依照某些法律規則和原則給予待遇的義務。”[21]據此,清政府有保護合法游歷者的義務。在此基礎上,東南路兵備道陶彬在遞東督錫良和吉林巡撫陳昭常的呈文中進一步指出:“外人每以游歷為名,輒就近向某衙門袛領護照,所到之地或測繪寫景,或博采詳察,肆其覬覦跡近偵探。甚或隨帶鳥槍任意獵狩,如入無人之境,莫之能御。鄉民輒環聚而觀,動起交涉。此等情形殊非嚴密國防,革屏釁端之道”,嗣后外人及各該省洋員游歷內地,“一切動作須立以規則,示以限制,并懇飭劃一發給護照,衙門以便稽查出入,調查行為,庶可稍收治外法權。”[15]603他主張實行游歷護照制度,藉以規范游歷者的行為,進而逐步收回領事裁判權。陶彬所言不無道理,外人游歷內地,“因有領事裁判權,不服從中國法律……雖任意踐踏,而媚外之風已成華人第二之天性。彼警察者,既不敢干涉,則鵠立以作壁上觀,警察權之難于實行。”[22]以致有不少持有游歷護照的外國人借游歷之名任意妄為,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地方穩定帶來重大隱患。要消除這種隱患,就必須加強對外來游歷者的管理,不斷健全國家法制建設,逐步廢除領事裁判權。鑒于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加大了對來華游歷者的管理力度。
二、頒發游歷護照,規范護照內容
為了規避和減少因游歷而產生的糾紛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歷者“必須請領護照為之限制”,“無照者不準前往也,發照之權,專屬之領事官,簽照之權,專屬之地方官。”[23]無護照之外國人不得到中國內地游歷。為此,洋務局還通飭各國:“凡有各國商民游歷內地者,須有上海各領事照會,再查確有商會印信、護照,方準任便游歷,妥為保護。”[24]且地方官府有權要求游歷者隨時呈驗護照,“無訛放行,雇船、雇人裝運行李、貨物,均不得攔阻”;如無執照,或內有訛誤及不法情事,“可就近交送領事官懲辦,沿途只可拘禁,不可凌虐” [2]525。然而,由于領事裁判權的存在,中國政府尚不具有對無照或不法游歷者懲罰的權力。但“中國人則自始堅持——雖不總是成功地——他們的最高的屬地法權權利”[25]。1880年,中德《續修條約》第六款中規定:“德國人等如有未領領事所發中國地方官蓋印執照赴中國內地游歷者,準該地方官將其人解交附近領事官管束外,仍應議罰,惟所罰之數不得過三百兩。”[2]374由此,中國政府首次以條約的形式取得了對無照洋人的經濟制裁權,這對那些無照擅闖中國內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根據護照申領制度,領事官不得為他國人民代發執照。1862年,暫波里國商人德勒耶領法國執照到營口租房設行。對此,盛京將軍致函法國臨時代辦哥士耆指出,法國領事官此舉“與條約不符”,“難以查核”,“實屬荒謬”,要求其將所發執照“即行掣回”,并“務遵和約,不得濫為別國商人代發執照” [26],以免引發外交交涉。后來,駐外公使也可以為赴華內地游歷者辦理護照。如1907年1月,瑞典國男爵馬達漢由俄國界入喀什噶爾,往和闐及庫車一帶游歷,由“中國駐俄大臣發給護照,遞至庫車轉交” [27]。馬達漢遂得以成行。
同時,清政府還不斷規范和完善游歷護照內容。最初的游歷護照由于內有“通商”字樣,導致各國商民赴內地游歷者易為朦混,以游歷為名奔赴內地設肆營業者甚多。為此,總署于1863年聲明:“凡洋商并不買賣貨物,專入內地游歷者,按照條約,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執照內只須注明‘游歷字樣,不必再寫‘通商等字樣,以免牽混。”[28]2052-2053另外,由于列強對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心存覬覦,他們“往往于游歷照內敘入查勘礦產,朦混請印,為異日爭辦礦務之據。”[29]對此,清政府皆依據條約進行處置。如1899年,因德國礦師柯和的游歷護照內填注有“查礦”字樣,清政府認為其有違約章,且“恐因而別生枝節”,即“照章批駁,飭令注銷” [30]。還有些外國人在護照中私自填有“查察佛教”等字眼,或持游歷護照從事宗教活動。如1900年,因日本教師紫云元范的游歷護照中有“查察佛教”字樣,清政府認為這與上年的“柯和事件”性質相同,即參照“柯和事件”的處理辦法,飭令其盡快將“查察佛教”字樣涂銷,并知照日本領事聲明,護照上只可注明“游歷”字樣。再如1910年,美國宣道會牧師程文熙持游歷護照,欲在廣西北流縣城開設教堂進行傳教,廣西當局認為,“洋人傳教,定章應領外務部傳教諭單,該教士只領游歷護照,遽欲朦混傳教,亦與定章不符”,且該地“民情蠻悍,匪風未靖”,地方官“恐滋生事端,迭次勸阻” [31]501。此類事件的頻繁發生,引起了清政府的強烈不滿。外務部認為,此類事件“已屬非是今借游歷為名,實則查察佛教,更違約章”,以后的游歷護照內“如有約所未載之事概不發給。凡從前誤行填出之照,一概涂銷。如果地方官遇有此等護照到境,亦可隨時扣留,稟請上憲酌辦。”[32]在此基礎上,外務部進一步規定:“惟護照中只填寫游歷字樣,不得注明調查地方事宜及商務、學務等事”[33],以免流弊而除糾葛。
為了切實規范游歷護照的內容,1911年清政府明確要求各關道:嗣后遇各國領事將游歷護照送請蓋印時,查明照內如有“通商”二字,即“備函聲明,如在內地賣洋貨、買土貨,應照章完納稅厘,不得長住、開設行棧,并不得在各省內地探勘礦產” [34]。再者,針對洋人在護照中擅填游歷“十八省”字樣現象的泛化,總署照會各國公使指出:以后若洋人游歷各省,“由何處至何處并經過何處,均于照內一一注明”,游歷省分“或三省或四省”,不得“泛言十八省” [35]5551。從而明確了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游歷的范圍。其外,清政府對逾限護照及執照遺失的處理也做了相關規定。清政府簽發給各國的游歷護照中,大多沒有標明使用期限,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一般以一年為期。對于逾限的游歷護照,總署指示各關道,“逾期作為廢紙,仍呈本關繳銷” [28]2020。1903年,僅九江道繳銷的逾期執照登記在冊的就有六十四張。至于目前“各關卡所發游歷執照是否均各如數繳銷,并無逾限,自應按時匯折,以憑查核”,并“將按年發銷,各數詳細造具清冊” [36]。針對游歷護照遺失現象,清政府規定:遺失護照者應由該游歷之人“向就近中國官員據實報明,即為知照就近領事官補發護照,送由地方官蓋印發給。”[28]2066上述舉措推動了游歷護照制度的漸趨完善。
三、劃分不同類型,加以區別對待
對于外人在華游歷過程中的種種不軌行為,因有條約在先,不可能驟然禁止其游歷活動。如果商令暫停,清政府又唯恐徒滋口實,無益于事,認為“惟有于無可限制之中稍示區別,以杜窺伺之漸” [10]1049,決定對無約國和有約國游歷者區別對待。1858年的《天津條約》雖然允準外國人持有護照即可前往中國內地游歷,但條約中的“外國人”指的是與清政府簽有條約之國家的人民,不包括那些尚未簽訂條約,或雖已簽有條約但還未正式換約的無約國人民。對于無約國人民游歷內地,清政府最初是嚴行禁止的,“并未換約之國,雖有該國領事官執照,亦不準前往內地”,因為此種人“必有內地奸民隨行”,如果該國人不遵約束,則“先將該奸民扣留,押解回籍,相應知照轉飭辦理。”[35]5536-5537可見,清政府對無約國人心懷戒備,一經發現其擅闖中國內地,即進行驅逐。1861年,荷蘭傳教士古路吉,持有上海道發放的游歷執照前往京城,因荷蘭當時為無約之國,總署當即派人將該教士“押送出城,并移咨三口通商大臣按照條約妥為驅遣” [28]2031。為了杜絕類似現象的發生,總署特行知各省督撫:“凡未設立條約之國及有約之國而并無執照者,均不準任其在內地游行傳教。”[37]這種狀況直到1908年才有所轉機,這一年,東三省總督就土耳其人民要求改護照為執照一事,呈請清政府定奪。清政府雖未答應對無約國人發放游歷執照,但在事實上默許了其游歷中國內地的行為。為了有效管理無約國游歷者,外務部規定:“無約國人民在中國居住或游歷者,中國仍保持施行司法權,與待中國人無異”,總之“無論何事,與各無約國一律辦理”[38]。1909年,義國照會清政府稱,自今以后所有三瑪利訥之人或在中國或在中國所屬之地,均歸義國使館并本國領事保護。清外交部認為,既然三瑪利訥國未與中國訂立條約,則屬無約之國,即應按照無約國人民游歷內地管理辦法執行,但“中國政府仍保持并施行其毫無阻礙之司法權,與待遇中國人民無異” [10]4211。顯然,清政府雖然允許無約國人民游歷中國內地,但對其并不像對待有約國人民一樣提供外交保護。不過,這并不影響無約國人民奔赴中國內地游歷的熱情。
在清政府的默許下,大量無約國人進入中國內地游歷。其中,有不少人趁清末動亂之機,在中國內地從事間諜活動,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進一步增強對無約國游歷者的管理,維護國家主權和利權,外務部接受了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的請求,對無約國人游歷中國內地的辦法加以變通,要求各“已設交涉使省,分由交涉使;未設交涉使省,分由各關道,照部頒照式發給執照。”如果交由他國領事代為申請護照者,“亦照式給與執照,地方官即驗照妥為保護,視同中國人民辦理” [39]。據此,無約國人民以后到中國內地居住抑或游歷,都必須申領游歷執照,并在取得中國外交保護的同時,認真遵守中國的各項法律、法規,如有違犯,則“按例懲辦”。此舉既強化了對外來游歷者的稽查和管理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國司法主權的獨立性,可謂是一石二鳥。
另外,清政府還對不同國家、不同身份地位的來華游歷者加以區別對待。如對于各國親王游歷內地,“須臨時看其品味,酌量接待,不能預定章程”;各國官員游歷則“照約只應保護,原無供給之理” [40],彰顯了清政府游歷管理政策的靈活性和嚴密性。
四、加強安全防護,避交涉而保利權
為了有效保護持照游歷者的人身安全,力避外交交涉,在一些特殊時期,如戰亂時期和中外關系緊張時期,對一些特殊區域,如戰略要地、民風剽悍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區,以及一些皇宮禁地、陵寢重地等,清政府一般都不允準外國人游歷。1907年,福公司洋人貝瑞森等二十余人各擬攜眷屬游歷山西內地,外務部認為其人數太多,“且晉省紳民現正竭力思保全礦產,若忽見大隊洋人來晉,難免不滋駭懼,加以謠言煽惑,倘釀事端為患何堪。”[41]對其加以勸阻,并聲明若有違游歷章程,則不提供任何保護。1908年,有洋教士持游歷護照不顧清政府的禁令前往青海游歷,駐藏大臣認為:“青海等處不準游歷,載明藏約第九條。今給護照與約不符,應即設法阻止,并取銷前給護照,以免釀生意外交涉。”[42]再如,“川省各邊番地,山深林密,該番眾又犬羊性成,難為理喻”,清政府特轉飭“游歷、傳教各洋人,嗣后勿得輕入川省各邊番地。即在內地游歷,亦應限期繳照,以資保護,而便稽查。”[31]166這在一度程度上減少了外人在游歷過程中意外傷害的發生。同時,持照游歷者的生命、財產一旦受到威脅時,清政府都會及時提供保護。1900年,有英國、德國商人與荷蘭國領事官在未通知縣衙的情況下,深夜乘坐禮和洋行的游船到廣東順德縣三洪奇地方游玩,由于船只擱淺而遭到賊匪的打劫。順德縣令獲悉之后,聯合三國領事官,派員“眼同懲辦”,才避免了事態的擴大化。為了懲前毖后,兩廣總督照會各國領事官“通諭洋人教士等,嗣后凡有前來內地各屬游歷、傳教,務必先赴地方官通知,以便驗照,按約保護”,如果不到縣營通報而擅自游行,“倘有疏虞,即不能責地方文武保護之不力” [12]277-279。顯然,只有那些持有合法護照且在官府備案的外國人,才能得到沿途兵弁的武裝護衛,即便是外國官員游歷中國內地也要領取護照,才能得到清政府的認可和保護。1902年,西班牙署使隨帶眷口及友人,申領護照后前往西陵游歷,泰甯鎮總兵兼總管內務府大臣慶福“遵照辦理,并行知易州文武隨事照料,一體保護,暨傳行內務府官員妥為伺應” [43]。1903年,葡萄牙駐華公使阿梅達致信清外務部慶親王,請領護照游歷萬壽山,外務部遂命人籌辦。不久,練兵處提調徐世昌即致函外務部丞參稱:已“傳飭各該經過處所站段看門弁兵,屆時由貴部派弁導引,即查照放進,并飭恪遵禮法辦理,勿得遺誤。”[44]可見,清政府對外國官員的游歷活動亦遵章行事,不過在接待規格及安保級別等方面要略高于普通游歷者。
同時,一些地方政府也出于“自我保護”的目的而對赴該地游歷者提供“特殊”保護。東南路兵備道陶彬認為:“外人藉名游歷,窺我內情,自應設法預防”,況“外人照游歷關系條約,其游歷之趣旨非經查察未能得其真相,禁阻未能,限制非易”,所以,呈請東督和吉林巡撫對到該地游歷的外國人,“寓限制于保護之中,以保護行查禁之法”,“由兵警隨其去向,跟蹤護送,記其行跡,察其舉動,嚴密監察,遇有違約行動,立時阻止”,并及時上報該管衙門,請其“具報核辦”,“庶有以戢外人之野心而維國防于完密” [15]604-605。而兩廣總督陶模則以“廣州口附近地方水道紛岐,盜匪易于出沒,防范尤應周詳”為名,要求“各國人民乘坐民船、游船往廣州口岸百里以內地方游玩者,由該守備填注印簽,派勇駕艇護送至有段船駐扎之處,即將印簽挨段溜交,遞相接護。如遇險僻處所,不宜灣泊船只,并由巡船弁勇詳細指明,此舉系為格外保護,用昭輯睦起見。”[12]393-394顯然,東三省及廣東官員的做法較具策略性,起到了保護、監督、限制外國游歷者的多重作用,有利于國家安全和地方利權的維護。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外來游歷者依約可以得到地方官府的保護,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官有為其提供饋贐及供給的義務。由于地方官最初缺乏辦理外交的經驗,也不知條約俱在,以致于經常遭到一些不法之徒的勒索和欺詐。如1897年,德國人諤爾福帶通事李文廷到長沙游歷,李文廷利用諤爾福的名義對湘潭、衡山、衡州等地官府敲詐勒索,不僅索要銀兩、寧綢、珠玉古玩等物,甚至索要婢女,“動以開釁恫喝”,地方官恐其決裂,除婢女外“皆從豐饋送,并致公函極道歉忱”。此事雖非諤爾福所為,但其“縱令通事到處詐冒需索”,不僅“不知自責”,反而“捏辭聳聽,圖掩飾”,亦難脫其咎[14]578-578。針對此事,湖南巡撫出示公告規定:“以后若有洋人游歷,嚴禁無禮生事,弊處應嚴札飭禁。”此類事件也引發了清政府的反思,總署認為:“向來各國洋人,無論官商或奉差或游歷,前往內地各處……一切舟車費用均系洋人自備,從無中國代辦驛站之理”。據此,外務部特飭地方官府:“嗣后各國洋人無論官差、游歷,前往內地各處,凡經過處所,各該地方官必須將執照驗明,即予放行。如系洋官,只可照料,不準應付水腳。”[28]2062-20631902年,外務部又咨行各省督撫:“查游歷、傳教人等經過地方,向無支給供應之例,自應查照舊章,凡填給護照只須聲明照約保護,不得填寫供給人夫車馬字樣。”[15]139-140此后,隨著外交經驗的豐富,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多次告誡,各地方官對外國游歷者的肆意勒索、欺詐行為不再一味屈從,而是據理力爭、依約辦理,從而逐漸減少了此類現象的發生。
五、結語
晚清時期內地游歷管理政策的形成和發展,是近代中外條約關系發展的產物。對清政府而言,外人進入中國內地游歷關涉國家主權,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所以清政府最初以消極和抵拒的態度待之。但隨著中外條約關系的深化,外國人的條約特權不斷擴大。作為應對,清政府遂將條約義務轉化為國內法,試圖通過法制手段來約束和限制外國人在華的活動。但由于時代環境的局限,清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游歷管理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常常形同具文,難以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執行。不過,它作為晚清對外政策的一部分,是清政府主權意識和國際法理念漸趨強化的體現,推動了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艱難轉型。
同時,盡管中外條約關系是“以不平等和強權政治為內核構筑的國際秩序”,但“同時又帶來國際關系的新模式和新觀念,包括近代交往方式和國際法中某些進步規則,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朝貢體系的缺陷,刺激中國了解和走向世界” [45]。清政府在對來華內地游歷外人管理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游歷可以開闊視野,借以了解各國情勢。然“近世士大夫非無才識宏通、學問淹博之人,而限于方域、囿于見聞,語及寰球各國交際之通例,富強之本計,或鄙夷而不屑道,所謂少見多怪,其勢然也”,“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勢,必自游歷始” [46]。鑒于此,清政府萌發了“遣材干之員游歷各國,以探消息而通聲氣”的念頭[47]。如此,既能夠獲取彼國的情報信息,還可以“深窺其曲折要領,從而學之,歸而求之,我增一長,彼失一恃,足為自強根基” [48],進而改變中國在對外交涉中一向的被動局面。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才有了斌椿、志剛、孫家谷、王志春、傅云龍等官員,及一些貴胄的海外游歷活動。這種活動由最初的零散性、臨時性,逐漸發展到清末“新政”時期富有政治色彩的“廣派游歷”。其實施效果盡管差強人意,但卻促使近代中國以愈益主動、開放的姿態向國際社會靠攏。同時,大量外國人前往中國內地游歷,增進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增強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也為近代中國入境游的開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馬戛爾尼.乾隆英使覲見記:中卷[M].劉半儂,譯.北京:中華書局,1916:16.
[2]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3]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組.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第1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0:173.
[4] 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238.
[5] 各國旅華人數(譯大阪日報)[N].時務報,1897(41).
[6] 各國旅華人數[N].商務報,1900(22).
[7] 各國旅華人數[N].申報,1902-10-12(1).
[8] 外人游歷[N].外交報,1903(55).
[9] 顧廷龍等.李鴻章全集·奏議九[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90.
[10] 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M].李育民,等,點校整理.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11] 交涉錄要:不準外人測繪地形[J].現世史,1908(3).
[12] 澳門基金會等.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13] 北洋洋務局.約章成案匯編·游歷門:卷33[M].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5548.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匯編:第34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315.
[15] 吉林師范學院古籍研究所.清代民國吉林檔案史料選編:涉外經濟貿易[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16] 外務部致南洋大臣電[J].東方雜志,1904(8):132.
[17] 各使允禁軍艦游歷中國內地[J].現世史,1908(5).
[18] 英輪游歷內地之交涉[N].申報,1908-07-03(5).
[19] 陳熾.庸書·內篇卷下:圖籍[M]//趙樹貴.陳熾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4
[20] 朱家英.許景澄集·許文肅公遺稿:卷7[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267.
[21] 勞特派特.奧本海國際法:上卷[M].王鐵崖,陳體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173.
[22] 論中國實行警察權之難及其原因[N].申報,1906-02-06(2).
[23] 柴云礽.外國人游歷內地之起滅問題[J].憲兵雜志,1935(3):3.
[24] 通飭無照洋商不準游歷內地[N].申報,1905-09-13(3).
[25] 威羅貝.外人在華特權和權益[M].王紹坊,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348.
[26] 蔡乃煌.約章分類輯要[M].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452-453.
[27] 許新江.近代外國探險家新疆考古檔案史料[M].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1:279.
[28] 徐宗亮.通商約章類纂:卷20.禮類三·游歷[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
[29] 湖南洋務局移會岳關道飭查照德礦師游歷護照內涂銷勘礦字樣文[N].秦中官報,1904(26).
[30] 飭銷游歷護照別項字樣[N].濟南報,1900(2).
[31]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美國政府解密檔案:中美往來照會集(1846-1931)[Z].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32] 外務部通飭各關道慎發游歷護照電文[N].北洋官報,1905(580).
[33] 北京電外部電各省督撫[N].山東官報,1905(8).
[34] 交涉司王詳各國來華游歷商人如在內地賣洋貨買土貨應照章完納稅厘不得長住及探勘礦產文[N].浙江官報,1911(28).
[35] 北洋洋務局.約章成案匯覽·乙篇:卷33下[M].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36] 九江道瑞咨旅辦處洋商請領游歷執照按年發銷文[N].江西官報,1904(10).
[37] 朱金甫.清末教案: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6:199.
[38] 外務部咨行各省無約國人民游歷辦法文[J].東方雜志,1908(12):179.
[39] 無約國人民游歷改給執照[N].外交報,1909(242).
[40] 大清光緒新法令·外交三·傳教游歷:第8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09:51.
[41] 福公司洋員擬游歷山西內地[N].順天時報,1907(1547).
[42] 札飭取銷洋教士游歷護照[N].吉林官報,1908(96).
[4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清代外務部中外關系檔案史料叢編——中西關系卷: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4:373.
[4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清代外務部中外關系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系卷: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4:219.
[45] 李育民.晚清中外條約關系與朝貢關系的主要區別[J].歷史研究,2018(5):69-70.
[46] 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20.洋務二十·培才[M].光緒壬酉夏月天章書局石印本.
[47] 王韜.弢園尺牘續鈔[Z].北京:朝華出版社,2017:161.
[48] 寶鋆,載齡,沈桂芬,等.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5156.
[責任編輯:陳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