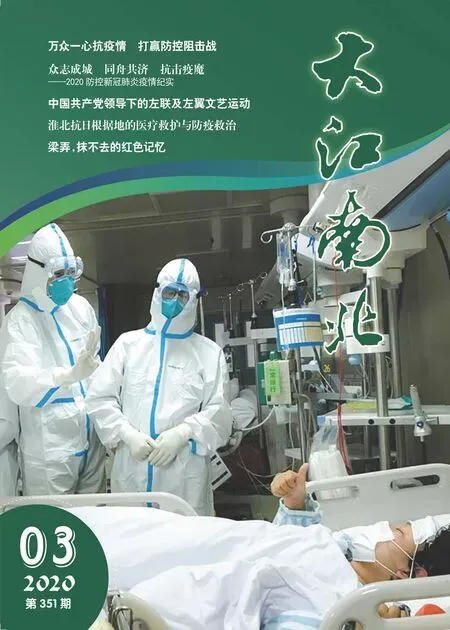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記上海市老干部大學原常務副校長沈詒
□ 陳 羽
上海市老干部大學原常務副校長沈詒先生,因病去世已有三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我的眼前。他生前始終保持著一股蓬勃朝氣,令我常想起一首很有名的歌曲——《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沈詒出身于浙江嘉興的名門望族,自幼受到其堂伯父沈鈞儒先生的薰陶,早在上海讀中學和大學時就參加了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并于1938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黨的工作需要,1941 年他被調入蘇北抗日民主游擊區,之后在新四軍擔任過各種職務。新中國建立后,他先后被調到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南京軍區和福州軍區任職,直到1966 年轉業到地方工作。起初,沈詒是在上海的科研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繼之被任命為上海科技大學黨委書記。
1986 年冬,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老干部大學首任校長鐘民找到沈詒,希望他能來老干部大學主持工作。沈詒時年64歲了,要在老干部大學白手起家,將會遇到的各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具有拓荒牛精神的沈詒卻愿意知難而進,于是他從事老年教育工作的生涯就此拉開了帷幕。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頒布后,上海成立了老干部活動室,但廣大離退休干部并不滿足于下棋、打牌等純粹娛樂活動,而要求緊跟形勢、更新觀念,繼續了解和服務社會,實現求知奮進的人生價值。上海市老干部大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沈詒本身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他深知老干部大學的學員都是從不同的崗位上離退下來的老同志,具有豐富的閱歷和經驗,他們對新生的老干部大學飽含期望與厚愛。因而沈詒清醒地意識到,必須下大力氣辦出一所高水平的具有特殊意義的老干部大學。上海市委給予大力支持,上海高等院校有一大批教授、學者作為師資后盾,一切準備就緒,就看辦學者的動作了。
沈詒辦老干部大學,不但有身體力行的實踐,更有先進的理念與理論。幾年來,他寫出《探索規律多辦實事》《發揮上海教育優勢,拓寬辦學路子》等論文或調查報告40 余篇。他還作為中國老年大學協會常務理事為協會起草了《關于大力推進我國老年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并作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在聯合國教科文老年教育國際研討會上發言,提出若干有建設性的想法,受到廣泛重視。
上海市老干部大學在沈詒主持工作期間,擁有政治經濟、文學、藝術、保健、史地等5 個系20 個專業。1994 年,學校經多方面磋商后成立了上海市老干部大學東方藝術院,使一批持之以恒、學有成效的優秀學員,有了繼續得到深造的機會;同時也讓這個東方藝術院發揮了凝聚人才的“蓄水池”和“人才庫”的作用。
沈詒直到1997 年75 歲才正式離休,但他仍擔任上海市老干部大學顧問、東方藝術院院長,繼續發揮余熱做出貢獻。更難能可貴的是,沈老先生離休后筆耕不輟,抓緊時間寫文稿或整理舊作,于1998 年出版了《謀厥集》。沈老告訴我,謀厥是其祖父給定的號。
三年多前的一天,我在華東醫院病房拜訪沈詒老先生,他拿出上年剛剛出版的新書《始吾之言》贈送給我,并在扉頁上鄭重地為我題字簽名。這本書還有個副題——《漫憶我的大家庭》,我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全書37萬多字,附有許多珍貴的照片。這本少見的大書引起我極大的興趣,自然我們的話題便轉到了他寫這本書的起因與經過。他在該書的自序里說:2007 年8 月他過85 歲生日,雖然兒孫繞膝,滿屋歡聲笑語,但他心頭卻百感交集,回憶往事的閥門一旦打開,便無法合攏。于是他突然有了一種緊迫感,決心要在有生之年把對祖父的記憶、對母親的感恩、自己當年背離家庭北上參加新四軍,以及沈氏大家族的歷史和故事一一記述下來,讓后人知道自己源于何處,又該奔向何方。就這樣,沈老不顧年邁多病,終于在家人和親友的協助支持下完成了這部家族史巨著。

《始吾之言》封面
《漫憶我的大家庭》寫的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家史,而且具有相當豐富的近現代史的史料價值,正如沈鈞儒的堂弟、沈詒的堂叔沈蘇儒為該書寫的序言所說:“作為家族史載體的‘家譜’,同全國到處都有的‘地方志’一樣,成為我們了解和研究中國歷史的寶貴文獻。”為這本書寫序的還有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德,她是沈鈞儒的孫媳婦、沈詒的堂侄媳婦,她在序言中寫的話恰當地評價了《始吾之言》的社會意義:“從詒叔叔的書稿中,幫我梳理了家族間的關系……使我更能體會到沈家這個大家族忠厚為本、詩書傳家的家風……這也折射出我們中國傳統家庭的些許狀況。”
那次我到病房里探訪沈老時,他正坐在輪椅上輸液,絲毫看不出有病容倦態,表現出真誠的樂觀主義者姿態,對我這樣的晚輩也非常熱情。聽他侃侃而談,不禁受到一種精神感染,對他肅然起敬。沈詒老人的革命經歷、工作干勁、特別是離休后努力為后人留下珍貴的精神食糧,讓我難以忘懷,謹以此文緬懷可敬的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