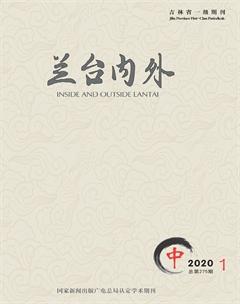數字人文中的定性與定量研究
陳天旭
摘 要: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是社會科學領域中最主要的兩個研究范式,數字人文的興起,為檔案學領域帶來了新的可能,定性與定量研究也不再涇渭分明,而是逐步走向融合,這也對定性與定量研究的整合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關鍵詞:數字人文;定性與定量研究;檔案記憶
當感性傳統的人文學術與以理性著稱的計算機技術相結合,一個不可思議的領域——“數字人文”出世了。數字人文究竟是什么?目前學界還沒有得出權威的概念,在首屆數字人文論壇上,武漢大學王曉光教授和哈佛大學徐力恒博士一致認為“數字人文”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無法清楚界定,未來還將繼續發展。一些國外學者則將“數字人文”定義為充分運用計算機技術開展的合作性、跨學科的研究、教學與出版的新型學術模式和組織形式。“數字人文”的出現昭示著人文學術與數字科技的結合。以往,人文學者多采用定性研究,通過觀測、實驗和分析來考察研究對象的屬性或特征,建立假設和理論,并通過證偽法等方法進行檢驗,在此過程中人文學者是主要研究工具。定性研究具有曖昧性、多義性和評論性,主觀性較大,故以質性研究為主。計算機技術則以定量研究為主,以數字化符號為基礎去測量,更具有標準化和規律性,以量化處理見長。數字人文的發展使二者得以結合,為檔案學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
一、定性與定量研究整合的必要性
1.有利于研究的嚴謹性
定性研究以質性研究為基調,深入研究對象的具體特征或行為,提供深度和細節,能夠根據收集到的各種信息及時做出調整,重點解決“為什么”的問題。但同時,由于定性研究的研究工具是研究者本人,導致定性研究具有樣本量過少、難以總結出客觀規律、時間耗費大以及缺乏隱私性等缺點。
定量研究重量不重質,是用數學工具對事物進行數量的分析,重點解決“是什么”的問題,信息收集和分析過程可實現自動化,大大節省調查時間,樣本的多樣性和廣泛性也得到顯著提高,不僅有效節約成本,研究結果也更加客觀。但定量研究缺乏細節,由于調查結果來自數據反饋,因而不涉及思想和行為的洞察,這也為設置開放式問題提高了難度。
正如馮惠玲教授所說:“數字人文不是在數量祭壇上犧牲質量,而是質量與數量的融合。”如果能夠在數字人文中把二者整合起來,就能夠大幅提高研究成果的準確度,既保“質”又保“量”。
2.有利于創新人文學術與增強檔案記憶的黏性
隨著文化資料逐漸向數字媒體遷移,以印刷術推動人文主義文化資料傳播的浪潮式微,一個多世紀以來,人文學者與人文主義批判者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辯駁,而數字人文的產生則為人文學術的創新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數字人文的高度合作性與學科之間的高跨度使得人文學被重新詮釋為“生產性人文”,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生產文本語言,也生產交流媒介所需的圖像、時間線等。定性與定量研究的結合使檔案學者可以在文本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空間與時間上的多維敘事,從不同的視角得出更有價值、更為準確的研究結果,建構更為真實的記憶。同時,數字人文的生產性還可以解決記憶空白問題,通過各種交流媒介,數字人文可采用各種眾包技術,將記憶工程與普通大眾聯系起來,鼓勵大眾通過各種在線平臺根據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填補記憶的空白,將豐富的人文知識引向大眾,培養一批公民學者,完善檔案記憶。
數字人文也使得單一的數字路徑中得以融入人文主義方法和價值觀,如人文游戲的誕生,使得玩家在玩游戲的同時能夠對當時的事件產生更強烈的共鳴,對人文學術的背景得到更加深入的了解。
3.有利于推動各學科研究
定性與定量研究的整合可以在大量的學術作品和史料中挖掘出新的內容。徐力恒博士在“數據驅動的史學研究——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的建設與使用”報告中鉆探如何通過歷史大數據推動史學研究,他強調,數據可視化能夠幫助史學研究在既有的史料中提出全新的問題,如在宋代4730個進士的籍貫分布和1080年18路人口分布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如“進士的數量與人口的密度是否存在正相關性”的問題。清華美院向帆副教授和朱舜山工程師在“數據可視化與人文藝術——全國美展獲獎作品視覺化分析”報告中對中國第6—12屆全國美展獲獎入圍的2276幅作品進行了數據可視化分析,得出更受到全國美展的青眼的作品集中于紅黃色調等高明度的色調的結論。同時,他們發現全國美展的油畫作品中大畫幅、獲獎經歷、暖紅色調、家園故土主題等因素與入圍獲獎相關度高。原本感性的人文科學中竟也包含著種種數字關系,定性與定量研究整合的必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定性與定量研究整合的適用范圍
1.追溯檔案間的聯系
數字環境中,我們可以便捷地將一份作品的多個版本匯集在一起,也可以將同一類作品匯聚在一起,找尋其中的邏輯及詞頻、語法關系,使用結構化或標簽的方法來識別人物、主題、地點或文本特征,追溯其發展。即使是不同時期的檔案之間也會存在著制度、語言等千絲萬縷的關系。如在法國的土地文件中,我們驚奇地發現大革命后的某些制度居然在中世紀時期就曾實行過。這不僅可以考察文本語言與語法的發展變化,還可以從微觀歷史的角度加深對社會的認識,從而提出一系列新的問題。雖然這項工作也可以僅通過研究學者來完成,但定性與定量研究的結合能夠大大加速這一進程。北大圖書館朱本軍就曾發表過“GIS輔助戰國歷史地理研究”的報告,他利用GIS系統找尋線路之間的關系,成功解決了傳統史學研究難以處理的戰國時期的交通線路問題。
2.實現多維敘事
微觀研究一直是人文學的核心,通過微觀閱讀,人文學者可以深入理解文本內涵,進行一系列研究活動,而在數據庫中,一切都是為了探索更大的趨勢和模式。數字人文將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能夠從多個角度對所掌握的數據進行分析。在宏大的數據庫中,我們可以在研究結果中插入各種數據集,通過非線性的方式呈現論證,在更龐大的背景下衡量事物的意義,實現檔案記憶的多維化。這樣,研究結果才能不浮于表面,探索更深層次的意義。當數據庫中加入了人文主義方法和價值觀,這些數據才能帶我們探索數字之外的天地。
三、整合時要注意的問題
1.避免極端對立
當代數字人文內部存在一種緊張關系:一派強烈推崇定量研究方法,另一派則繼續堅守人文學領域傳統的定性研究方法。實際上,數字人文的關鍵在于跨學科、多領域合作。法國史學家使用數字技術研究法國十九世紀新兵情況,最后得出的結果僅僅是北方人高,南方人矮。美國史學家運用數學方法調查美國南部奴隸制經濟,得出的卻是南方奴隸比北方工人生活條件好的顛倒黑白的結論。在定性與定量研究整合的過程中,任何一派占絕對優勢都不利于研究的進展,我們應當吸收各自的長處,克服自身局限,以人文理念為指導,數字技術為支撐,做到質量數量兼長。
2.要符合辯證唯物主義
唯物辯證法指出,量變引起質變,在新質的基礎上,事物又開始新的量變。我們在數字人文實踐中運用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時,要遵循物質變化規律,以定量研究為基礎,在一定的樣本數量的基礎上進行定性研究,這樣得出的結果才能更具有說服力。
3.培養“刺猬狐”型人才
希臘詩人阿爾奇洛科斯分別以狐貍和刺猬來代表世界上的兩種人:“狐貍懂得很多伎倆,而刺猬則有一技之長。”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以賽亞·伯林則用其描述兩類思想家:“一類人將一切都歸入一個單一的中心,他們的中心系統有著不同程度的完整性和清晰性;另一類人則同時追逐若干個互不相連甚至相互矛盾的思維線索,這些線索之間可能只是有些現實意義上的關聯。”在數字化的現在以及走向更加智能化的未來,知識系統將會發展得更加龐大,我們應當將二者相結合,既保留樂于學習的狐貍式思維,又保留嚴謹認真的刺猬式思維,對世界有著廣泛看法的同時又能專心研究某個特定的領域,實現數字人文新的轉變。
四、結語
1959年,利瑪竇在中國提出了建造“記憶宮殿”的計劃,四百多年過去了,如今的檔案學家們仍在堅持不懈地建造屬于全世界共同財富的“記憶宮殿”,數字人文的產生使得“數字檔案館”這一概念越來越廣為人知,我們應當將定性與定量研究最大限度地結合起來,更好完善檔案記憶。
參考文獻:
[1]朱本軍,聶 華.跨界與融合:全球視野下的數字人文——首屆北京大學“數字人文論壇”會議綜述[J].大學圖書館學報,2016
[2]安妮·伯迪克,約翰娜·德魯克,彼得·倫恩費爾德,托德·普雷斯納,杰弗里·施納普.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游戲規則[M].馬林青,韓若畫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3]朱本軍,聶 華.互動與共生: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第二屆“北京大學數字人文論壇”綜述[J].大學圖書館學報,2017
[4]李傳印.論史學的定性與定量研究[J].安徽史學,1987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