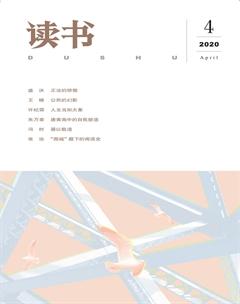巨人的智慧及其身體奧秘
徐明
拉伯雷在《巨人傳》中塑造的高康大和龐大固埃父子不僅是世界文學中的經典形象,也是其人生哲學的代言人和踐行者。巨人父子有著異于常人的外形和體能,不僅衣著起居需要耗費驚人的人力物力制作,有著過量甚至“過度”的飲食需求和發達的新陳代謝系統,他們還對新事物抱有強烈的求知欲,在印刷革命掀起的新浪潮中勇于探險、勤于思考,在感與知的結合中去認識自身、擁抱世界。可以說,巨人形象是融合了身體、品德和學識的復合物,在感性和理性數倍放大的背后是對平凡人的自然天性和潛在能力的尊重和頌揚,這就是拉伯雷在應對文字符號革命時所懷揣的人文主義理想。
借助拉伯雷的放大鏡, 當代法國哲學家米歇爾· 塞爾(MichelSerres,1930-2019)看到了巨人形象的現代身影,他認為處于信息革命中的現代人面對的是與拉伯雷的人物相同的境遇。高康大父子所在的印刷革命時期是一個集宗教改革、古風盛行、文藝復興為一體的轉型時代,印刷書籍為頭腦卸下了繁重的記憶負擔,如釋重負的大腦能夠去從事更加復雜的思維活動,而閱讀又激發了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使人們積極參與到將思想轉化為現實的體驗中去。在塞爾看來,信息技術使知識外化為電子產品的顯示器(屏),搜索引擎掃除了知識傳輸的空間阻礙,使頭腦和身體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這將是孕育新的巨人誕生的搖籃。與此同時,塞爾也提醒到,書架上的典籍、儲存器里的資料只是客體化的頭腦,只有當信息轉化為真正心領神會的東西,當頭腦重新回到身體時才能實現主體的身心合一,而拉伯雷的巨人智慧則為我們處理自身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建議。
“知識的淵藪”
在十六世紀的法國,索邦大學的經院哲學家占據了知識界的主導地位,他們在繁復的論證、機敏的應答和雄辯的口才中決定學識的多寡,按照法國歷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在《十六世紀的不信教問題:拉伯雷的宗教》中所言:“這是比武大會,而非真槍實劍。”身處這一環境中的拉伯雷不得不說是一個特例,他不僅是一個修士,也是醫學博士、法律顧問,還在大學里教授天文學,可以說他是一邊誦經一邊撰寫科學論文,與此同時還發明了一些醫療器械。在印刷術盛行的時代,拉伯雷作為一個集知識和實踐于一身的人文主義者,并沒有像經院學者那樣對印刷書籍心懷恐懼而封閉在傳統的思維模式中,相反,拉伯雷更愿意讓“精神和書在一起就跟干柴碰到烈火一樣,難解難分”,這其中產生的興奮之處就是知識的推動力量,一種由求知欲激發的巨大潛能,而人本來就應該成為一個“知識的淵藪”,這是高康大對其子龐大固埃的期望,也是拉伯雷對巨人的思想和身體的生動概括。
在那封著名的家書中,高康大指出了兩種知識以及兩種不同的習得方式:一種是書面知識,需要勤學苦讀才能在精神上有所收獲;另一種是文字以外的知識,包括德行的培育和來自日常經驗的判斷,這是無法用文字表達但卻更為重要的知識,只能通過由內而外的理解和消化才能獲得。需要注意的是,拉伯雷借高康大之口提到的“第二種知識”幾乎貫穿了《巨人傳》的全部五卷本,這是一種融合了理性與感性的身體智慧,其中,“消化”是巨人哲學的關鍵詞,也可以視為拉伯雷對亞里士多德“凈化說”的戲仿,它不但是對閱讀帶來的精神活動的消化和輸出,還是生理系統對外來信息的去粗取精甚至消化排泄的過程。拉伯雷把人的自然本性置于首位的做法顯然是在反對“人性本惡”的宗教禁欲主義,而對身體需求不厭其煩的夸張描述則是在激烈地反抗經院學者脫離世俗的空洞言辭。
塞爾也因此稱贊拉伯雷的勇氣,敬佩他能夠在索邦大學那些神學家的嚴苛審查下寫出一部專注于描述人的進食、飲酒、消化、睡覺方式的書,他在《拇指一代》中寫道:“我傾向于站在拉伯雷這邊,而不是索邦大學教授那邊。”根據塞爾的分析,從印刷革命到現代信息技術,知識載體由書本上的字母變成屏幕上的圖像,認知方式也從閱讀書頁上的單一符號過渡到瀏覽屏幕上的信息內容,網絡技術特別是信息搜索帶來的便利使抽象概念走向了具體的特殊性。然而,信息并不一定是知識,塞爾在二0一八年接受澳大利亞學術專欄《談話》采訪時提到,現代人因對技術盲目自信而忽視了認識論問題,“信息成為交流方式的同時,也是好壞兼備、善惡兼具的事物,我們有大量信息,但我們卻沒有知識”。如何獲得真正的學識,這是塞爾最關心的事,與拉伯雷同處于印刷革命時期的蒙田也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寧要一個健全的頭腦,不要記憶裝得滿滿。在此,塞爾提出了關于頭腦和身體的思考,即實現一個完整的認知過程需要做到的身心合一。
成為知識的“淵藪”而不是“漏斗”,這是巨人智慧給我們的啟示。當信息網絡為人際交流掃除障礙,在時間上留出更多空余可供自由支配時,我們得到解放的頭腦便可以重新回到身體并投入到新的研究和創造之中。這是拉伯雷從一個社會轉型中看到的有利于巨人形象誕生的機遇,塞爾則更進一步指出這枚拋向空中的硬幣還有另一面:那些外化為顯示器的頭腦是否還能回到身體,或者說,技術再一次把我們推到了身心可能分裂的十字路口—是讓技術繼續取代文字符號成為觀看世界的方式,還是將久被忽略的感性體驗重新提上日程,像巨人一般在受益于技術進步的同時仍不忘培養自身的所思所感?
“不協調性的集合”
塞爾沿著拉伯雷這條阿里阿德涅之線發現了技術與身體之間所隱含的世俗化問題。自然科學的高度專門化把人們對精確性的追求發揮到了極致,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使作為知識媒介的技術工具正在取代人自身去認識世界,但是這一幕并不陌生,早在十七世紀近代科學誕生以來,科學家和哲學家們就開始使用實驗科學方法去定義自然、尋求真理,把能夠用語言清晰表達的歸入理性和正統,而那些無法言說的模糊之物則被排除在真理范圍之外。如此一來,感性就被驅逐出語言的邏輯框架,認知的整體平衡也被破壞,最后還導致了作為認知主體的人自身遭到忽視。在《五感:一種混合身體的哲學》(The Five Senses: A Philosophy ofMingled Bodies )中塞爾把這種對技術趨于神學化的崇拜視為“世俗化的失敗”(a failure of secularity),而將知識的堆積看作一種“消化系統疾病”(adigestive problem),因為被當作圣物供奉在神龕中的技術產物一旦成為衡量現實的唯一標準,它就失去了與現實相聯系的功效,并反客為主地成了人的主導者,這使得巨人般的認知主體有可能在技術去世俗化的過程中淪為機器的“精神幽靈”(phantom)。
正因此,塞爾將拉伯雷視為技術革命時代的先鋒,他筆下的人物不僅擁有對智性的追求,還渾身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智慧。與神話中的巨人形象不同,高康大父子有著普通人的想法和性情,他們的不同尋常之處并不是具有神一般的超能力,而是他們身上有著比普通人放大多倍的身體能量,比如童年龐大固埃“每頓飯喝下四千六百頭奶牛的奶”,他少年時“記憶力更是好得可以裝下十二大桶橄欖油”,成年后在一次出海前痛快地“喝了兩百三十七大桶酒”,等等。在此,精確的數據與模糊的輪廓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是巨人區別于常態的不協調性。但是拉伯雷并沒有對此大費筆墨,不像他同時代的英國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借助測量和計算的準確數據來達到真實性的寫作意圖,拉伯雷把工具性的證明放在第二位,把人以及人的身體感覺放在第一位。
巨人世界因不對稱性呈現出的各種現狀其實是對禁欲主義理想的宣戰,在《環游世界的作家、學者和哲學家》(?crivains, Savants etPhilosophes Font le Tour du Monde )中,塞爾指出巨人的故事是諸多“不協調性的集合”(des ensembles disparates)。事實上,拉伯雷并不局限于對理論的概念思考,他還熱衷于羅列由個體特殊性帶來的偶然性,他的寫作方式更多地關注事物發展的過程而不限制在結果的推理程序之中,強調的是事物或事件的多樣性而不是傳統哲學追求的觀念論,因此,世俗化的巨人可以到現實中去暢游,在空間中去為諸多不協調性建立相互關系。例如,龐大固埃不滿足于圖書館的藏書,毅然踏上了尋找神瓶的旅程,一行人馬在經歷各種艱難險境和奇聞趣事之后最終求得了神諭:“喝吧。”針對龐大固埃的這場“朝圣之旅”,我們可以借助塞爾在《赫爾墨斯文集:文學、科學和哲學》(Hermes: Literature, Secience, Philosophy )中對“奧德賽”的兩種解讀來理解:一種是“命運之旅”,這是如俄狄浦斯照著德爾斐的神諭,按照理念“文本”去執行的行程計劃,其結果必然是俄狄浦斯的命運悲劇以及等待奧德賽返鄉后的一系列仇殺;另一種是“漫步之旅”,更注重“旅行過程”而非目的地,其中充滿著冒險和驚奇,就如奧德賽在海上漫游了十年所收獲的充實經歷,這是人在現實中的生存實驗以及記憶儲存式的身體書寫,等待他的自然是回家之后的團圓和暢飲。
顯然,拉伯雷為這趟朝圣之旅披上了自己“職業的道袍”(費弗爾語),他所掩護的或說是根本掩蓋不住的就是巨人身上流溢出來的生機勃勃的人性氣息,這種旺盛的生命力在塞爾看來完全超越了歐幾里得幾何學空間的認知秩序規范,而在拓撲學空間產生出了身體體驗的多樣性。因為不管是觀看聆聽,還是觸摸、擁抱甚至感受苦和樂,都是更為可靠的真實性。由于身體所在的多維空間突破了思維能夠計算的精確邊界,這使得主體的認知既有理性作為保障,又可以借助靈活的感覺直接做出判斷,也就是說,精神活動離不開身體這塊基石。雖然拉伯雷之后的近代科學將模糊的感覺排除在真理之外,將無序的感覺經驗與有序的心智活動對立起來,但是揭開技術的面紗、回到理性霸權的源頭就會發現,久被遮蔽的巨人依然還在那里,身心合一的強大潛能讓他在經歷印刷革命之后又一次出現在信息技術的浪潮之中。
米歇爾·塞爾其人其思
米歇爾·塞爾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科學史家、法蘭西學院院士,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求學期間學習數學和古典文學,并于一九六八年以《萊布尼茨體系及其數學模型》獲得博士學位。塞爾生前任教于索邦大學、斯坦福大學、蒙特利爾大學等多所海內外高校,出版專著達六十余部,內容涉及哲學、科學、文學、美學、生態學等領域。塞爾的哲學思想繼承了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開創的法國特色的認識論傳統,將科學與詩學相結合去探討人與自然、物質與精神之間的關系,到理性與感性的對話中去尋找雙方合作的可能性。
塞爾的思想軌跡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早期著作借助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信使形象為自然科學與人文藝術的互通往來開辟航線,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思考聚焦于自然科學與生命哲學相互對照的體驗與反思,二十一世紀后則移步至人類學中去研究人與科技的關系。可以說,塞爾的一生都在縫補著由學科分化導致的知識裂隙,這也構成了他的哲學研究中的關鍵詞即“混合”(un mélange)的概念。不管是學科間的融會貫通還是認知方式的感知匯合,塞爾的混合哲學所歌頌的認知主體有著拉伯雷式的巨人形象,但這也旗幟鮮明地顯示出他的知識論拒絕巴什拉的“認識論決裂”(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他反對巴什拉使用理性技術去對現象進行區分或提純,認為那種唯理性主義是一種化繁為簡、化異為同的非理性模式,提倡在考察科技發展的同時不忘人文關懷的優良傳統,即以人本位為基礎去進一步開拓理性的廣度和感性的深度。
進入數字化時代,塞爾從技術帶來的社會轉型中看到認知方式從血液循環般的書籍印刷轉變成了一個更為復雜的神經網絡系統,在人對技術的依賴日益加重的同時,身體也面臨著逐漸喪失感知力和判斷力的風險,因為那些觸屏圖像、視覺瀏覽以及媒體信息既沒有在大腦中形成曲折的神經回路,也沒有在皮膚上產生記憶的摩擦,更不可能鑄造出龐大固埃式的混合身體智慧。面對信息這把雙刃劍,塞爾在二0一0年接受訪談時反思說:“也許,我們現在還沒有學會如何在網絡中智慧地航行。這種官能是網絡的女兒,但不是網絡的母親。”
的確,認知能力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它除了后天的習得和培育,更離不開到現實的旅途中去發現和完善,這是一個將資訊化為知識,再由身體進行翻譯和轉化的創造過程。拉伯雷將身體的奧秘寫進巨人的智慧里,塞爾將其呈現給再一次處于技術革命中的現代人,并且還留下了信心滿滿的祝愿:“我們會擁有自己的奧德賽之旅,那將是全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