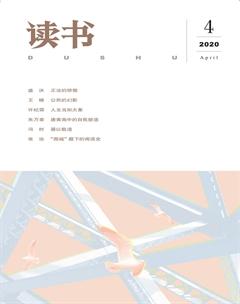劫灰飛盡古今平
廉萍
趙珩《彀外譚屑》中收趙守儼《幻園瑣憶》一文,其中有一段:
由于生長在亂離之中,從小我就感到任何事物都是靠不住的,對于這座小園, 因為愛之過深,就產生了一種“怕”——深恐什么時候會失去它,與它永別。我所碰到的許多事都往往勾起了這種聯想,可是這種思想活動,當時不敢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記得我在書房里讀過一首長篇紀事詩( 似乎是南北朝無名氏作品,原詩始終沒有再查到過),作者是一位婦女( 或模擬一位婦女),在戰亂造成的顛沛流離中,追憶當年恬靜美好的家庭生活,其中有這樣兩句:
溶溶日影上闌干,花落庭前鳥聲碎。
它引起我許多的聯想與深刻的共鳴。我把詩中的環境完全想象成我父親書房中暮春之際的景象,我想有一天我會不會和此詩的作者一樣,以同樣凄楚的心情來追憶小園中這段恬靜的生活呢?想到這里,我幾乎無法克制內心強烈的傷感,這種傷感直至今天還常常再現。
趙守儼先生是著名學者、出版前輩, 文章以學術著作為主,平實嚴謹。趙珩也說這篇“從內容到文風都與他平時的文章迥異,但卻是他內心深處有感而發的純情之作”。寶玉聽完黛玉葬花后,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曾在大觀園悲嘆“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幻園”新主人揚之水也曾在日記中寫下:“此所在非是不易之居,焉知何時即將易主。”可見有情之人,古往今來,感慨如一。
戚戚之余,不免對作者“始終沒有再查到過”的原詩好奇,“溶溶”兩句,也實在不太像六朝風味。好在如今網絡發達,一下就查到。原來是明初作品,只是“溶溶日影”,應當寫作“融融日影”。全詩太長,開頭幾句是“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接下去寫千辛萬苦、今昔對比,不全抄了。
刻印于嘉靖年間的楊慎《皇明詩抄》(五卷本),卷四已經收錄此詩,題目《題郵亭壁歌》,作者標“宋氏”,應該就是根據詩中所說“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宋學士即宋濂。《萬歷云南通志》卷十一載:“宋氏,金華人,其夫任閬州守,洪武中以誣卒于獄,宋坐戍金齒,扶其姑來戍,節操凜然,有郵亭題壁詩。嘉靖十六年,御史陰汝登立祠以祀之;三十二年,御史黃中刻其詩碑于祠。”祠、碑今不存,據說詩有殘拓。宋氏生平,應該也是根據詩意,撮要敷衍而成。總之,嘉靖年間, 此詩已經開始流傳。此后,由明至清,胡文煥《胡氏粹編》、酈琥《彤管遺編》、鐘惺《名媛詩歸》、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錢謙益《列朝詩集》等均有收錄,作者亦都標“宋氏”,惟詩題小異。民國時還曾收入商務版初中《國文》課本。
乾嘉學者桂馥《札樸》卷十“滇游續筆”也記載了此詩始末,并評論說:“今讀其詩,詞意率直,音節悲涼,有古樂府之風。”我很懷疑大概就是這句“有古樂府之風”,誤導了趙守儼的記憶,以為“似乎是南北朝無名氏作品”。趙氏沉潛經史,本不以詩為意,自然無妨。但他以為作者“或模擬一位婦女”的直覺,卻很有道理。詩的前半部分,鋪敘宋氏的悲慘遭遇,后半部分忽然插入“同來一婦天臺人, 情懷薄似秋空云。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的情節對比,忽然大發“吁嗟風俗日頹敗,廢盡大義貪黃金”的迂闊議論,都不太像是婦人口吻。“路傍過者為酸心”,作者則一如中國古代文學同類作品(《兵車行》《連昌宮詞》《秦婦吟》等)中的旁觀者,也忍不住直接露面。
明末清初學者周亮工認為,這首詩的真正作者是明代男性詩人陶振,詩題原作《戍婦行》。《因樹屋書影》卷二載:“林若撫曰:明初宋氏《題郵亭壁歌》,《彤管遺編》《明人詩抄》俱摭入,而不知此詩乃陶振子昌所作,見《瓊臺清嘯集》,名曰《戍婦行》,初非出于宋氏也。振,吳江人,自號釣鰲叟;明初至金陵,進《紫金山》《金水河》二賦,被寵遇。其七言歌行擅場。若撫吳人,斯言有據。”言之鑿鑿,是很有價值的線索。可惜眼下還沒查到陶振《瓊臺清嘯集》。
陶振的生平著作,《江南通志·藝文志》《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等都有記載,和周亮工所言相合。目前市面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筆記叢書”、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三四二冊子部四庫撤出書”版的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陶振”之名都誤為“白振”。
不管作者是誰, 這首長詩所描述的洪武年間宋氏的悲慘遭遇,當年應該不是個案,所以才會引起廣泛同情。宋氏丈夫的詳細案情,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因為這首詩,終究有所流傳。揚之水《〈讀書〉十年》(百花文藝版)第五卷收錄王泗原先生的一封信札(“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曾提及王氏先人在明初的滅頂之災:“族譜有的事也不敢直書,明洪武年間族中因重案株連遭抄沒。什么重案,缺載。口頭相傳是血洗。”當年人人噤言的那段痛史,如今徹底湮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