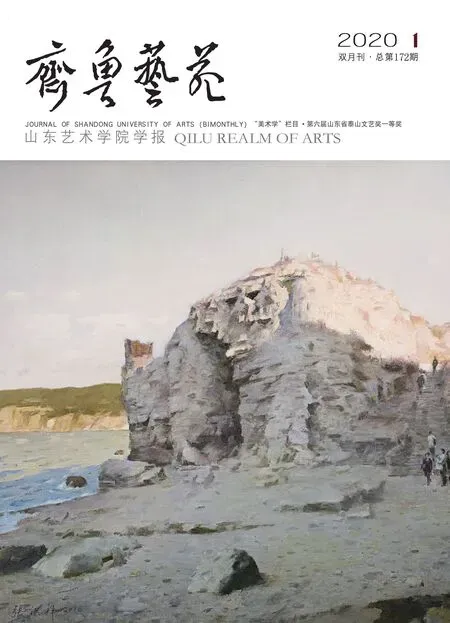沉思與游戲
——解讀塔法奈爾《田園風格的行板與小諧謔曲》
陳 歌,李文菁
(山東大學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克勞德·保羅·塔法奈爾 (Clande Paul Taffanel,1844-1908) 是現代法國長笛學派(1)法國長笛學派形成于巴黎音樂學院成立之時,即1795年。當波姆長笛代替巴洛克長笛走上歷史舞臺,現代法國長笛樂派即拉開序幕。的奠基人,他終其一生將長笛藝術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作為長笛演奏家,塔法奈爾追求優雅、自然的音樂表達,雖然擁有一流的演奏技法,卻從不賣弄;作為音樂教育家,他不僅編纂了長笛經典教材,還改革了長笛教學模式。此外,塔法奈爾對法國早期音樂復興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他將很多被歲月掩埋的長笛經典作品如巴赫的奏鳴曲、莫扎特的協奏曲等重新挖掘,對長笛音樂作品的再發現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本文所要分析的《田園風格的行板與小諧謔曲》是塔法奈爾晚年時期的代表作品,樂如其名,作曲家用音樂指引我們進入到美好的田園風光之中,看孩子們嬉戲玩鬧。
一、歷史背景
塔法奈爾出生于法國盛產葡萄酒的波爾多,自幼跟隨父親學習長笛,16歲考入巴黎音樂學院。在音樂學院期間,他分別獲得過長笛、和聲與賦格的第一獎,這為其日后的表演及創作生涯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19世紀是長笛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此之前,長笛因為音色、音準等難以攻克的技術問題一直屬于樂隊中的邊緣化樂器。直至1847年,德國巴伐利亞的長笛演奏家、作曲家和樂器改良家西奧博德·波姆(Theobald Boehm,1794-1881)通過多次嘗試研究出了新的指法系統,制定了長笛的標準化,確定了長笛準確的音孔位置和按鍵系統,同時也擴展了長笛的音域,于是出現了現如今最為常見的長笛。新型波姆長笛的音準更加穩定,操作也更加方便,由此長笛音樂的發展較之前有了質變的飛躍。塔法奈爾作為新型波姆長笛的擁護者,對其進行了大力推廣,并用自身嫻熟的技藝證明了新型長笛的優雅與表現力。
塔法奈爾在18歲時作為長笛演奏家任職于喜歌劇院、巴黎歌劇院和巴黎歌劇院管弦樂團,直至48歲,即1892年。在此期間,塔法奈爾分別于1872年、1879年創辦了古典協會和管樂室內樂協會,演出和推廣了眾多國內外優秀音樂作品。1893年,49歲的塔法奈爾被聘為巴黎音樂學院的長笛老師與巴黎歌劇院的首席指揮。在教學方面,塔法奈爾將傳統的大師班教授形式調整為教師與學生一對一的授課形式,還將包括巴赫、莫扎特等外國作曲家的音樂重新發掘,對法國早期音樂復興做出了貢獻。與此同時,塔法奈爾還邀請當時的作曲家為長笛創作比賽和畢業考試的曲目,極大地豐富了長笛音樂作品,如法國作曲家加布里埃爾·弗雷(Gabriel Faure,1845-1924)的《幻想曲》,羅馬尼亞作曲家喬治·埃內斯庫(George Enescu,1881-1955)的《如歌與急板》等。這些作品都是由極具抒情性的慢板樂章與突出技巧性的快板樂章組成,這樣“慢—快”兩部分的結構要求也成為法國長笛學派這一時期的標志性特色。
經由塔法奈爾修訂改編的長笛曲目跨越了巴洛克時期、古典主義時期,一直到19世紀。在今天的音樂舞臺上最為活躍的有:改編自韋伯歌劇《魔彈射手》的長笛作品《魔彈射手主題幻想曲》,改編自托馬歌劇《迷娘》的長笛作品《迷娘幻想曲》以及本文所要分析的塔法奈爾在晚年創作的《田園風格的行板與小諧謔曲》。塔法奈爾在晚年時遭遇身體疾病,《田園風格的行板與小諧謔曲》創作于他離世的前一年,即1907年。塔法奈爾不僅在此作品中充分探索了波姆長笛的音色和技能、優美的旋律以及恰到好處的戲劇性,還引發了自己晚年時期對于生命的感嘆,故爾使得此曲在長笛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音樂本體特點
這首為長笛和鋼琴而作的樂曲分為行板與小諧謔曲兩個部分,筆者將先后對這兩個部分進行音樂本體分析,在把握全曲情感氛圍的基礎上,從各部分的主題與動機入手,分析該作品的和聲與曲式結構特點。
(一)主題與動機
樂曲兩個部分的主題各具特色。通過分析并探究主題間動機的相關性,可以在各個主題之間建立起一定的聯系,提煉塔法奈爾在這部作品中的一致性思維。
行板部分的音樂主題a在全曲中總共出現了三次,是全曲的核心材料。它的基本形態是:圍繞BAFD四個音展開的下行旋律進行,其中包含了兩個動機材料。動機1為復附點八分音符節奏型,主要音高為B和A;動機2為附點十六分音符節奏型。這兩個動機材料是引出諧謔曲部分的關鍵(見譜例1)。
譜例1:行板主題a(第12-13小節)及動機

行板部分主題b在全曲中僅出現了一次。它的基本形態是:一個附點八分音符與多個十六分音符組成的階梯式進行。此時的伴奏聲部為與其配合,在主和弦基礎上以三度和聲音程形式作音階上行運動。與抒情性的主題a不同,主題b具有行進般的動力感(見譜例2)。
譜例2:主題b

諧謔曲部分主題c在全曲中共出現了三次,它選擇了行板部分主題a中動機1的音高材料B和A來發展。其基本形態是:兩個強奏的八分音符A和B“先發制人”,隨后音樂在一系列精巧的十六分音符中展開。此時的伴奏聲部以跳躍的柱式和弦加以配合,明快的節奏使其充滿了活潑、熱烈的氣氛(見譜例3)。
譜例3:動機材料1與主題c的對照

諧謔曲部分主題d在全曲中共出現了兩次,是由行板部分主題a中的動機材料2發展而來。相比于動機材料2,主題d在節奏上進行了擴大,但仍然保持了動機材料2中附點節奏的推動力,這一主題的基本形態是:以富有流動性的小附點節奏型為基礎,音樂呈現出波浪式的上下行運動規律。此時的伴奏聲部以流線型的分解和弦與其相呼應。與活潑熱烈的主題c不同,主題d更具抒情性(見譜例4)。
譜例4:動機材料2與主題d的對照
綜上所述,塔法奈爾利用了行板主題a中的元素來發展諧謔曲,使得這兩個部分聯系密切。雖然從表面上看這種關聯并不明顯,以至于在初次聆聽諧謔曲時,難以捕捉到行板主題a的影子,但是通過對這一隱秘關聯性的分析,更加能夠感受到塔法奈爾精細的創作手法和縝密的音樂思維。
(二)和聲與曲式
這首長笛作品雖然創作于20世紀初,但是其音樂語言、表現手法和結構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浪漫主義音樂傳統。塔法奈爾在創作中引用了中古時期的調式系統,調性變化雖較為豐富,但仍然以傳統的調性和聲與曲式結構為基礎。
1.中古調式的引用
中古調式在11世紀基本得到確立,分為四個正調式和四個副調式。塔法奈爾在此曲中就引入了中古調式,如行板部分的第20小節處:低音伴奏聲部所用的和弦為g小調三級和弦的第三轉位,同時降低了二級音,于是在一級音和二級音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弗利幾亞小二度音程(見譜例5)。此外,行板部分的第43-44小節是在g小調的基礎上升高了四級音,由此在一級音和四級音上構成了利底亞三全音這一特性音程。
譜例5:降二級音的g小調與弗里幾亞調式的對照

2.轉調手法的運用
塔法奈爾在這首作品中主要采用主調與近關系調間轉換的手法。在行板部分中,主題a的出現與再現都在樂曲的主調g小調上進行,只是在對比主題b出現時進行了幾次短暫的轉調:調性首先從bG大調轉向其近關系調bb小調,隨后由于音樂旋律的下方三度模進,調性由下方三度關系的E大調轉向近關系調#g小調,緊接著連接部分又轉調為B大調。
在諧謔曲中,主題c一共出現了三次,其中兩次都經歷了轉調。首次出現時,調性從D大調轉向其上方近關系調#f小調;主題第二次呈現時,調性從D大調轉向其下方平行小調b小調;主題第三次出現時調性始終保持在D大調上直到結尾完全終止。對比主題d則先出現在b小調上,而后由于旋律聲部進行了下行三度的模進,調性也轉為下方三度的#g小調。在隨后出現長達17小節的連接部分中,音樂先后在E大調、A大調和#f小調這三個近關系調上進行。
3.明確的和聲終止
在主調音樂中,終止式是和聲功能體系的重要標志,明確的和聲終止能夠體現出作品的調式調性特征。這部作品的樂句和樂段在結束時都有明確的終止,可以體現出塔法奈爾對傳統功能和聲的繼承。
在行板部分中,樂段A在結束時使用了正格終止形式(見譜例6);樂段B在結束時先用正格終止結束,之后又用變格終止作為補充終止,使得音樂張弛有度,同時也增加了音樂的完整感和結束感。
譜例6:正格終止

在諧謔曲部分中,樂段C在b小調上進行了正格終止;樂段D則是開放式結尾,結束于#g小調的屬和弦上;再現C樂段是在主調D大調上的正格終止;尾聲部分則再次運用了補充終止,這個長達12小節的補充樂句使全曲的結尾更加豐滿而輝煌。
4.曲式結構
“田園風格的行板”部分采用了再現單二部曲式,帶有11小節的引子。主要調性為g小調,拍子在12/8、6/8、9/8之間不斷轉換。圖示如下:

引子部分首先為全曲拉開了田園風格的序幕,結束于半終止。A樂段由兩個樂句構成,結束于完全終止,是一個明確的收攏性結構。B樂段開始的部分具有新的情緒特征,音樂在節奏、速度和調性上都進行了改變。連接句的調性轉為關系大調,結束于升高二級音的屬和弦,該和弦與主調主和弦形成的兩個共同音為主題a的再現做了準備。隨后主題a在材料和調性上都得到回歸,并在結尾處運用了補充終止,增添了從容、安靜的意境。
“小諧謔曲”部分為再現單三部曲式,帶有引子和尾聲。主要調性為D大調,拍子為2/4,速度較快。圖示如下:

引子部分呈現出熱烈的音樂氛圍,結束于半終止。C樂段由兩個樂句構成,是一個開放性的轉調樂段。D樂段采用了全新的音樂材料,調性轉為主調的關系小調,音樂情緒較為陰郁,結束于半終止。連接部分的調性輾轉變化,最終停留在#f小調的六級和弦上,該和弦同時也是主調主和弦,由此暗示了C樂段主題的再現。再現C樂段中的主題與調性同時得到回歸,但是長度有所減少,為縮減再現。在尾聲部分中,塔法奈爾再次運用了補充終止,使結尾豐滿而輝煌。
三、音樂風格與演奏特點
本文在音樂本體分析的基礎上,探究塔法奈爾這一作品的風格特征,以及該作品的演奏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與昔日的波姆長笛相比,今日的長笛在其基礎上采用了開孔按鍵,加入了B尾鍵,并以貴金屬作為材料,在音色、音量和低音區的音樂表現力上更為突出。
1.音色的選擇與呈現
不同的音色能夠營造出不同的情感表達,即使是同一件樂器也具有豐富的音色變化。如長笛的高音區通常明亮而富有金屬色澤,強奏時帶有尖銳的穿透性,弱奏時十分縹緲柔和;而低音區的音色通常比較深沉,強奏時音響豐滿扎實如小號,弱奏時音色婉轉悠遠似洞簫。
此曲中對于音色的選擇首先體現在對于主題的呈現方面。
在演奏不同的主題時,需要借助音色來表現不同的音樂情感。在行板部分中,主題a以中板的速度在附點節奏型基礎上呈現出舒緩的音樂情緒。長笛旋律開始于弱起小節,音區為中音區,這時就需要一種柔和、純凈的音色。當主題b出現時,鋼琴聲部以三度音程作音階上行運動,長笛聲部的旋律為先下行后上行的階梯式進行。與主題a相比,此時的速度要快一些,音樂更具流動性,因此需要表現出一種行進般的堅定的和略微明亮的音色。
與此同時,在演奏相同主題時,也需要選擇不同的音色來表現細微的情緒變化。如在諧謔曲部分中,主題c一共出現了三次,需要使用不同的演奏方式來呈現。首次出現時為強奏,長笛中高音區的強奏以穿透性和力量感營造出一種猝不及防的呼和,正符合“諧謔”的主題;第二次呈現時為弱奏,與主題c的首次呈現形成力度上的反差,另外這種在強拍上的弱奏同樣具有詼諧特色;最后一次出現與首次出現時音樂形象一致,形成前后呼應的效果。在演奏這一主題時,需要關注音色的變化:強奏時需要氣息和腹部力量的共同配合,使得音色飽滿、高亢;弱奏時所需氣息相對較少,為了塑造出活潑的音樂形象,音色需要保持干凈、輕盈。
對于音色選擇的另一個方面在于調性變化。
塔法奈爾在此曲中進行了多處轉調,不同的調性呈現出不同的主題形象:具有柔和甜美性質的主題a與主題d用小調式來呈現,而具有進行曲風格的主題b和熱烈的主題c用大調式來表現。在演奏時,主題a與主題d多使用柔和、略顯黯淡的音色,而主題b與主題c多使用熱烈、較為明亮的音色。
此外,塔法奈爾在相同主題的呈示中安排了三度關系的轉調,向上方音方向的轉調會有一種明朗的感覺,而向下方音方向的轉調會帶來些許陰霾。行板部分主題b首先出現在bG大調上,隨后又出現在下方三度的E大調上。在對該主題的兩次呈現時,需要注意到細微的差別:bG大調上的主題應更顯堅定與明亮,而E大調上的主題則要柔和一些。諧謔曲部分主題d首先為b小調,隨后轉為下方三度的#g小調。在對該主題的兩次呈現時,也有微妙的變化:b小調上的主題情感要更加充沛,而#g小調上的主題較為內斂與柔和。
2.整體結構布局與表現
在行板部分中,塔法奈爾以單二部曲式四個樂句完美地詮釋了“起承轉合”的功能邏輯。A樂段始終在主調g小調中陳述,由兩個平行樂句組成。這兩個樂句在整體上沒有較大的起伏,都從弱奏開始,根據情緒的波動經歷小范圍的力度變化,之后又以弱奏結束。在演奏這一樂段時需要一氣呵成、力度變化自然而不夸張,表現出悠揚舒緩的情緒。當進入B樂段時,音樂情緒變得輕快愉悅。這時的速度變得更加輕快,多次運用突強到弱的戲劇性力度變化,同時調性和節奏也在不斷地改變,音樂形象較之前形成了明顯反差。在演奏這一樂句時需要突出戲劇性的強弱對比,同時音樂更加流暢。緊接著的連接句采用了較多裝飾音和切分節奏使音樂達到高潮,隨后又使用長時值音符和漸慢的速度變化進行緩沖,為主題再現做了準備。在演奏連接句時,要在主題b的情感基礎上更進一層,突出音樂高潮的表現力,然后再逐漸恢復平靜,這一過渡要不留痕跡地進行。音樂主題a再現時速度得到還原,采用了重復音型以及和聲上的補充終止為全曲留下一個意猶未盡的結尾,這時要演奏出略帶憂愁與不舍的情感。
在諧謔曲部分中,塔法奈爾采用單三部曲式來表現樂思的呈示、展開、收攏,以及它們之間的對比與聯系。整體上速度輕快、節奏簡單明確。C樂段由兩個平行樂句構成,采用了大調式明亮的色彩、“無窮動”(2)具有兩種不同含義:其一是以連續不斷的音符為特征且通常節奏較快的樂曲片段;其二是以無限重復演奏的形式演奏整首樂曲。本文中引用第一種含義。式的節奏模式,并在樂句的起始處都安排了由強到弱的力度對比。在演奏這一樂段時,要突出表現無窮動式的旋律所帶來的歡樂熱烈的情緒,需要注意連音和吐音的清晰呈現,尤其是吐音的顆粒感。D樂段的音樂變得抒情起來,采用小調式暗淡的色彩,節奏變得舒緩,速度稍微加快,音樂形象與C樂段形成鮮明的對比。演奏時要著重表現出小調式略帶傷感的抒情性。此后出現了長達17小節的接連部,音樂材料采用了前兩個主題中的元素,并以重復音型的出現和漸慢的速度變化營造出結束的氛圍。但是隨后主題a又再次奏響,這一再現成就了音樂的高潮,最后音樂在無窮動式的旋律中結束。在演奏這一部分時,需要在漸慢的結尾處營造出一種收束感,這樣當音樂的高潮——響亮的主題再現時,才足夠詼諧。
3.音樂的織體與配合
塔法奈爾在此曲中主要運用了主調和聲的織體,突出了長笛旋律聲部的音樂表現性,但是作為單旋律樂器的長笛在音樂表達上難免不夠豐滿,這時就需要鋼琴聲部來渲染音樂氛圍,推動音樂的發展。此曲中的鋼琴伴奏聲部多以流線型的分解和弦織體或柱式和弦織體出現,分解和弦的音響特征可以較好地表現出行板部分音樂的流動性和抒情性;柱式和弦的音響特征主要用于表現諧謔曲部分熱烈歡快的音樂形象。
作曲家將分解和弦織體與柱式和弦織體交互使用,既能夠烘托氣氛,又不至于單調乏味。在行板部分中,具有舒情性質的主題a在鋼琴伴奏聲部采用了十六分音符的分解和弦與柱式和弦相結合的形式,樸素簡單的和聲促成了穩定的音樂情緒,同時凸顯了旋律聲部的音樂走向,使得主題a在發展的過程中層層遞進,音樂進行更加流暢。在演奏該主題時,旋律聲部要嚴格按照音樂進行的方向做出強弱變化,而鋼琴聲部需要緊跟旋律聲部做出適當的力度起伏。主題b是具有動力性的階梯式進行,鋼琴伴奏聲部在主和弦基礎上以連續的三度音程來加強音樂氛圍。在演奏該主題時,兩個聲部要在力度上形成對比與交替,使得聽覺效果變得豐滿:旋律聲部從突強漸弱開始,隨后進行漸強,而鋼琴聲部則與之相反,音樂由漸強到漸弱。
在諧謔曲中,主題c以活潑的四個十六分音符節奏型為基礎,采用無窮動式的寫作手法,洋溢著歡快熱烈的氛圍,鋼琴聲部則使用了柱式和弦進行伴奏。在演奏該主題時,長笛聲部要以靈活、清晰的頓音來表現熱情活潑的旋律,而鋼琴聲部則用帶有頓音記號的“調皮”的八分音符柱式和弦加以配合。主題d是由小附點節奏型組成的抒情性主題,在演奏該主題時,長笛聲部要以強奏和富有表情性的方式來詮釋這一抒情性主題,鋼琴伴奏聲部則是以流線型分解和弦的形式來襯托主題。為了不喧賓奪主,鋼琴聲部需要以輕柔的弱奏來表現音樂情緒,并且加入延音踏板來增強音樂的連貫性。
4.節奏的變換與配合
塔法奈爾在此曲中進行了節奏節拍方面的探索,使音樂打破了規律性節奏的平衡。行板部分在6/8、9/8和12/8之間頻繁轉換,雖然始終以帶有律動性的三拍子為基礎,但在強弱關系上出現了變化,打破了單一節奏的強弱規律。此外,塔法奈爾還利用延長音和連音線打破了節拍重音,避免了節奏運動的機械性。在樂曲的縱向發展上,作曲家為了避免節奏的同步運動,上方旋律聲部與下方伴奏聲部的節奏運動有時并不受統一的模式控制。
在演奏時,兩個聲部需要相互配合共同詮釋出統一的音樂形象。以行板部分為例:在第26小節處,長笛旋律聲部以延長音的形式改變了原有的節奏重拍,使得音樂形象更具動力性,此時雖然低音伴奏聲部并未改變其三拍子的節奏韻律,但在實際演奏時還是要與旋律聲部保持一致。再如第35-36小節,延音線出現在B、A和F上,形成類似于切分音的結構。這三個音打破了節拍重音規律,長笛聲部按照此時樂句的強弱起伏在情感上富于變化,這就需要伴奏聲部放棄原有的節拍重音規律,與旋律聲部保持一致,使二者默契配合,對位準確。
5.裝飾音的應用與表現
裝飾音作為一種豐富音樂形象,增強音樂表現的手段被廣泛應用在作品中。一向不喜華麗裝飾的塔法奈爾在此曲中并為使用過多的裝飾音,僅在行板部分中有所運用,分別是顫音、倚音和波音。
顫音在行板中僅出現了一次,位于引子部分第三樂句的結尾處,即整個引子的結尾處。引子部分由三個抒情的獨立樂句組成,第三樂句的旋律走向是以EDCBA為基礎的下行音階進行,顫音出現在最后一個音A上,這里的顫音表現了一種較為低沉的音樂情緒。在演奏這一裝飾音時,首先需要保持樂句中音色的一致性,按照情緒發展做出漸強到漸弱的變化,其次為了突出引子部分結束的終止感,并在情感上營造出一種不舍之情,顫音的速度可以處理為“慢—快—慢”的變化。
倚音在行板部分僅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引子部分的顫音A之后的同音上,節奏為三個十六分音符的形式,音高為G、A、B。如果將這一樂句比作湖面,顫音就是湖面蕩漾過后將要消失的漣漪,而倚音則是湖面平靜前的最后一絲波瀾。因此這個倚音在演奏時需要與前面顫音的形象形成對比效果,但是這種對比并不能太強烈,只需要做出微弱的力度變化即可。第二次的倚音出現在第17小節,即主題a的首次呈現之后。此時音樂在主題a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但是不再運用主題a中長時值的四分音符,音樂變得更加緊湊起來。因此,這里的兩個十六分音符的倚音在音樂表現中應該更加活潑、俏皮一些,但是為了不影響此處主和弦的鋪墊,演奏時不能用力過猛,而要使重音依然保持在主要旋律音B上。
波音在行板部分一共出現了7次,且均為單次上波音的形式。其中在連接段的兩小節內出現了6次,分別位于連續的6個六連音內。與此同時,這里的波音與切分節奏的出現正好形成了行板部分音樂的高潮。在演奏時需要飽滿的音樂情緒,但是要注意到節奏重拍的變化,以及出現在弱位上的波音需靈巧清晰地呈現。
結語
自誕生以來,《田園風格的行板與小諧謔曲》就以其無與倫比的優美旋律深入人心,廣受長笛演奏者的喜愛,收錄在諸多長笛名家的專輯中(3)《田園風格的行板與小諧謔曲》收錄于由環球唱片公司發行的加拿大長笛演奏家蒂莫西·哈欽斯(Timothy Hutchins)的專輯《法國長笛》之中、由英國唱片公司Chandos發行的英國長笛演奏家蘇珊·米蘭(Susan Milan)的專輯《法國長笛名家曲目》之中、由瑞典唱片公司BIS發行的以色列長笛演奏家莎隆·貝扎莉(Sharon Bezaly)的專輯《牛奶咖啡》之中、由法國唱片公司Saphir Productions發行的法國長笛演奏家菲利普·班諾德(Philippe Bernold)的專輯《隨想曲》之中等。。此外,此曲還以其豐富的技巧性考驗著演奏者的水平,因而常常被用于各類國際國內的長笛比賽中,如在第九屆中國音樂金鐘獎長笛比賽中成為半決賽的指定曲目等。
19世紀初期的長笛演奏家喜好浮夸的炫技性風格作品,使得長笛音樂流落為“只是發出一堆無意義的熱鬧聲音與低俗品味”的代名詞。塔法奈爾整頓了長笛演奏名家的曲目,從歷史的塵埃中找回巴赫、莫扎特等人的經典作品,將其傳承下來。同時,塔法奈爾自己的音樂也不同于20世紀初期在法國占主要地位的印象主義音樂,而更偏向傳統,音樂簡單樸素,音響更加抒情。《田園風格的行板與小諧謔曲》作為塔法奈爾晚年時期的杰作,在誕生百余年后的今天依舊活躍在音樂舞臺之上。行板部分從鋼琴聲部的引子開始就將聽眾帶入一個田園般的意境之中,優美而精致,仿佛置身于塔法奈爾家鄉浪漫的葡萄莊園;快板部分的小諧謔曲像是作曲家與聽眾開的一個玩笑,音樂詼諧、有趣,如同孩童般的嬉戲玩鬧。耐人尋味的是,塔法奈爾在1901年的時候身體遭遇了不適,而此曲創作于1907年,也是塔法奈爾離世的前一年。從這一層面來說,此曲中不斷出現的下行音階和黯淡的小調式也許正暗示了塔法奈爾晚年內心深處的憂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