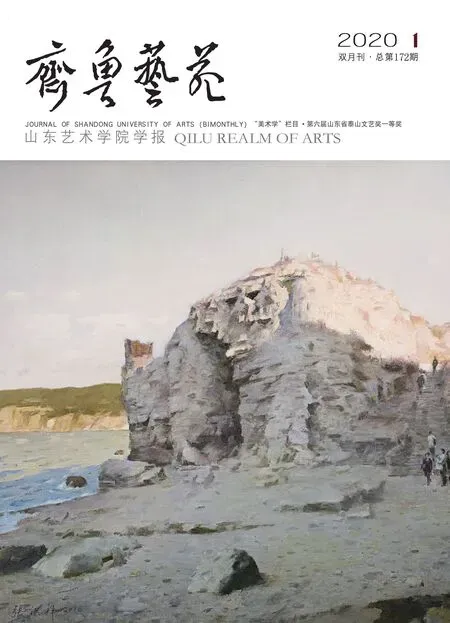產品形態設計的矛盾論
左鐵峰
(滁州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
依循馬克思主義哲學矛盾論,矛盾規定為反映事物的對立統一關系的哲學范疇,并認為任何事物都是作為矛盾統一體而存在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1](P31)根據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產品形態作為產品得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視覺載體與價值依托,其設計的架構是在諸多相關矛盾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中達成的,而各種矛盾因素也必然且富于價值地作用于產品形態設計過程的始終,并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向度與維度呈現出不同的內涵、特質與表征。
一、需求與滿足的供需矛盾
產品是為人服務的,是人需求、欲求的產物。[2](P11)作為產品的價值載體與視覺顯現,產品形態是人需求得以滿足,形成可視供需關系的重要物質依托與方式之一。就物質型產品而言,產品形態設計可詮釋為:設計者憑借對產品造型、色彩、材料等因素的組織、經營與架構,為人需求提供的產品物質層面的“答案”。人的需求同“答案”存在著映射性的矛盾關系,是促發“答案”形成的主要動因、重要的實施依據與關鍵的品評要素。
首先,人類學上,人被定義為能夠使用語言、具有復雜社會組織與科技發展的生物,其需求具有多樣性、源發性、主動性、動態性等特質。[3](P3)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可劃分為生理、安全、愛和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等五類需求,存在著由較低到較高的層次排列。就產品形態設計而言,若要對如此復雜、多層的需求均做出有效回應與高度滿足,其難度不言而喻。同時,相較于人的需求,產品形態設計映射的行為及結果往往是個體的、后發的、被動的與靜態的,無論在時間、空間及心理上也均處于“劣勢”。因此,人的需求與產品形態設計間的矛盾常表現為供不應求、眾口難調。習見的情形是:面對琳瑯滿目、形態萬千的產品,人們總是發出“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感嘆!
其次,在具體的產品形態設計中,需求與滿足的供需矛盾每每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直接矛盾,這種矛盾主要表現在與人需求能夠直接發生關系的產品,比如座椅、家電、工具等。這類產品的突出特點在于其效用和價值直接面向人,人的生理、心理與情感等需求必需在具體的產品形態創設中得到有效的回饋和彰顯;二是間接矛盾,這類矛盾凸顯于為產品生產提供條件的產品,如工程裝備、加工機械、維護設備等。該類產品形態設計優先滿足與服務的對象是與人能夠發生關系的產品,實施與操作的可行性、效率性需求成為其形態設計首要考量的要素,人的需求是以其他產品為中介的形式間接得到滿足。
再次,在需求與滿足構成的系統中,還存在著個體與群體的點面矛盾。現代產品形態雖然可劃分為批量化與定制化兩大類成品形式,但主流是批量化,仍是以一件設計面向多個用戶的供需關系為主。在現有的生產、經營與消費模式下,產品形態的創設多由駐廠設計師或自由設計師的個體來完成。而設計展開的基點、路徑則多以特定用戶群體各項需求的最大公約數為坐標與向度,由此達成的產品形態更多彰顯與滿足的是特定用戶群體的共性需求。如男鞋的尺寸常以39~42碼為主,職業女士的箱包多具有暖灰的色彩傾向,嬰兒用品多會采用富于韌性、穩定性材料等。這是一種在設計和生產源頭出現的“一對多”供給矛盾關系,而相關矛盾在消費與使用環節則轉變為“多對一”的需求矛盾,即大量形態各異的同一產品與用戶個體的采選問題。若某用戶患有“選擇恐懼癥”,就會產生“幸福的煩惱”。
二、理性與感性的思維矛盾
信息論指出:思維是人對新輸入信息與腦內儲存知識經驗進行一系列復雜的心智操作過程。以思維對人言行起作用的角度和方法析之,思維可劃分為理性與感性兩種思維方式。[4](P9)對于產品形態的創設,其思維的萌起、演進與達成同產品及其形態設計的屬性關聯密切。根據李硯祖教授“人造物系統”的層級結構理論,產品從屬于人造物系統結構的中層,其形態設計既區別于以感性思維方式為主要維度的“藝術造物”,亦不同于以理性思維方法為基本向度的一般性手工與技術造物,是實用與審美的統一且與人的生活發生最密切關系的物類創設。在產品形態設計中,設計者的“行事軌跡”常是徘徊、游走于“藝術理想”與“現實應用”之間。這種呈現出一定“矛盾”特質的工作屬性與行為表征決定了產品設計師有別于純粹的藝術家與工程師,注定了他們的命運是“戴著鐐銬而舞蹈”。[5](P2)產品形態設計既有源自設計者理性思維的分析、推理與論證,也有靈感、頓悟和情感等設計者感性思維的身影,兼具了理性與感性雙重思維的屬性與特征。其中,在理性思維導引下,產品形態設計可以按照一定科學方法與設計原則展開,具有一定邏輯與思辨的屬性。因理而生、循理而行、據理而結、以理服人。產品形態設計中“理”的存在,一是源于產品及其形態創設的科技屬性,二是基于特定時空語境下人們需求與欲求的“共識性”;與之相對,產品形態設計亦可表現為瞬時思想、觀念的“靈光一現”,或是諸多素材、問題聚合在一起的陡然“茅塞頓開”,亦或由一個形象到另一個形象毫無征兆與因由的“華麗轉身”,具有鮮明的直覺、靈感、頓悟與感知等感性思維特質。由感而發、行隨情動、借物詠志、以情動人。在產品形態設計中,兩種不同類型思維的存在,雖各具價值,但二者沖突、碰撞的負面效應亦不可漠然視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或引發設計者邏輯的混亂與向度的搖擺,并顯現于具體的形態表征。
同時,作為產品形態設計的接受方,用戶亦會“陷入”理性與感性的思維斗爭。基于克里·彭多夫的產品形態語義學,用戶對于產品的認知需經歷產品的辨明、自我驗證、發現新形式和解讀符號語義等四個階段。無論是認知的哪一階段,產品形態作為產品各種屬性信息的重要載體,均扮演著關鍵角色。用戶可依據自身的需求、閱歷和經驗等,通過產品形態的觀、觸、用,對產品的屬性、操作及內涵等作出感性的體認;用戶亦可在產品實際使用中,憑借對其流程設置、功效發揮與措施改進等問題的分析、論證及推演,構建產品及其形態的理性判斷。至于用戶最終的抉擇,必然是感性體認與理性判斷間矛盾斗爭的結果。
三、構思與實踐的轉化矛盾
對于產品形態設計,設計師種種創新性、建設性的構思需經各類不同階段、形式的實踐轉化,才能為他人所認知與解讀。相較于標識、圖案、影像等設計造物,產品形態設計的構思不僅需要依托手繪SKETCH、電腦建模、模型樣機等常見設計方法實踐的有效表述,更需要來自科學技術、材料及其加工工藝、經營銷售等相關產銷領域實踐的有力支撐。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是客觀、必然的,產品形態設計構思與實踐的轉化矛盾同樣如此。
其一,在產品形態創設階段,就目前的設計手段與方式而言,設計者最先面對的是構思與表達的矛盾,即如何準確、高效、全面地將頭腦中的設計意向以手繪的方式呈現于紙面或屏幕,實現設計意向與二維物象的轉化,在達成瞬間靈感與感性認知得到捕捉、獲取的同時,完成二者間的有效互動,并在短期內取得外界必要的意見補足。該轉化過程的矛盾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想與做的矛盾,即設計者的構思與其手繪表現能力間的“心手一致”矛盾;二是想與說的矛盾,即設計構思與設計者語言表述間的“詞能達意”矛盾。依照一般的設計流程,在SKETCH研討之后,后續的電腦輔助設計與模型樣機制作屬于相對理性的想與做矛盾。其中,電腦輔助設計階段的突出矛盾為設計構思與設計者電腦應用水平的矛盾,體現為設計者的建模、渲染及相關的編輯能力同設計構思的詮釋程度;而模型樣機制作的矛盾則與設計者的動手技能、工具選擇和制作條件等因素相關,表現為二維構思與三維實體的差異性。
值得關注的是:現代設計的任務與目標之一在于賦予產品、服務和系統以表現性的形式(語義學)并與它們的內涵相協調(美學)。[6](P7)作為這一任務與目標的響應,產品形態設計不僅需要依托語義學表現產品設計的構思,還需要這種表現實踐與其構思的內涵相協調,具有美學的價值訴求。因此,在產品形態創設階段,設計者不但有著想與說、做矛盾的困擾,還存在著如何做、怎樣做的矛盾。依循美國設計心理學家唐納德·A·諾曼的觀點,好的設計有兩個重要特征:可視性及易通性。其中,可視性是指所設計的產品能不能讓用戶明白怎樣操作是合理的,在什么位置及如何操作;易通性是指所有設計的意圖是什么,產品的預設用途是什么,所有不同的控制和裝置起到什么作用。[7](P79)基于該觀點,設計者不僅要突破準確、全面地展示產品形態設計構思的實踐轉化矛盾,更要確保轉化的實踐是能為他人看得懂、懂得用的成果,而重視與處理好產品形態的可視性和易通性,無疑是需要攻克的難點和矛盾之一。
其二,產品形態設計實現由構思與實踐的轉化不是想當然的主觀臆造,它需要相關科學、技術的依托、制約與保障。產品形態設計的構思往往是主觀的、理想的,而其實踐的轉化則是客觀的、現實的。科學、技術雖為構思與實踐的轉化提供了可能與可行,但實踐的結果卻未必是最初構思的完全映現。二者矛盾決定了產品形態設計的構思不會是天馬行空的任意放飛,自然與人文科學在為其插上合理與合情翅膀的同時,也制約、束縛著它的飛行能力和路線。如扳手的造型需遵循杠桿原理,汽車的改型需兼顧企業文化的傳承;相較于科學側重知識構建,重在知識應用的技術對于設計構思與實踐轉化的矛盾形成,作用尤為顯著,特別是涉及相關的材料及其成型技術,其策動與約束力更為直接、實效。如金屬鍍鉻及彎管技術與瓦西里椅設計、復雜曲面三維數控彎板技術與055型驅逐艦設計等。需要言明:產品形態設計構思能否得到最終的實踐轉化還取決于用戶的接受能力。物美價廉,用戶在追求產品形態具有美感的同時,價格因素同樣重要,而產品價格的形成亦與其用材、工藝及流通、銷售等實踐因素構成矛盾。
四、造物與環境的系統矛盾
當下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人工化的環境中,為人造物所包圍,設計的重要性自然顯現。[8](P12)根據李硯祖教授的“人造物系統”理論,物質型產品的形態設計是一項系統性的人造物活動。依循一般系統論及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系,產品形態與用戶及其共同維系和存在的環境能夠構成一定相互依存、作用與制約的關系,并形成彼此具有“場”效應的系統。在產品形態設計的造物活動中,環境既包括產品形態與用戶及既有產品形態之間等構成的以產品形態為基點的微觀環境,也涵蓋產品形態與社會、文化、生態等人工與自然環境共同建構的宏觀環境。環境在為產品形態設計提供活動舞臺的同時,也為其活動實施構造了一個具有一定限定、束縛與對抗效力的“場”,并能夠深刻地左右、導向與回饋其形態的內在構成與外在表征,對其使用模式和行為模式亦會產生影響。產品形態設計不是一匹脫韁的野馬,自由馳騁、隨性而為。作為特定系統的構成要素,產品的形態設計可理解為:在一定環境框架下,產品設計師憑借一定的自然與人工材料,在特定設計與生產方法的作用下,給予系統的“新物種”,而這個“新物種”與系統既有要素之間必然存在著“新舊磨合”“水土不服”等矛盾。就如同植物的品種嫁接、人體的器官移植,出現不良與排斥均屬于正常的反應與現象。
首先,就產品形態與用戶構成的微觀環境而言,系統矛盾形成于產品形態設計與人需求的直接對話。基于人因工學,產品形態的體量設定、色彩配置、質地選擇等靜態表征,以及其工作幅度、區域和頻率等動態信息,均“受制”于人的生理、心理特質,并以操作使用的安全、高效與舒適為取向,即“機宜人”,反映的是人與機構成的系統矛盾。如座椅的尺度與人體參數的矛盾,汽車方向盤的材質與操作可靠性的矛盾等。對于微觀環境的另一面,在多數情形下,單一產品是不具有完整效能的,常需與其他產品構成有機的系統,才能為人所需、為人所用。如輪轂與車身、龍頭與面盆等。因此,設計者在創設“新物種”時,必需面對“新物種”與預設環境中“既有物種”間在尺度、色彩、肌理及風格等方面的系統矛盾。如插排的形態設計與各式插頭的匹配矛盾;迷彩服的色、質與特定環境的協調矛盾等。
其次,對于宏觀環境,其中的人工環境特指一定時期狹義的源自產品設計相關理論、思潮形成的本體語境,如通用設計、服務設計等,和廣義上與產品形態存在關聯屬性的拓展語境,如一帶一路、3D打印等;而自然環境則指向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置身于產品周圍,對產品形態具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各種天然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環境。與微觀環境的系統矛盾所不同,產品形態設計與宏觀環境的矛盾不具有直接對抗性,往往呈現出隱性、“綏靖”的特質,主要表現為產品形態設計的學術理念矛盾、語境融合矛盾、生態發展矛盾等。譬如,巴洛克風格辦公室的座椅、燈具及飾品的形態設計會面對奢華、夸張與不規則等特質語境的學理挑戰;汽車公司推出的新車型會遭遇“家族臉”的文化羈絆;各式家居產品的用材亦需在適用與環保間做出取舍決斷。
五、矛盾的認知與化解
英國設計理論家阿切爾曾言:“設計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創造性活動。”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9](P77)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與唯物辯證法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啟示我們:產品形態設計中存在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是相互依存的,各種矛盾的出現恰恰為產品形態設計工作的必要性提供了前提與基礎,為其持續迭代、嬗變注入了源源的動力,并共同作用于產品形態的統一體中。產品形態設計的種種矛盾是客觀與多樣的,且并不以設計者或用戶的一廂情愿而消除。產品形態設計正是在不斷地認知、化解矛盾的常態中砥礪前行。“小矛盾”的彌合達成的是產品形態的遲遲吾行;“大矛盾”的冰釋則昭示產品形態的煥然一新。同時,產品形態設計的矛盾解決,實質是矛盾雙方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轉化。這種轉化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辯證的否定。倘若既有矛盾得到一勞永逸的撫平,而新生矛盾又被淡化或漠視,那么一以貫之的產品形態設計的價值及作用便會受到質疑,成為無病呻吟、矯揉造作的同義語。因此,產品形態設計中矛盾的存在是合理且富于價值的,苛求一件產品形態的設計能夠化解與處理所有矛盾,顯然是不公正、不現實亦是不科學的。對于用戶,審視、挑剔的眼光無可厚非,但更需受益惟謙,有容乃大的心態;對于設計者,左支右絀與畏手畏腳不足取,正視并將矛盾視作設計的機遇與原動力,才是行事之道。
其一,面對矛盾,設計者應構建理性、健康的設計觀。根據國際工業設計聯合會的設計界定,作為產品設計的重要構成與主要工作,產品形態設計的目的在于為產品以及其在整個生命周期中構成的系統建立起多方面的品質,并負有在經濟、社會、環境和倫理層面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的職責與任務。因此,面對諸多矛盾的挑戰,設計者應以關愛之心、責任之心、道德之心及平常之心,積極、客觀、理性和冷靜地面對。在實踐中,設計者應重視、敬畏來自各方的合理、合情矛盾,充分的前期調研、反復的多方論證與審慎的設計實施是必要與必需的。苦心人天不負,相信“實力+心態+執著”能夠換來矛盾的云開霧散。而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道理,亦應是設計者需秉持的樂觀心態與具備的樸素認知;同時,作為矛盾的任意一方,其訴求不免是一隅之說或顧此失彼。設計者要勇于擔當,敢于向種種不良或負面的矛盾“說不”。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設計者對于矛盾的回饋不應是一味、不加辨明地“屈從”,而應是以糾偏導正與補偏救弊的策略與方式予以“回擊”。
其二、產品形態設計所要解決的矛盾不但具有縱向的延續、重生等特質,而且常會呈現出橫向的疊加、多維等復雜性。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矛盾,可謂時刻圍繞、應接不暇。對于如此矛盾,再完美的產品形態設計都不可能成為一舉多得、包羅萬象的“解題神器”,更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左右逢源的“有求必應”。設計工作必須采用科學、有效的應對策略和遵循契合、明達的化解原則,在主次、大小、先后等不同類型矛盾間作出符合設計價值取向的判斷與選擇。明確目標、因地制宜;統籌兼顧、適時突顯。盲動盲從、舍本逐末,只會將貌似沉謀重慮、策無遺算的設計做成“一鍋夾生飯”。例如,根據產品的功能層次理論,工具類產品應把功能實施的效率作為形態設計的要點,電器設備的形態設計需格外關注認知功能的達成,而“Juicy Salif”檸檬榨汁器的設計成功則彰顯了形態的情感功能。
其三,產品形態設計雖總是與各種矛盾相絆相生,但二者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問與答”、“先與后”的主被動關系。設計有來自客觀利益的驅動,也應有來自設計深層價值思考的推進。在產品形態設計的矛盾化解中,設計者可以新的視角與向度界定自身的角色,變后發為引導、化外壓為自發,以主動式設計掌控與引領設計的走勢與矛盾的話語權。依循清華大學方曉風教授的觀點,設計者應當審慎而富有創造性地使用手中的權力,而不應在商業利益的裹挾中放棄權力。產品形態的主動式設計,設計發端于設計者專業的深廣研究、職業的敏銳洞察,并歷經市場的科學預測、機會的前瞻捕捉與設計的精心打造,才有后續的推廣應用。在此過程中,設計者扮演的是產品形態設計的矛盾提出者、化解者與推介者,占據了矛盾的相對主導地位,具有極大的心理優勢和行事空間。當下各個生產廠家、設計團體與個人舉辦的新品發布會便是這一矛盾角色轉換的印證與價值體現。
六、總結
在產品形態的設計與構建中,矛盾的內容、形式會因產品的類型、用途及功效等因素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亦會因設計者、用戶與環境等系統要素的轉變而大相徑庭,但矛盾層出疊現、時時刻刻的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現階段能夠達成的共識是:矛盾是產品形態設計無法回避且不可或缺的,是其工作常態化的基本構成與根本屬性;對于產品形態設計中矛盾的認知與化解,這既是一項具有互動性的理論和實踐工作,也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領域和體系。只有不斷地深入、拓展與豐富相關矛盾的認知,并依托大量的設計實踐檢驗,才能確保矛盾化解的相對科學、全面與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