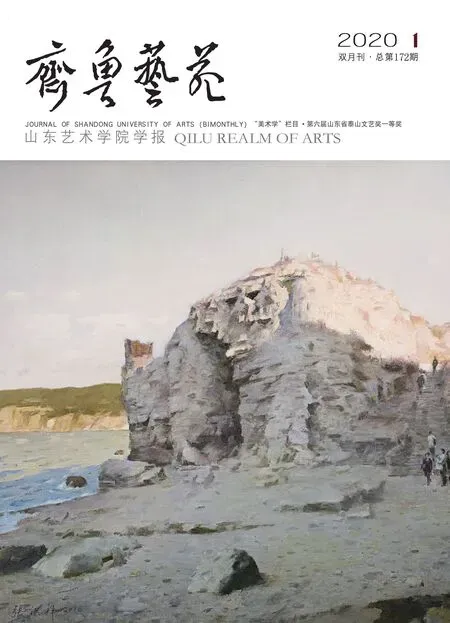徐冰之“圓”
——以跨學科路徑解讀徐冰武漢個展
劉 純
(中南民族大學外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一、前言
1.國內外學術背景
話語分析自上世紀80年代末進入多模態時代:1988年Gunther Kress與Robert Hodge聯合撰寫的《社會符號學》標示著多模態話語時代的到來;1994年Michael O'Toole的《陳列展示藝術之語言》、1996年Gunther Kress及Theo van Leeuwen聯合撰寫的《閱讀圖像:視覺設計語法》及2001年的《多模態話語:現代交流之模態與媒介》均對多模態話語分析的穩步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2008年7月Kay O'Halloran于“第35屆國際系統功能會議”上做出題為《全球多模態:過去、現在與未來研究方向》的發言;同年9月Theo van Leeuwen與Carmen R. Caldas-Coulthard在“第四屆拉丁美洲系統功能會議”上分別發言,呼吁關注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多符號資源、多模態形式及其運用。
多模態話語分析于本世紀初引入我國,李戰子、胡壯麟、張德祿、田海龍等均為代表人物,研究涵蓋多模態話語體系的理論基礎、理論框架、研究方法、模態選擇機制、實證研究等。此外,諸多研究者對文本之外的非語言符號如何表達、生成、促進及構建意義等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
2.現狀及問題
多模態話語分析現以圖像、視頻、聲音、音調及手勢等模態資源為主,集中于商業廣告、政治新聞、電影電視、外交演講、學術研討、課堂教學等領域,鮮少涉及藝術話語的意義生成與解讀。
同時,藝術評論現以哲學思想、美學思想、藝術批評、精神分析理論、心理學理論為主,解讀單件展品涵義,鮮少涉及展品間的關系、展覽與人的關系等。
3.研究目的及意義
鑒于此,該研究擬以跨學科路徑研究藝術話語,以多模態資源為切入點,以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為基礎,對藝術話語意義的生成、傳播及其與人的關系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該研究的意義在于:一、為多模態話語分析提供新的研究領域,拓展其實用價值和發展途徑;二、為藝術評論體系提供新的跨學科研究路徑,為豐富其理論提供新的可能。
二、該研究主要情況介紹
1. 研究對象
以武漢合美術館“徐冰同名個展”為研究對象,包括徐冰近30余年的主要作品及其相關文字資料[1]。展品并非按年份陳列,而是根據場館特點,按主題系列安排。展品、展品主題系列及展覽空間等作為一個整體,成為本研究的多模態資源。
2. 徐冰作品研究之現狀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家領軍人物之一,徐冰每一件作品均引起國際關注與廣泛贊譽,對其作品的相關研究不計其數。以中國知網(CNKI)為例,1988年至今,相關文章共143篇,有效成果131篇(12篇為重復發表),具體包括28篇新聞報道與103篇期刊文章,其中87篇為藝術評論,除3篇分別從哲學、符號學及古文字的視角對徐冰的藝術思想、《地書》符號類別及《天書》的字體等進行探討外,其余均在藝術批評理論的范疇內解讀作品。
可見,徐冰作品研究呈四個特點:一、研究視角仍立足于藝術評論層面;二、研究路徑仍集中于藝術批評理論;三、研究對象仍關注于單件展品涵義或展品的單層面意義;四、研究結果仍涉及藝術內涵與價值等層面。
3.展覽形式與內容
該展被設計為“開篇”“主體”和“結語”三大部分:“開篇”包括“序”“藝術家自述”“策展人語”及“目錄”(地書符號書信墻內容);“主體”包括三個章節,即展品的三大系列——“文字系列”(一樓)、“背后的故事系列”(三樓)、“動物系列”(地下一樓)及其它;“結語”包括“跋”。
從展覽形式上看,該展猶如一本書(如圖1);從展品內容來看,展品系列完整,時間跨度30余年;從文字資料來看,均以第一人稱撰寫,或摘錄于徐冰個人訪談,或來自于徐冰自述,以展品與文字兩種形式,同時展示藝術家的經歷及其思想轉變。因此,該展可視為徐冰的立體“自傳”,觀者可隨意“翻閱”任意“章節”,“閱讀”任意“段落”。
該研究著重分析三大系列中的9幅展品:一樓“文字系列”的《天書》《地書》《英文方塊字》與《鬼打墻》;三樓“背后的故事系列”的《煙草計劃》《何處惹塵埃》與《背后的故事:仙山秋逸圖》;地下一樓“動物系列”的《蜻蜓之眼》與《鳳凰》。

圖1 徐冰同名個展的形式與內容
4.研究視角及理論基礎
每個展廳視為自傳的“每一頁”,展品及文字資料即“每頁的圖像與文字”,展廳與展品整體形成“每頁圖文關系”,生成意義。“每頁圖文關系”連續相接,傳達思想,體現風格。具體來說,“單件展品含義”為本研究的微觀層面,“展品間的關系與意義”形成中觀層面,而“展品系列間、展覽與人之間的關系與意義”則為宏觀層面(如圖2)。

圖2 研究視角
因此,該研究在系統功能語法的基礎上,以多模態話語分析為視角,作以下三層面分析:以視覺語法理論(Kress與van Leeuwen)為框架,在微觀層面考察“單幅圖像圖文關系”,即單件展品含義;以視覺敘事理論(Painter,Martin與Unsworth)為框架,在中觀層面考察“連續圖像圖文關系”,即展品間的關系與意義;最后,在宏觀層面探討展品系列間、展覽與人之間的關系及意義。
三、三層面多模態話語分析
1.微觀層面分析
(1)視覺語法理論
Halliday認為“語言是種社會符號,是‘意義潛勢’系統;語言的語法不是一套用來參考的規則,而是制造意義的資源”[2],即語言只是意義系統中的一種符號,可通過語法產生意義,而其它非語言因素的符號性也具備這種潛勢。其語言三大元功能雖基于對語言的研究,但并不意味著僅局限于語言。
基于此,Kress與van Leeuwen構建了視覺語法理論框架(見表1),使Halliday的語言元功能理論在非語言符號的多模態領域中得以傳承與發展。
表1 語言元功能與視覺語法理論框架對比

張敬源教授指出,上述視覺語法理論框架中“再現意義”的“敘述再現”之各細分過程間不具互補性;“互動意義”中“接觸”的“提供”與“索取”不明確,“情態”部分不系統;“構圖意義”的“顯著性”忽略符號本身的社會屬性。根據其補充完善方案,最終形成調整后的視覺語法理論框架(見表2)。
表2 調整后的視覺語法理論框架

(2)單件展品的含義解讀
三大系列9幅展品的視覺語法資源分布情況見表3:
表3 三大系列9幅展品的視覺語法資源分布情況

根據上述資源分布情況,“文字系列”4件展品的視覺語法分析如下:
A.《天書》以中國活字印刷術大量印刷無意義的宋體字,懸掛于展廳上方及四周墻壁,并制成古線書攤鋪于展廳地面(見圖3)。
再現意義方面,象征過程:橫撇豎捺象征中國文化根基,筆墨紙硯、活版印刷、宋體線書、篆刻工具均象征中國文字神圣莊嚴;分析過程:中國文字雖以古老形式重組,卻無法識別,系“偽文字”;心理過程:文字資料中以第一人稱敘述創作初衷,娓娓道來。
互動意義方面,以間接接觸客觀呈現“偽文字”特征;黑白基調,色彩暗,不飽和,但展廳照明亮,深度深,再現“偽文字”的制作工序及細節;圍擋線保持中景,與古書保持距離,即保持敬畏;仰視(懸幅)表現對中國文字/文化的崇敬,俯視(古書紙硯)表現對文字產生及傳播的了解與自信,平視(文字墻)表現以平和之心辨識文字。

圖3 《天書》展廳
構圖意義方面,古書與懸幅占據前景與中心,強化對中國文化的尊崇與了解;文字墻及篆刻工具處于背景與邊緣,弱化識讀障礙。
總之,當我們以崇敬心態觀看中國文字/文化,以慣常方式閱讀文字時,卻發現這些具備漢字外形結構的文字其實根本無法識別。于是,神圣與平凡、熟悉與陌生、形式與意義、觀看與閱讀、理解與阻滯之間的矛盾呼之欲出,不僅引發文字理解層面的反思,還有文化心理層面的反思。
B.《地書》搜集并整理社會生活中的最簡符號或標示,進而以此為語言描述一切人類活動。展覽包括地書工作室和地書書信墻(如圖4)。

圖4 《地書》展廳
再現意義方面,分析過程:展品部分展示了符號搜集過程及其實際運用;心理過程:文字資料以第一人稱反映創作初衷。兩者結合,讓觀者既了解地書的形成與特點,又主動解讀其含義。
互動意義方面,以間接接觸、自然主義編碼呈現工作室場景,以間接接觸、科學技術性編碼向觀者表達問候與建議;兩部分展品均色彩不飽和,色調不協調,但工作室照明亮,深度淺,旨在將搜集過程細節化,予以強調,而書信墻所在的走廊照明亮,深度深,旨在將書信與走廊融為一體,使其語境化,弱化其主觀態度;兩部分均保持近景、平視或俯視,意在與觀者平等交流,使其融入其中。
構圖意義方面,兩部分展品均置于背景及邊緣,但因前景及中心并無它物,且背景比重大,顏色明顯,故仍占主要地位,委婉表達平等交流之意。
總之,地書工作室完整呈現藝術家們的工作場景與狀態,使觀者了解地書來源、搜集過程與意義生成規律后,進一步對書信墻的內容保持興趣。同時,熱情展示、親切敘述、熱切希望與委婉意愿在觀展過程中一覽無遺。
C.《英文方塊字》用形似26個英文字母的中文筆劃重新組合,形成外觀似中文,內在為英文的新型字體,即英文方塊字。展覽包括展品廳和學習教室(見圖5)。

圖5 《英文方塊字》展廳
再現意義方面,分析過程:各類相關展品、照片及學習教室分別展示了英文方塊字的藝術成果及習得過程;象征過程:《蘭亭序》、 LV定制硬箱、白瓷碗碟套裝與歌詞書等象征文字/文化的中西融合;心理過程:文字資料以第一人稱釋惑。
互動意義方面,展品廳以間接接觸、自然主義編碼客觀展示展品與照片,以玻璃罩保持中景,即冷靜遠觀的社會距離;學習教室以直接接觸、自然主義編碼主動邀請觀者參與習得過程,以近景拉近距離,以平視與俯視表達謙遜之態;展品區色彩飽和,色調協調,照明亮,深度深,將白瓷碗碟套裝等展品語境化的同時,將LV定制硬箱和《蘭亭序》細節化,突顯“中西融合”的主題;練習教室色調單一,黑白分明,展廳亮,深度淺,將黑板與四周墻上的意義生成規律語境化,將課桌椅細節化,弱化語言規律,突出語言習得。
構圖意義方面,LV定制硬箱和《蘭亭序》置于展廳的前景與中心,其它展品與文字處于背景與邊緣;課桌椅置于學習教室的前景與中心,而文字轉化規律置于背景與邊緣。
總之,英文方塊字保留漢字的象形結構與英文的音意系統。展廳的LV定制硬箱和《蘭亭序》,學習教室的課座椅,均強調“中西融合”的主題以及邀請觀者(不論國籍)主動參與習得的熱切希望。當觀者主動參與習得,其習得行為本身也成為展品的一部分,即“中西融合”除了上述文字/文化的融合,還包括行為的融合。
D.《鬼打墻》拓印長城城墻,并鋪于室內墻壁與地面,輔以沙堆、竹架和樓梯(見圖6)。
再現意義方面,分類過程:長城拓品雄偉、龐然;思維過程:文字資料以第一人稱反映創作思維過程。
互動意義方面,以間接接觸、自然主義編碼客觀反映長城的巨大恢宏;以平視視角與其保持平等心理地位;色調灰暗,局部照亮,凸顯肅穆壓抑;展廳深度淺且保持近景,形成視覺局促與心理壓迫。

圖6 《鬼打墻》展廳
構圖意義方面,展品比重大,置于前景與中心,無背景與邊緣,凸顯龐大與壓抑間的對抗,即視覺與心理的對抗。
總之,展廳狹小局促,長城拓品龐然嚴肅,咄咄逼人。雖以樓梯和竹架與之保持平視,但視覺上的壓迫感使心理上的壓抑感無所遁形。這與平視的蘊意貌似矛盾,但結合當時國內主流評論對徐冰藝術風格的批判[4],不難發現,這正是對他當時身處主流輿論而必須面對接受現實的隱喻。
上述分析綜合呈現如表4:
表4 “文字系列”的視覺語法分析

限于篇幅,“背后的故事系列”與“動物系列”的視覺語法分析綜合呈現如下:
表5 “背后的故事系列” 的視覺語法分析

表6 “動物系列”的視覺語法分析

(3)本節小結
本節以視覺語法理論為框架,解讀展單件展品的含義:
“文字系列”中,《天書》同時表現神圣與平凡、熟悉與陌生、形式與內容、觀看與閱讀、理解與阻滯等矛盾,引發文字理解與文化心理兩個層面的反思;《地書》全景展示工作室,并以地書符號信件表達問候并提出觀展建議,真誠熱情,委婉低調;《英文方塊字》結合中文象形結構與英文的音意系統,并邀請觀者主動參與習得,同時體現文字/文化與行動兩層面的中西融合;《鬼打墻》以拓印方式將長城引入室內,引起視覺緊張與心理壓迫,反映徐冰當時的思想狀態。
“背后的故事系列”中,《煙草計劃》以煙草變形后的各類物品隱喻煙草與人的關系;《何處惹塵埃》將911的灰塵沉降為一句中國禪語,引發對安全、社會狀態的反思;《背后的故事:仙山秋逸圖》畫作背后是廢棄物,凸顯藝術與自然的關系;
“動物系列”中,《蜻蜓之眼》將公共攝像頭的視頻信息人為剪輯成與影像本身毫無關系的故事群,以此探討內容與形式、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矛盾;《鳳凰》分別以視頻、文字資料和模型展示設計、原材料及制作過程,在華麗與卑微、尊貴與艱辛之間形成強烈對比。
總之,單件展品含義雖不盡相同,但均以親切積極的姿態拉近與觀者的距離,歡迎并鼓勵觀者主動參與、互動、交流和思考,無不體現著藝術與觀眾的溝通,即徐冰一直秉持的“藝術為人民”[5]的創作思想。
2.中觀層面分析
(1)視覺敘事理論
如果說Kress和van Leeuwen的視覺語法理論確立了多模態話語分析的學科地位, 那么Clare Painter, Jim Martin與Len Unsworth潛心十年的研究成果《解讀視覺敘事》(2013)的視覺敘事理論則標志著基于語料分析對視覺語法理論的補充、修正與發展。
經馮德正教授的簡化、修改與補充,視覺敘事理論于2015年進入我國研究者的視野:一方面,其研究對象超越單幅圖像的意義生成,轉而關注多幅圖像合成的復雜視覺敘事;另一方面,其理論框架對視覺語法理論中頗有爭議之處進行大幅修改,且就“情感表征”、“事件關系”等方面進行有益補充(見表7)。
表7 視覺敘事理論框架

(2)展品間的圖文關系及意義
三大系列9幅展品的視覺敘事資源分布情況見表8:
表8 三大系列9幅展品的視覺敘事資源分布情況

根據上述資源分布情況,“文字系列”4件展品的視覺敘事分析如下:
A.《天書》
概念意義方面,轉喻表征凸顯“偽文字”僅具漢字象形結構,不具意義;懸幅、文字墻、古書與篆刻工具屬同時發生的事件展開關系,在相同背景下,以不同視角投射想象的事件關系:“偽文字”高高在上,一本正經,實則虛有其表,毫無作用。
人際意義方面,旁觀型互動、引發性主觀視角聚焦荒謬與矛盾無處不在;鑒賞類情感介入反思文字/文化本質;亮色度、暖色調與高自然度激活氛圍,使觀者主動融入、積極思考。

圖7 《天書》展品特征
組篇意義方面,文字與展品不對稱,屬連接型擴展;展品為主,文字為輔,意義連接,但位置相隔,以話語投射補充創作靈感及初衷。
總之,天書具漢字象形結構,有其形卻無其實,無人能識卻煞有介事。這種荒謬與矛盾反映人對文化本質的警覺與反思(如圖7)。
B.《地書》
概念意義方面,完整表征再現地書工作室與書信墻;兩者屬先后發生的事件展開關系,在無背景條件下投射真實的事件關系,即地書人人識讀,源于生活。
人際意義方面,旁觀型互動、直示性主觀視角聚焦地書的符號性、文化性、敘事性和實用性等;個體類情感介入熱切希望觀者了解并接受地書;亮色度、暖色調和高自然度激活氛圍,使觀者積極融入,保持對話。

圖8 《地書》展品特征
組篇意義方面,地書工作室中的展品與文字不對稱,屬連接性擴展,內容連接,但位置分隔,展品為主,話語投射補充“普天同文”[6]的理想;地書書信墻屬包含型擴展,文字既是展品形式,也是展品內容,兩者融為一體,互為彼此。
總之,地書雖無字形規律,無讀音,卻有意義,人人能懂,平易近人,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如圖8)。
C.《英文方塊字》
概念意義方面,完整表征既展示各式制品——英文方塊字融入社會的程度,又展示學習教室——習得過程;兩者屬先后發生的事件展開關系,在不同背景下投射想象的事件關系:英文方塊字形為中文,神為英文,具使用價值與文化價值。
人際意義方面,旁觀型互動、客觀視角聚焦英文方塊字的融合性與矛盾性;鑒賞類情感介入反映“阻礙—習得—理解”過程;亮色度、暖色調與高自然度激活氛圍使觀者身臨其境,領略中西融合的樂趣。
組篇意義方面,展品與文字不對稱,屬連接型擴展,內容相連,但位置分隔;展品為主,以話語投射補充展品的接受度及創作心態。
總之,英文方塊字結合了漢字象形結構與英文音意系統;“阻礙—習得—理解”的文字習得過程,實為“不解—認知—接受”的文化心理過程,最終引起對文化差異及文化融合的態度之反思(如圖9)。
D.《鬼打墻》

圖9 《英文方塊字》展品特征
概念意義方面,轉喻表征反映長城的真實、龐大與權威之感;城墻、沙堆、樓梯與竹臺屬同時發生的事件展開關系,在相同背景與視角下投射真實的事件關系:室外的長城置于室內,令人緊張、局促、壓迫。
人際意義方面,旁觀型互動、引發性主觀視角聚焦狹小空間內的長城,龐然霸道,威嚴肅穆;個體類情感介入表現緊張之感;展廳為黑白調,未激活氛圍,冷靜旁觀,肅然起敬的同時,又窒息無力。

圖10 《鬼打墻》展品特征
組篇意義方面,文字與展品不對稱,既有連接性擴展,又有包含性擴展,內容連接,但位置分隔,展品為主,以話語投射補充創作前語境、,創作時心態及創作后評論。
總之,龐大長城與狹小空間的對抗,隱喻著長城威嚴霸道與觀者緊張不適的對抗、長城壓迫之勢與觀者冷靜之態的對抗、當時國內主流評論與徐冰面對輿論的對抗(如圖10)。
上述視覺敘事分析過程綜合呈現于表9:
限于篇幅,“背后的故事系列”與“動物系列”的視覺敘事分析綜合呈現為表10和表11。
(3)本節小結
A.除《鬼打墻》外,“文字系列”的其它三件展品均以中國文字為基礎元素,經過拆解、變形或重構,形成新的文字,通過阻礙理解與表達,使思想回到原點,重新思考:
《天書》在乎文字的象形結構,“偽文字”虛有其表,無人認識,反映的正是對文化本質的警覺與反思。相反,《地書》既無讀音,又無字體結構規律,僅有表意功能,人人可識;它并非像天書那樣生造,而是來自生活,表達生活,體現著“普天同文”的理想。兩者共通之處在于均忽略觀者的教育背景與文化程度,即展品面前“人人平等”的狀態(一個無人能識,一個人人能識)。
《英文方塊字》在漢字象形結構及阻礙理解等方面與《天書》類似,但它有形有音有義,介于《天書》與《地書》之間。
《鬼打墻》對比龐然與拘謹、嚴肅與壓迫,旨在凸顯緊張、不適與矛盾,隱喻當時國內主流評論與徐冰選擇面對現實時的狀況。因此,該展品可視為該系列的總結。
表9 “文字系列”的視覺敘事分析

表10 “背后的故事系列”的視覺敘事分析

綜上所述,“文字系列”4件展品之間的關系與意義見圖11。
B.“背后的故事系列”均以中國文化為內在思想,以生活普通物品為原材料,將之變形為另一種形式,進而引發對人、生活、社會的關注與思考(如圖12):
《煙草計劃》中普通物品變形為其它普通物品,實體到實體的變形,思考人、煙草、生活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何處惹塵埃》中特殊廢棄物變形為特殊話語,實體到虛體的變形,反映人、安全與社會共存之間的關系;《背后的故事:仙山秋逸圖》中普通廢棄物變形為特殊物品,實體到實體的變形,探討人、藝術與社會自然之間的關系。因此,三者本質一致,相互互補(如圖12)。
表11 “動物系列”的視覺敘事分析


圖11“文字系列”展品的關系及意義

圖12 “背后的故事系列”展品關系與意義
C.“動物系列”均以社會真實碎片為原材料(一個是影像碎片,一個是實體碎片),將之重組后呈現新的藝術形式(一個是影像重組,一個是實體重組),通過對比重組前后的狀態,反映社會的真實狀態。
《蜻蜓之眼》將公共攝像頭視頻人為編撰剪輯成故事群來反映社會,即真實通過虛構來反映真實;《鳳凰》將廢棄物通過艱辛勞動組裝成藝術,即卑微通過卑微來達到尊貴。因此,兩者目標一致,路徑不同。前者反映社會語境本身,而后者結合宏觀社會語境,其涵義更為深刻,即“平凡勞動者通過平凡的勞動創造著偉大的社會與時代,從而體現勞動的價值與尊嚴”(如圖13)。

圖13 “動物系列”展品的意義及關系
3.宏觀層面分析
藝術手法與目標方面,三大系列自成體系,卻又彼此相承:均以中國文化為思維基礎,以生活元素的拆解、變形與重組為藝術技巧,以阻礙理解、制造矛盾、打破思維為藝術手段,達到探討文化、生活與社會本質之目的。
展覽與觀者之關系方面,三大系列均通過展品布置、空間安排與文字資料的情態特征,熱情邀請觀者全情融入、參與互動,進而保持對話、交流思想,最終走近藝術、走進藝術,即徐冰“藝術為人民”的思想。
展覽與徐冰之關系方面,三大系列依次關注語言文字文化、人與社會的關系、社會狀態及問題。可見,徐冰的作品越來越接近社會問題,越來越具有社會性。藝術的轉變體現的正是思想的轉變,徐冰指出:“(藝術)必須要跟這個時代的問題發生關系”,“你生活在哪兒就面對哪兒的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7]
綜上所述,單件展品雖各有意義,但并非孤立無關,而是相互連接、相互補充、相互解釋;展品系列間也如出一轍,雖各有主題,但相互照應,相互承接,互為因果。如同若干個大大小小的圓,彼此連接,彼此包含,首尾呼應。“展品的圓”體現的是“意義的圓”,最終體現的是“思想的圓”(如圖14)。正如徐冰專訪中提及的:“把所有的作品放在一塊兒看的時候,我發現其實我建立了一個閉合的圓,所有內容都是能自圓其說的......這個圓里不同的作品之間相互注釋、相互幫襯,讓我看清楚自己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對什么感興趣。”[8]

圖14 徐冰之圓
四、結語
針對當今多模態話語分析模態資源有限,以及藝術評論理論范式有限等現狀,本文從跨學科路徑出發,在多模態話語分析框架下對徐冰同名個展的視覺藝術話語進行研究。
通過考察展覽內容與格局布置,將該展視為徐冰的立體自傳。首先,在微觀層面上以視覺語法理論框架詮釋單件展品含義;其次,在中觀層面上以視覺敘事理論框架分析展品間的關系與意義;最后,在宏觀層面上分析展品系列間、展覽與人之間的深層關系和思想內核。
該研究為多模態話語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領域,也為藝術評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隨著社會與語言的快速發展,多模態話語分析領域不斷拓展,文藝評論范式也不斷豐富,跨學科研究極可能產生新的理論,如多模態藝術話語分析等,更科學、更全面、更有針對性地解讀藝術話語,這也是本研究今后將繼續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