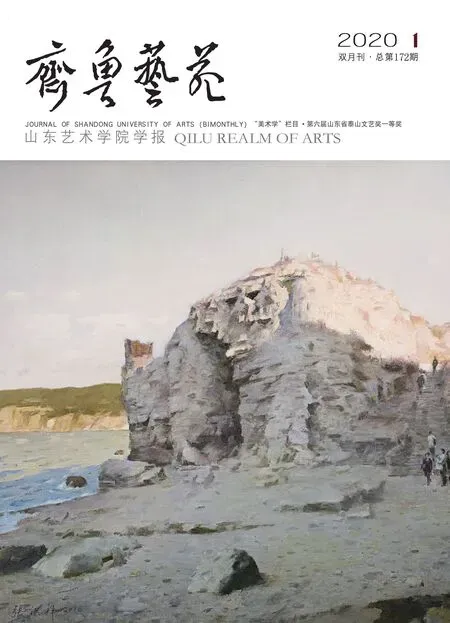韓國的電影審查與分級制度研究
孫 晴
(山東藝術學院藝術管理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韓國電影憑借自身較高的完成度、豐富多樣的類型、富有魅力的演員以及能夠引起東方觀眾共鳴的題材席卷亞洲甚至全球,為人們所稱道。而在80年代末期,韓國電影還僅僅是軍人政府換取政治、經濟利益的工具,在好萊塢電影、香港電影的沖擊下無法自處。韓國電影之所以能在短短十余年的時間內迅速崛起,與20世紀90年代電影政策的變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中,電影審查的廢除與電影分級制度的確立可以說是韓國電影迅速崛起的關鍵因素。由于政治制度、社會背景與民主化程度的不同,韓國電影審查在各政權時期的主要內容都有所不同。一般來講,民主化越徹底,審查制度越會由國家主導的強制性規則向保護個人利益與產業利益的方向轉變。韓國學者樸圣鉉在探討電影審查對韓國電影的影響時曾提到,“審查,在朝鮮電影的濫觴期,是阻礙電影發展的最大障礙,可以說,不討論這種審查帶來的影響,也就無以描摹韓國電影的歷史”[1](P80-89)。且在特定意義上說,分級制又是電影審查制的延續和變型,是電影審查的現代形態[2](P44-47)。因此對韓國的電影審查與分級制度進行歷史性的梳理與分析,有利于進一步了解韓國電影成功的原因并深化對韓國電影文化與政治之間關系的認識。
一、韓國電影審查的歷史語境
相比在西方國家中作為自發接受的產物,電影是通過一種現代文化(殖民式地)移植方式傳入韓國的[3](P5)。據相關史料考證,1897年10月19日《倫敦時報》的一則報道中寫道,英國人阿斯頓·豪斯(Astor House)和朝鮮煙草株式會社(The Korean Tobacco Company)共同購買了法國百代公司的紀錄短片,在忠武路北村租用了一所破舊的棚子3天,利用瓦斯燈放映電影[4](P1)。這是電影在朝鮮半島公開放映的最早記錄。電影傳入之初,作為當時的政治勢力,朝鮮總督府對這一新興媒體的管理,主要集中在放映場所的衛生與公共安全的維護上,管理主體為警察,管理規則以《保安法》和各地區理事廳的《理事廳令》為依據,并沒有對電影內容上的要求。所以這一時期對電影的管理僅限于放映場所的治安管理,并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審查。
真正開始對電影內容進行審查是在日本殖民時期。1919年10月27日,在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的第九年,第一部由韓國人制作的活動寫真連鎖劇(1)電影傳入韓國之后,韓國最初把“電影”翻譯為“活動寫真”(Moving Pictures,Motion Pictures),繼而又轉譯為“映畫”(Film)。而活動寫真連鎖劇這一名詞源自日本,不過是在舞臺上演出戲劇時,插入電影畫面,作為背景交代或者串場過場使用,并不是一部完整的電影。《義理的仇討》公開上映。雖然這部作品僅僅是插入了1000英尺左右膠片拍攝的外景,但是民眾對民族電影意識的覺醒,使殖民者認識到限制電影內容,加強思想管制的必要性。概括來講,日本殖民時期的電影審查,主要是通過《興行與興行場(2)“興行”在韓語中是“公演”的意思,“興行場”則是公演場所的意思。取締規則》《活動寫真和電影檢閱規則》《朝鮮映畫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得以實施。1922年,朝鮮總督府制定《興行與興行場取締規則》,該法規規定活動寫真、話劇以及音樂劇等所有公演物在公映之前都要接受劇本的審查,“凡劇本中有通奸、接吻等有損風紀的內容,會造成暴力、犯罪等社會問題的內容,以及煽動獨立運動的內容,均禁止上映”[5](P466)。此時,統治勢力對電影的管制依舊比較寬松,主要還是通過警察的現場臨檢行為進行管理。然而在1926年,由羅云奎撰寫、編劇、導演并主演的電影《阿里郎》上映,影片蘊含民族抵抗意味,用一種當時難以想象的電影蒙太奇技術表現出來,吸引了無數觀眾[6](P79),造成了強烈的反響。在《阿里郎》的影響下,更多具有民族反抗思想,體現殖民統治下民眾悲慘生活的影片被制作出來。這一現象導致朝鮮總督府開始對電影進行專門化的管理,于1926年7月5日制定了電影的專門化管理法規——《活動寫真與電影檢閱規則》并開始在全國范圍施行,電影審查的標準實現了統一化。法規中嚴苛的電影審查標準,使電影的主題與內容一旦觸及政治、民族的要素就會遭到強行刪減。許多電影被禁止或是在大量刪減之后才得以上映。
1938年,日本殖民統治者由于中日戰爭的經濟政治壓力,開始對朝鮮半島實施全面強制性的統治,而其電影審查管理也變得更加嚴苛。韓國電影也因此陷入了“史上飽經磨難的最黑暗的時期”[7](P141),成為宣傳殖民意識形態、鼓吹戰爭的工具。1940年8月,朝鮮總督府制定《朝鮮映畫令》,規定所有電影的制作、上映和宣傳必須獲得朝鮮總督的許可,從事有關電影行業的工作都應事先向總督府注冊。電影創作必須通過劇本的事前審查與成片的事后審查,以妨礙戰爭執行為目的,“有褻瀆皇室尊嚴或者損害帝國威信”的電影或美化戰爭大國(如美國等)的電影都屬于主要審查對象。戰時動員體制狀態下的殖民政府試圖通過《朝鮮映畫令》控制電影劇本、制作、發行的整個領域。這一時期,迫于殖民政府的壓迫,大量電影公司倒閉,一部分電影人被吸納進入殖民政府創辦的“御用團體”朝鮮映畫制作株式會社,以協同日本殖民者制作了大量軍國主義御用宣傳片,另一部分不愿意妥協的電影人被迫離開電影界,電影徹底失去了藝術性和娛樂性,淪為殖民者宣傳戰爭與殖民思想的工具。
隨著電影對大眾的影響力日趨增強,日本殖民時期的電影審查從限制禁止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性內容轉向利用電影宣傳戰爭和殖民思想。可以說,在日本殖民時期,電影被看作是壓制人民獨立思想,傳播帝國主義文化的意識形態工具,其藝術性被政治性意圖淹沒。電影審查作為殖民政府的文化統治策略,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作為歷史語境的日本殖民時期對解放后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電影的管理也是如此。電影審查作為文化統治手段在這一時期被認為是必然之物,以至于解放后韓國政府依舊模仿、摘抄、復制殖民時期的電影法規對電影進行管制。例如樸正熙政府時期制定的韓國第一部電影基本法《電影法》就與日本殖民時期《朝鮮映畫令》在內容上有著驚人的相似。從這一意義上,韓國的電影審查制度可以看作是殖民時代電影審查的延伸。
二、各政權時期下的電影審查
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以后,經歷了朝鮮半島南北分裂與朝鮮戰爭的混亂時期。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在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南地區成立了大韓民國政府。從韓國的執政勢力的分期來看,電影審查的歷史主要分為李承晚政權時期、樸正熙政權時期、全斗煥政權時期和盧泰愚政權時期四個階段。雖然各個時期的電影審查會根據政權當局對于電影的認識或審查制度給予社會結構帶來的諸多影響而有所不同,但是其根本意圖都是壓抑表達自由、維護統治或宣傳意識形態。可以說,在審查的籠罩下,韓國電影一直深受政治和社會環境影響,從未有過自由寬松的創作氛圍,在任何時候,都處于壓倒文本的語境重壓下[8](P274)。
(一)李承晚政權時期(1948-1960)
李承晚政權時期由于政治體制、法律和社會制度等各方面都處于尚未完備的狀態,因此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完全是依靠美國援助支撐,導致這一時期的韓國政府對美國具有很強的附屬性。作為新生國家的第一代政府,李承晚政府不但沿用了美國駐軍時期的許多政策,還通過一系列法令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在當時韓朝雙邊意識形態敵對的情況下,電影成為宣傳反共思想、維護獨裁統治的工具。
李承晚上臺后,以大韓民國政府名義施行的第一項電影政策就是對當時韓國國內制作、國外進口以及從軍政廳過渡到公報處的所有電影進行再審查。這一政策名義上是為了審查趁行政混亂時期非法上映的走私電影,藝術性喪失的電影以及膠片老化的電影,實際上是對電影內容進行限制,以達到思想上管制的目的。電影審查機構不是主管藝術、文化、教育的文教部,而是主管宣傳、信息、輿論的公報處,也表明了電影在新生國家誕生時期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宣教的工具而存在的。1955年,審查機構轉移至文教部,但是不久后又重新移交至公報處,行政歸屬混亂,電影的審查沒有實現體系化。這時期電影審查的標準是1957年7月21日文教部公示的《公演物細則》。此細則作用于電影、話劇、舞蹈等所有公演物,并通過國家法律、宗教教育、風俗、性關系、暴力性和其他等六大領域對公演物進行限制或禁止。該細則將公演物可表現的范圍過分地縮小限制的規約,遭到了強烈而廣泛的反對,但是審查機關內部仍舊將此作為審查標準繼續施行。
(二)樸正熙政權時期(1962-1979)
1961年5月16日,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軍部精英開始取代保守的文人政客擁有主導國家的權力,韓國正式進入“軍事政權”時期。在軍事時期,殖民時期以管制為主的電影政策依舊沒有被廢除,以至于在許多條款中依舊能看到殖民時期的影子。因此,軍事政權時期依舊將電影看作維護統治、宣傳意識形態的工具,將電影審查作為壓制民主思想、言論自由的手段,以達到文化控制的政治意圖。
樸正熙政權時期電影審查的最大特征是審查的合法化與制度化。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電影業的控制,樸正熙政府于1962年1月20日制定了韓國第一部電影基本法《電影法》,電影審查以“上映許可制”和“上映許可審查基準條款”的名目被書于其中。同年第五次憲法修訂中,電影審查又以保障公共道德和社會倫理為借口,作為合憲行為被法律明文規定。樸正熙通過電影審查的合憲性使政府壓抑公民表達自由的行為合法化。隨著審查的日漸法制化,審查標準與程序也愈加嚴苛。1966年,在《電影法》第二次修訂中,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作為電影劇本審查的主體被設立,與公報處一起對電影開始施行“制作前劇本審查和制作后成片審查的“雙重審查制度”。具體審查流程是電影業者向公報處提出制作申請之前必須先要經過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的劇本審查,劇本審查通過之后,才能向公報處提交制作申請,電影制作完成之后公映之前又必須接受公報處的成片審查。特別是在1971年進入“維新體制”(3)維新體制是韓國軍人集團面對工人階級斗爭不斷高漲、知識階層自主意識漸趨增強以及在野政治勢力日益壯大等社會問題所采取的一種適應性統治方式,是韓國官僚權威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實質上是樸正熙政府為了維持統治權力,巧妙利用偽飾手段實行獨裁政治,操控意識形態話語的變通形式。之后,政府每年都會頒布電影時策,以強化對電影的管制。1972年,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對電影劇本的修改、打回比率已經達到58%,到1975年,80%的劇本都需要進行修改和刪減[9](P489)。這意味著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已經超出了正常權利,屬于凌駕于法律之上的行為,公民自由表達的基本權利變得毫無意義。
由于嚴苛的電影審查制度,70年代的韓國電影又一次跌入低谷,而受思想政策限制較小的“情色電影”被大量制作出來。鑒于“情色電影”對青少年的不良影響,樸正熙政府在1979年開始對電影進行分級。電影在上映之前被分為未成年者可觀看、國民學生不可觀看、青少年不可觀看三個等級。這是韓國電影分級制的最初形態。
(三)全斗煥政權時期(1980-1988)
20世紀80年代,維新體制崩潰后,全斗煥政府意識到軍事政權的不正當性與道德上的薄弱性,開始采取暴力與綏靖并存的統治政策。電影政策上主要表現為1984年《電影法》的第五次修訂。當時面臨美國要求全面開放市場的壓力,全斗煥政府制定了電影公司注冊制取代許可制,設立獨立電影制作制度以及制作與發行分離等一系列措施,韓國電影制作開始自由化。在電影審查上,事前“審議制”代替“審查”制度,審查業務由政府文化公報部轉移至公演倫理委員會。但是這些規則上的緩和僅僅停留于表面,政府對電影內容上的管制絲毫沒有松懈。“審查”制度被事前“審議制”所代替,只是為了反映憲法第八次修訂中“審查禁止”的規定,將審查制度在名稱上進行改變而符合憲法。事前審議制的主體、標準和程序等與之前的審查制度幾乎完全相同。韓國公演倫理委員會作為電影審查的主體,名為民間機構,實際上依舊受政府控制。唯一有所改變的是對電影在性表現方面的進一步放寬,導致以《愛麻夫人》為代表的韓國“情色電影”的泛濫。但是,通過電影審查,觸及政治性、社會性內容以及挑戰權威秩序的影片仍會受到徹底壓制,從這一點上來看,全斗煥政府時期的電影審查制度是維新時期電影審查制度的延續。
(四)盧泰愚政權時期(1988-1992)
盧泰愚政府上臺的80年末90年代初,在“民主化”要求日漸高漲的氛圍下,對電影的管制有所緩和,但是緩和的范圍主要是對非建交國家電影進口限制的放寬。在本土電影的審查標準上卻絲毫沒有放松。1989年8月19日,政府以保護青少年免受性和暴力電影傷害為名對《電影法》進行第六次修訂,追加了電影審查標準的內容,對“意圖誹謗、否定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的內容,美化、宣傳、煽動左翼思想活動的內容以及歪曲客觀事實、敵對友邦國家的內容”[10](P501)進行嚴格禁止。這次修訂與其說是為了限制色情暴力電影,不如說是意圖加強對電影內容的控制。嚴苛的電影審查實際上一直持續到90年代。但不容忽視的是,這一時期的韓國政治開始急劇變動,經濟的快速發展使社會各階層的自主意識普遍提高,民主運動和工農運動空前高漲。通過1987年6月“民主化”運動(4)“六月抗爭”,1987年6月9日,參加民主改憲運動游行的韓國延世大學學生李韓烈,被警方的催淚彈擊中頭部不治身亡。這一事件引發了韓國民主運動的高潮,韓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游行示威,民主改憲運動發展為全體國民參加的全民運動,史稱“六月抗爭”。在全社會強大的壓力下,6月29日,盧泰愚發表了“6.29宣言”,民主改憲運動取得了全面勝利。的勝利,韓國民眾對于自由和權利的意識增強,也為韓國電影人廢除電影審查,爭取表達自由提供了契機。
三、電影審查的廢除及其意義
20世紀80年代后期,韓國社會要求民主化的呼聲愈加高漲,這一民主化熱潮也波及至電影界,具體表現為電影人要求廢除電影審查制度,呼吁創作與表達的自由權力。1993年,金泳三政府的上臺結束了韓國長達30余年的軍人獨裁統治,迎來了文人民主政治的新時代。1995年12月30日,韓國政府廢除了建國后就被設立的以“管制”為中心的《電影法》,制定了以“振興”為要旨的《電影振興法》,開始免除對短篇電影、小型電影以及國內外電影節上映電影的審查,盡管大部分韓國電影和進口電影依然要接受審查,但這一措施已經體現了隨著民主化進程的加快,韓國電影人對于電影業的改革建議與要求正逐漸被政府接納的趨勢。
引發韓國電影審查制度得以根本廢除的關鍵事件是憲法裁判所對電影審查制度的違憲判決。1996年,韓國獨立電影《啊!夢之國》和《打開緊閉的校門》因違反公演倫理委員會的事前審議制度,未經審查就公開上映,其主要負責人均被強制拘留。韓國電影人以此為契機,發起了廢除電影審查的運動。1996年10月4日,憲法裁判所對這一案件進行審理,認為“電影作為思想和觀點的表現手段,依據憲法中的表達自由應得到保障”,“公演倫理委員會禁止未經上映審查的影片,并對違犯者處于刑事處罰的行為是違背憲法精神的”[11](P32-54),對公演倫理委員會的事前審議制下達了違憲判決。通過這次事件,電影表達自由獲得法律保護,束縛電影創作自由的審查制度終于失去了法律效力,審查合法化被徹底否定。1997年4月10日,依據電影審查的違憲判決,《電影振興法》進行了第一次修訂,這也標志著長期束縛韓國電影發展的審查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被明文廢止,電影分級制度也在此時被正式引入實施。
從韓國的發展經驗來看,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導型市場經濟一直是韓國所堅持的獨特“東亞模式”。因此,文化產業作為核心競爭力被引入市場,政府的政策發揮了主要作用。一直以來,韓國電影事業發展都深受政府政策影響。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審查制度,體現了政府把電影長期作為思想管制或意識形態宣傳工具,而忽視電影作為藝術的功能定位,那么創作自由性與本體性也就隨之喪失,電影很難得到真正的發展。從 1998年“文化立國”的戰略確立,韓國政府認識到文化領域的產業價值,開始不遺余力地扶持文化產業的發展,電影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受到重視。廢除電影審查,確立電影分級制不僅是韓國電影人與政府之間關系由對抗到協商的結果,更是電影產業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而這一轉變的實現,對此后韓國電影行業的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其意義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首先,電影審查制度的廢除對韓國電影帶來的最大的影響就是電影題材和類型的多樣化。20世紀90年代之前,政府苛刻的審查制度是電影題材貧瘠、類型單一的最主要因素。電影審查制度廢除之后,創作自由得以保障,韓國電影人開始涉足以前不準涉及的領域,許多揭露社會現實、批判政府腐敗和直面民族歷史創傷的作品被制作出來。受益于寬松的電影政策,電影新人開始陸續登場,他們根據時代的要求創作了許多與以往電影不同的新類型作品,彌補了韓國電影類型單一的不足。題材與類型的多樣化成為90年代韓國電影的最大收獲。公平地說,韓國電影當下能夠具備如此的競爭力,早先廢除電影審查以確保表達自由的措施起著決定性作用[12](P294)。其次,從審查制到分級制的更迭,不僅體現了韓國政府對電影功能的認識定位實現了由文化統治工具到藝術商品的轉變,更體現了電影政策方向由管制到扶持的轉變。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上臺的金大中政府,以文化產業價值與自律性發展意識為基礎,確立了“扶持但不干涉”的文化政策方針,將振興電影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最后,電影分級制度的確立也是韓國電影產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基本原則是在保護青少年免受色情和暴力電影傷害的前提下,確保電影創作與表達的自由。
四、分級制度的確立與爭論
韓國現行電影分級制度主要以《電影和錄像物相關振興法》為法律依據,以年齡為分級標準,共分為全體可觀看、12歲以上可觀看(未滿12歲者需法定保護人陪同)、15歲以上可觀看(未滿15歲者需法定保護人陪同)、青少年不可觀看(5)“青少年不可觀看級”中的“青少年”指包括高中在校生在內的未滿18歲公民。和限制上映五個等級。電影業者制作或引進的電影(包括預告片和廣告電影)在上映之前,都必須接受映像物等級委員會對電影的分級,特殊情況除外(6)以下為特殊情況,無需接受電影分級:在特定場所內針對不包括青少年的特定人群免費上映的小型電影和短篇電影;電影振興委員會推薦的在電影節上映的電影;以國際性文化交流為目的,文化體育觀光部部長認定的無需接受分級的電影。。不可偽造上映等級和隨意變更已定等級的電影內容,未受分級的電影公開上映或者限制上映館允許青少年進入的,處三年以下徒刑或三千萬韓元的罰款。分級的具體參照標準主要有危害性主題、色情、暴力、低俗性臺詞、恐怖、毒品、模仿危險性七大要素。電影分級制度的貫徹與實施由韓國映像物等級委員會(Korea Media Rating Board)執行。映像物等級委員會于1999年6月7日成立,作為法定的民間機構,委員會除了具體執行包括電影、錄像制品、廣告等影像物的分級,還擔當向外國人推薦韓國影視作品以及影像物調查研究和宣傳教育工作。在機構人員構成上,委員會成員大部分由電影、青少年、輿論、法律、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專家構成,以期分級結果能夠反映社會多樣化的觀點。
如今,韓國電影分級制已經基本完善,但依舊還存在一些遺留問題。例如在“限制上映級”的爭論上。有韓國學者認為,根據《電影和錄像物相關振興法》規定,獲得“限制上映級”的電影,其上映與宣傳只允許在限制上映館內進行。而如今限制上映館在韓國尚未建立,“限制上映級”實際上擔任著電影審查的工作[13](P42)。2002年,韓國電影《七十好年華》成為第一部被評定為“限制上映級”的電影,該作品雖然在國內外電影界獲得了一致好評,但是映像物等級委員會卻由于影片中七分鐘的性愛場面將其判定為“限制上映級”導致影片無法上映。韓國200多名文化藝術界人士聯名發表宣言,要求撤回對該電影的分級并公開審議過程。映像物等級委員會依舊保持對該電影“限制上映級”的分級。最終,《七十好年華》被迫對有關部分進行刪減,經過再審議之后,以“18歲以上可觀看”的等級得以上映。這一事件也體現了“七大要素”作為分級的具體標準,其范圍寬泛、內容模糊的事實。如何界定藝術與淫穢,進一步明確電影分級標準是韓國電影分級制需要解決的問題。
此外,映像物等級委員會的自律性和中立性問題,也是韓國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像美國、日本的電影分級制度,其分級所依據的標準、分級機構以及機構委員的任命均由電影行業內部解決,具有自律性和獨立性。而韓國電影分級制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電影分級的標準不是以行業內部規則為依據,而是以《大韓民國憲法》《電影與錄像物相關振興法》為依據。 另外,映像物等級委員會雖然身為民間機構,但其委員的任命由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負責,機構運營的大部分經費也出自國庫,對政府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映像物等級委員會與政府的密切關系,使其不可能成為完全自律的民間機構,因此韓國電影分級制的實施必然深受政府影響。如何保障分級機構的自律性以及進一步確保電影創作自由空間,也是韓國分級制需要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