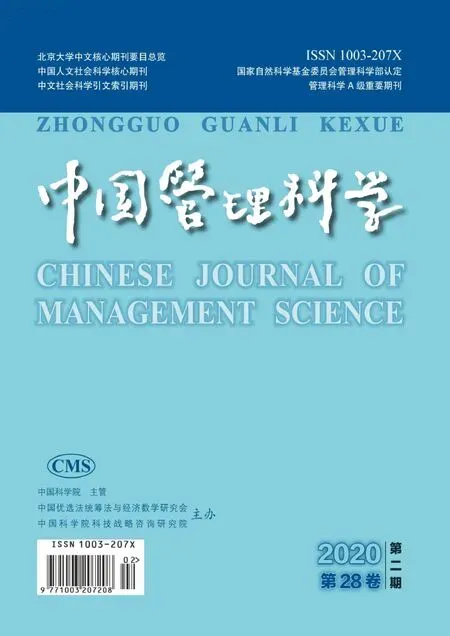養老金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最優組合策略研究
金博軼,閆慶悅,于文廣
(山東財經大學保險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2)
1 引言
長期以來,對養老金制度的選擇一直是理論和實務爭論的焦點。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傳統的現收現付制養老體系面臨著巨大的支付壓力。為此,許多國家進行了養老金體系改革,改革的思路主要有兩種[1]:一種是參量式改革,即在維持現收現付制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提高生育率、延遲退休、提高在職職工繳費率等辦法改善養老金的收支失衡問題;另一種是結構式改革,即通過引入個人賬戶,從而實現現收現付制向累積制或混合制的轉變。其中,混合制(在我國稱為“統賬結合制”)是將現收現付制與累積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與單一養老金制度相比,引入混合制的目的之一是分散風險[2],現收現付制主要面臨人口風險、工資增長風險等代際風險(inter-generational risk),累積制主要面臨投資風險、長壽風險等代內風險(intra-generational risk),兩種制度的組合能夠將上述不同的風險進行分散。
由于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均可以被認為是繳費者擁有的資產或準資產,因此,賬戶組合的選擇實則是投資組合的選擇。從國際上看,不同國家的選擇不盡相同,以瑞士為例,其養老金繳費中進入現收現付賬戶的比例為86.5%,其余13.5%進入個人賬戶,拉脫維亞和波蘭的相關比例分別是70%、30%和62.6%、37.4%[3]。在我國,在職職工養老金總繳費為工資的24%,其中,16%進入統籌賬戶(企業繳納),另外8%進入個人賬戶(個人繳納),也就是說,進入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的資金大約分別占總繳費的66.7%和33.3%。那么問題是,從風險-收益的角度講,這樣的組合是否是最優的呢?如果不是,在總繳費不變的條件下,能否通過調整賬戶繳費比例從而實現帕累托改進呢?不同風險因素及其相關性對最優組合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養老金面臨巨大收支壓力的背景下,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到目前為止,最早研究混合制下養老金賬戶組合策略的文獻見于Merton[4],Merton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了混合制養老金對稅收轉移計劃的影響。但是他并沒有研究混合制下的賬戶最優組合策略。Dutta等[2]在投資組合的框架下分析了混合制的最優組合問題,他們使用二次效用函數得到賬戶最優組合。另外,Van Praag和Cardoso[5]使用納什均衡分析了賬戶的最優組合問題,結果發現,政治因素也可能影響最優組合策略,如果人口老齡化導致老年人口的政治話語權增加,現收現付制在組合中所占有的比重也會增加。Devolder和Melis[6]在工資增長率、人口增長率以及投資收益率隨機的條件下構建了一個兩期迭代模型,并使用二次效用函數得到了混合制下的賬戶最優組合。實證方面,Matsen和Thφgersen[7]通過對瑞士、挪威、美國和英國的研究顯示,前三個國家的最優策略是實行混合制,英國的最優策略是實行完全累積制。Borgmann[8]采用德國與美國的數據得到了不同制度下養老金計劃的有效邊界,結果發現,混合制的風險分散化效應明顯優于單一制養老金計劃。Guigou等[9]以養老金系統的財務可持續性為標準分析了盧森堡養老金賬戶的最優組合問題,他們發現,在最優組合下,完全累積制所占比例應該高于實際值。Boado-Penas和Godínez-Olivares[10]同樣以養老金財務的可持續性為條件,使用非線性優化模型得到了不同賬戶的最優繳費率及其動態調整。Bouhakkou等[11]考慮到了股票市場的不對稱性和尾部風險對最優組合的影響。Wang等[12]則專注于討論養老基金賬戶的最優投資組合問題。
國內方面,現有文獻大都使用世代交疊模型(OLG模型)在一般均衡理論的框架下,通過個人效用最大化和社會福利最大化計算個人賬戶和統籌賬戶的最優繳費率,進而得到賬戶最優組合。例如,封進和宋錚[13]在高生育和低生育假設下測算得到的統籌賬戶最優繳費率分別為22%和25%;孫雅娜等[14]得到的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的最優繳費率區間為16.86%-23.85和9.83%-25.79%。康傳坤和楚天舒[15]研究表明,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將提高最優統籌繳費率,而人口增長率降低將降低最優統籌繳費率。
縱觀國內文獻,僅有宋超吾[16]從投資組合的角度研究了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最優組合問題,但他對兩種賬戶收益率的假設與Dutta等[2]相似,過于簡單且缺乏精算基礎。國外研究只提供了思想上的借鑒,相關結論無法直接應用于我國。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各國養老金體系存在較大差異,現有文獻構建的賬戶收益模型基于不同國家的政策法規,到目前為止,鮮有文獻從監管者的角度出發對我國養老金賬戶收益進行精算建模;其次,由于各國的經濟和社會因素存在較大差異,不同國家養老金體系面臨的人口風險、投資風險、長壽風險等風險因素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國家養老金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的風險及其相關性也不相同;最后,由于賬戶收益模型和賬戶風險存在上述國別差異,不同國家的最優賬戶組合也可能不同,因此,國外的研究結論對我國養老金賬戶最優組合決策沒有參考意義。
本文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根據我國養老金體系的相關規定,使用一個多期迭代模型對我國養老金不同賬戶的收益進行精算建模,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基于風險-收益的最優組合規劃模型,并對模型進行優化求解;第二,使用我國的經濟社會數據并對不同養老金賬戶的收益進行隨機模擬,分析了不同賬戶之間的相關性;第三、在模型的數值計算部分,我們首先比較了混合制、現收現付制和累積制的有效邊界,然后求解得到不同賬戶的最優組合。本文的結論具有豐富的政策含義,一方面,通過有效邊界的分析為混合制養老保險的合理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持,彌補了現有文獻的研究不足;另一方面,通過最優賬戶組合的求解為政策制定提供決策支持。
2 理論模型的構建
2.1 確定性的兩期迭代模型
在兩期模型下,假設個體只存活時間長度相等的兩期:工作期(xy)和退休期(xo)。下面,我們將通過替代率的比較來分析現收現付制和累積制的優劣。
首先分析累積制,個人賬戶養老金按照生存年金的形式繳費和領取。t-1期在職者的繳費被累積到下一期,支付給了t期依然存活的退休者,賬戶的收支平衡等式為:
L(x0,t-1)πS(t-1)(1+it-1)
=L(xr,t)P(t)
(1)
其中,S(t-1)為t-1期的工資,π為養老金繳費率,it-1為t-1期投資收益率,P(t)為t期退休者領取的養老金,L(xy,t-1)為t-1期在職者人數,L(xo,t)為t期退休者人數,如果p(xy,1)表示t-1期在職者活到退休期(t期)的概率,那么,P(t)可表述為:
(2)
養老金的替代率RRA(t)為t期退休者領取的養老金與同期在職者的工資之比,如果用gt表示工資從t-1期到t期的增長率,RRA(t)可表述為:
(3)
下面分析現收現付制,在現收現付制下,t期在職者的養老金繳費被立即轉移支付給了當期的退休者。賬戶的收支平衡等式為:
L(xy,t)πS(t)=L(xo,t)P(t)
(4)
假設在職人口從t-1期到t期的增長率為dt,養老金的替代率RRT(t)為:
(5)
顯然,當RRT(t)>RRA(t)時,現收現付制優于累積制,反之則相反。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養老金的替代率主要取決生存率(或死亡率)、工資增長率、投資收益率和人口增長率。如果上述變量是確定的,單一養老金制度是最優選擇,混合制并不可取。下面我們分析在上述變量隨機的假設下,養老金賬戶組合的最優選擇問題。
2.2 一個基于統賬結合制的混合模型
下面分析一個帶有多個隨機因素的混合模型,在混合模型下,養老金繳費的一部分進入個人賬戶進行累積,另一部分進入統籌賬戶進行轉移支付。我們的目標是確定最優的組合比例,從而使養老金領取人在退休時收益最大,同時有效控制風險。考慮在日歷年t進入工作崗位年齡為x1的個體,假設其養老金繳費有一部分進入個人賬戶,進入個人賬戶的資金可以投資于n種資產,個人賬戶的繳費到退休時刻的累積值(Fund)為:
Fund

(6)


(7)
個人賬戶累積到退休后按月發放,按照相關規定,每月發放的養老金等于累積值除以計發系數(n),若身故時個人賬戶依然有余額,該余額可以被繼承。若將養老保險的繳費和領取做年化處理,在退休時刻,個人賬戶養老金的精算現值(AF)為:

(8)

下面分析統籌賬戶,按照現行規定,退休時從統籌賬戶領取的養老金等于上年度所有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與本人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之和的平均值乘以繳費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再乘以1%,則t年度年齡為x歲的退休者領取的平均養老金(pay(x,t))為:
pay(x,t)=S(t-(x-xr)-1)×TI
×(1+k)x-xr×1%
(9)
其中,k養老金年增長率,TI為繳費年限。
t年度統籌賬戶的平均養老金(pay(t))為:
(10)
其中,xω為個體的最大存活年齡,wx為x歲退休者在所有退休者中所占的比例。
大量的研究[17-18]均表明,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背景下,現行計發模式會導致統籌賬戶在未來收不抵支(收支缺口),而且缺口規模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為此,本文以年度收支平衡為條件確定統籌賬戶的養老金領取額,使用該方法能更好地反映統籌賬戶的現收現付特征。t年度統籌賬戶滿足如下的收支平衡條件:

(11)

(12)
統籌賬戶領取的養老金在退休時的精算現值(PF)為:

(13)
其中,ν為貼現因子,x-xrpxr表示xr歲的個體活到x歲的概率。
跟隨Devolder等[6],本文使用相對財富(RV)度量養老金的賬戶收益,RV被定義為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現值之和除以退休年度的工資水平,即:
(14)
上式可以改寫成如下的簡潔形式,得:

(15)
RV可以理解為退休者從各種賬戶領取的養老金現值的加權,不同賬戶的權重分別為κh(h=1,…n+1)。Fh(h=1,…n+1)代表從不同賬戶領取的養老金在退休時刻的價值,Fh(h=1,…n+1)可表述為:

h=1,…n

(16)
2.3 混合模型下最優組合的確定

Rockafellar和Uryasev[20]認為,在收益率給定的情況下,組合的CVaR可以通過最小化下式得到:

(17)
其中,f(x,y)代表組合損失(負的f(x,y)代表組合收益),其中向量x代表n種資產在組合中的比例,向量y代表n中資產的損失,p(y)為y的分布密度,β∈(0,1)為給定置信水平,α為在給定置信水平上的VaR。
上式也可以通過蒙特卡洛模擬的方法近似的表述為:
CVaRα=VaRα
(18)
其中,q代表模擬的次數,x=(x1,…xn)代表資產組合中,各種資產所占的比例,yk=(yk,1,…yk,n)代表n種資產第k次模擬的收益率。
我們最終得到養老金賬戶收益一定的條件下使風險最小化的優化模型:
(19)
上述優化模型在不同收益的條件下得到的Pareto最優解集(有效邊界)中存在很多最優解,這無疑增加了政府的決策難度。為了得到單一的最優解,我們使用線性加權法將上述優化問題進行轉變,轉變后的模型(模型1)變為:
(20)
模型1最大化求解項的表達形式與經典的二次效用函數非常相似,可以將其理解為基于CVaR風險測度的效用函數,該函數分配給收益項的權重為1,分配給風險項的權重為φ/2,φ可以理解為風險偏好水平,φ越大,表示投資者越厭惡風險。
為了對不同模型的優化結果進行比較,本文同時給出了基于VaR風險測度的優化模型(模型2):
(21)
3 相關變量的隨機模擬
由于表述的復雜性,很難推導出隨機變量Fh(h=1,…n+1)的聯合概率分布和邊緣分布,因此,我們使用隨機模擬方法生成制度贍養率、死亡率、投資收益率等變量的模擬值,然后根據式(1.16)計算隨機變量Fh(h=1,…n+1)的模擬值,最后通過優化模型(1.20)和(1.21)對養老金賬戶的最優組合進行數值求解。
3.1 人口年齡結構隨機模擬
制度贍養率主要取決于人口結構,本文使用人口結構轉變矩陣對制度贍養率進行模擬,人口結構轉變主要由分年齡生育率和死亡率來驅動,假設個人存活的最大年齡為100歲,經典的Leslie人口結構轉變矩陣可表述為:
(22)

由上式可知,人口結構的轉變主要取決于基年人口結構、分年齡生育率和死亡率三個因素。其中,基年人口結構主要與選擇的基年有關,分年齡生育率主要描述不同年齡育齡婦女的生育狀況,是分析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的重要依據。定量分析生育率的數學模型主要包括兩大類,第一類是概率分布函數模型,包括龔帕茲模型、伽馬模型、生育率組合模型等。第二類是時間序列模型。我們選擇時間序列模型對分年齡生育率進行建模,主要原因在于,雖然概率分布函數模型能夠較好的擬合歷史數據,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未來的生育率進行隨機模擬,因此,時間序列模型更為合適。跟隨任強和侯大道[21],我們選擇自回歸積分滑動平均模型(ARIMA) 對生育率進行建模。分年齡人口生育率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1995-2016)。為了簡化問題,我們不區分農村和城鎮婦女的生育率差異,直接選擇全國育齡婦女分年齡生育率作為原始數據。我們使用Box-Jenkins方法對模型進行診斷分析并對相關參數進行參數估計。
為了預測人口的結構變化,還需要對死亡率建模,傳統的確定型死亡率模型不能預測死亡率的變化趨勢,Lee和Carter[22]最早提出了一個簡潔的動態死亡率模型,該模型的數學表達式為:
lnmx,t=αx+βxκt+εx,t
(23)
其中,mx,t為x歲個體在日歷年t的一年期中央死亡率,αx為年齡效應,κt為時間效應,βx為年齡改進效應,εx,t為誤差項。
Lee和Tuljapurkar[23]通過對英、美、法等西方七國的研究后發現,Lee-Carter模型非常有效,足以解釋94%的死亡率變化,因此,本文使用Lee-Carter模型對人口死亡率進行建模。所有數據都來源于《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1995-2016),參數估計結果見圖1。

圖1 Lee-Carter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最后,需要對出生人口的性別比做出假設。長期以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較高,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數據分別為119.2和118.06,2014年降到115.88。考慮到國民生育觀念的改變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本文假設出生人口性別比緩慢降低到105的正常水平。
在完成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隨機模擬后,就可以根據Leslie 轉移矩陣對未來年度的人口結構進行模擬,并計算不同模擬結果下的制度贍養率。
3.2 投資收益率隨機模擬
本文選擇的資產包括無風險資產、股票和債券,假定股票的價格A(t)服從幾何布朗運動,可表示為:
dA(t)=μA(t)dt+σA(t)dω(t)
(24)
其中,μ和σ分別為收益率的均值和標準差,ω(t)為標準布朗運動。A(t)服從對數正態分布,ΔlnA(t)服從正態分布,有:

(25)
同時,跟隨張冀等[24],我們利用修正的CIR模型來刻畫債券收益率的變動,模型為:

(26)
其中,α 為長期平均價值收益率的增長速度,μ為到期收益率的長期回復均值,σ為波動率。
我們選用wind 數據庫中的申銀萬國銀行指數作為債券資產收益率,上證綜合指數的收益率作為股票資產收益率,時間段為2006年1 月1 日至2017年6月1 日,表1給出了兩種風險資產的參數估計結果。

表1 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
3.3 工資增長率隨機模擬
近年來,不少學者[25]對工資增長與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還有學者[26]認為,隨著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經濟環境和資源條件等因素對年平均工資開始起阻滯作用,平均工資增長率會經歷先增長后下降的趨勢。因此,他們使用Logistic 阻滯增長模型對工資增長進行建模,并取得較好的預測效果。但是,這些模型均沒有辦法對未來的工資增長率進行隨機模擬,因此,本文對工資增長率構建時間序列模型,我們選擇1985年到2015年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實際工資增長率為指標,單位根檢驗后發現,工資增長率是平穩時間序列,經過Box-Jenkins方法分析診斷,最終確定該序列屬于AR(1)過程,參數估計結果見表2。

表2 工資增長參數估計結果
4 數值計算
4.1 相關假設
假定勞動者22歲進入工作崗位并參加養老保險,參保者自進入制度至退休,整個參保期間連續足額繳費。按照相關規定,我國目前法定的退休年齡是男職工年滿6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為了簡化問題,我們將男女性的退休年齡統一設定為60歲。我們選擇一年期國債作為無風險資產,根據中國債券信息網數據,近年來,一年期國債收益率在1.86%-3.60%之間,均值為2.81%,因此,我們將無風險資產的利率設定為2.8%。我們將風險偏好系數設定為2,直觀含義是風險主體對收益和風險同等重視。為了使結論更加穩健,我們將對風險偏好系數在2到8之間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見4.3)。
4.2 數值計算結果
表3給出了不同賬戶收益的均值和方差-協方差矩陣。從均值和方差來看,股票資產賬戶收益的均值最高,方差也最大,統籌賬戶和債券資產居中,無風險資產賬戶的均值最低,方差也最小。從協方差矩陣來看,首先,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的收益(包括個人賬戶下的無風險資產賬戶、股票賬戶以及債券賬戶)負相關,因此,二者的組合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的風險對沖機制,即當統籌賬戶的財富下降時,個人賬戶的財富會增加,反之亦然。其次,個人賬戶間的相關性均為正,但相關系數小于1,可見,個人賬戶不同資產的組合也起到風險分散的作用。導致賬戶間相關的可能原因是所有賬戶的收益均與死亡率相關,其中,個人賬戶與死亡率負相關,死亡率降低使個人賬戶的領取期限延長,收益增加,反之則相反。死亡率對統籌賬戶的影響較為復雜,一方面,與個人賬戶類似,死亡率降低延長了統籌賬戶的領取年限,從而增加了賬戶收益;但是,另一方面,死亡率降低加劇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提高了制度贍養率,從而使統籌賬戶養老金的領取金額下降,收益降低;由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負相關可知,后者的作用顯然超過了前者。

表3 賬戶相對財富的均值以及方差-協方差矩陣
注:T表示統籌賬戶,FW表示無風險資產賬戶,FG表示股票賬戶,FZ表示債券賬戶。
圖2給出了現收現付制、累積制和混合制養老金基于風險—收益的有效邊界。由于現收現付制下養老金只有一種資產,因此,其所謂有效邊界就是一個點,累積制可以選擇無風險資產、股票和債券三種資產投資,混合制可以選擇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下的三種資產進行投資,二者的有效邊界均是一條曲線。由圖2可知,混合制養老金的有效邊界在現收現付制和累積制的上方,由此可見,與現收現付制或累積制相比,在風險一定的條件下,混合制的收益更高,或者在收益一定的條件下,混合制的風險更小。因此,從風險-收益的角度講,混合制優于單一養老金制度。

圖2A 有效邊界(模型1)

圖2B 有效邊界(模型2)
表4給出了養老金賬戶的最優組合策略。首先,個人賬戶投資種類的選擇對最優組合會產生影響,若只選擇股票和債券兩種資產進行投資,在模型1下,個人賬戶的最優占比為55.22%,其中股票和債券的占比分別為24.62%和30.60%,統籌賬戶的最優占比為44.78%。若選擇全部三種資產進行投資,個人賬戶的最優占比提高到56.69%,其中股票、債券、無風險資產的占比分別為23.72%、28.18%和4.79%,統籌賬戶的占比則下降到43.31%;其次,模型的選擇也會對最優組合產生影響,以個人賬戶選擇三種資產進行投資為例,在模型1下,統籌賬戶的占比為43.31%,高于模型2的41.74%,其中,股票和債券的占比分別為23.72%和28.18%,也高于后者的25.50%和19.06%,只有無風險資產的占比(4.79%)低于后者(9.14%);最后,根據不同條件下的計算結果來看,統籌賬戶的最優占比介于38.60%到44.78%之間,低于現行統籌賬戶66.67%的占比,個人賬戶的最優占比介于55.22%到61.39%之間,高于現行個人賬戶33.33%的占比。可見,從最優組合的角度講,現行制度下的統籌賬戶占比偏高,而個人賬戶占比偏低,這一點于Guigou等[9]對盧森堡養老金賬戶組合的研究結論相同。因此,適當的降低統籌賬戶的比例,增加個人賬戶的占比確實能夠更好的分散風險,提高收益。

表4 數值計算結果
注:NR表示個人賬戶投資于股票和債券,RF表示個人賬戶投資于無風險資產和債券,NG表示個人賬戶投資于股票、債券和無風險資產。
養老保險的費率結構可以通過同時調整兩個賬戶的繳費比例或只調整一個賬戶的繳費比例來實現。2019年4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自2019年5月1日起,降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賬戶繳費比例,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從20%下調到16%,個人賬戶繳費率維持8%不變。顯然,此次統籌賬戶的降費措施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率占比提高,統籌賬戶的繳費率占比降低。雖然此次降費的主要目的是減輕企業負擔,但是從本文的結論來看,降低統籌賬戶繳費率也進一步優化了養老保險的費率結構。
4.3 敏感性分析
最優賬戶組合除了受模型和個人賬戶投資種類選擇的影響外,還可能會受到退休年齡、無風險利率水平、風險偏好等因素的影響。下面我們就上述因素的影響進行敏感性分析。
圖3給出了退休年齡變化對最優賬戶組合的影響。由圖3可知,隨著退休年齡的延遲,統籌賬戶的最優占比緩慢增加,個人賬戶的占比緩慢下降。退休年齡提高到70歲,統籌賬戶的占比從43.31%提高到47.09%,個人賬戶的占比從56.69%下降到52.91%,股票資產的占比基本保持穩定,從23.72%變為23.99%,債券資產的占比從28.19%緩慢增加28.92%,無風險資產的占比從4.79%下降到零。
目前,我國正在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制度,其目的是為了阻止制度贍養率的過快提高,緩解人口老齡化導致的養老金收支失衡問題。從本文的結論來看,即使是退休年齡提高到70歲,統籌賬戶占比依然偏高(與最優組合相比),個人賬戶占比依然偏低。而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統籌賬戶的最優占比會繼續下降,個人賬戶的最優占比會繼續上升。

圖3 退休年齡敏感性分析
圖4給出了無風險利率的變化對最優賬戶組合的影響。由圖4可知,無風險利率提高,無風險資產的占比會增加,其他資產的占比會降低。無風險利率從2.8%提高到4.8%,在模型1下,無風險資產的占比從4.79%上升到14.57%,統籌賬戶的比例從43.31%降低到40.29%,股票資產和債券資產的占比分別從23.72%和28.19%下降到21.89%和23.25%。

圖4 無風險利率敏感性分析
由于我國個人賬戶存在一定的“空賬”運行的情況,個人賬戶部分淪為記賬工具。長期以來,個人賬戶的記賬利率由各省自行確定,而各省的記賬利率普遍偏低,有的甚至低于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以2015年為例,根據各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公布的數據,山東省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記賬利率為4.25%;遼寧省為2.76%;上海市、貴州省為2.75%;廣東省為2.12%;安徽省為1.62%;湖北省甚至低至1.5%。為此,人社部與財政部于2017年6月聯合發布的《關于公布2016年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記賬利率等參數的通知》,明確2016年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記賬利率統一設定為8.31%,遠高于往年地方發布的記賬利率,甚至比一些理財產品利率還高。由于“空賬”可以認為是個人賬戶投資于無風險資產(由政府作擔保的養老金機構向繳費者的借款),從本文的結論來看,無風險利率(記賬利率)的提高確實能夠增加無風險資產的持有比例,提高養老金未來的領取額,但是,記賬利率下的資產只是賬面上的,并沒有實際的資產與之對應,因此,這樣的制度設計并沒有起到風險分散的作用。而且,較高的記賬利率使社保機構在未來面臨較大的支付壓力,這一點與統籌賬戶面臨的困境是相同的。當然,若記賬利率過低,養老金未來的支付雖然有保障,但也會降低繳費者的繳費積極性,導致嚴重的逆選擇問題。
最后,我們對風險偏好系數做敏感性分析,風險偏好系數越大,表示個體的風險規避意識越強。圖5給出了風險偏好系數的變化對最優賬戶組合的影響,由圖5可知,風險偏好系數的提高導致無風險資產的占比增加,其他資產的占比下降。如果風險偏好系數從2提高到8,無風險資產的占比從4.79%上升到20.02%,統籌賬戶的占比從43.31%降低到33.78%,股票和債券資產的占比分別從23.72%和28.19%下降到19.61%和22.52%。
一般認為,風險規避系數在生命周期內是遞增的,也就是說,年齡越大,風險規避意識越強,風險容忍度越低。根據本文的結論,我們建議,政府應該根據不同年齡結構的風險容忍度設定差異化的個人賬戶投資策略,從而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

圖5 風險偏好敏感性分析
5 結語
本文從風險分散的角度出發在投資組合理論的框架下對養老金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的最優組合問題進行了研究。為此,我們首先在確定性條件下對不同賬戶的收益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若投資收益率,制度贍養率、工資增長率等相關變量都是非隨機的,那么,單一養老金制度是最優選擇,混合制(或稱統賬結合制)并不可行,若上述變量帶有隨機性,混合制便可能成為最優選擇。隨后,在上述變量隨機的假設下,本文使用一個多期迭代模型對養老金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的收益進行精算建模,計算了不同養老金賬戶的收益,在此基礎上使用CVaR風險測度方法構建了養老金賬戶組合最優決策模型。
為了對上述模型進行優化求解,本文使用蒙特卡洛方法對死亡率、生育率、投資收益率以及工資增長率等變量進行隨機模擬,并通過模擬值計算不同賬戶的收益,對收益的方差-協方差矩陣進行分析后發現,個人賬戶與統籌賬戶的收益負相關,個人賬戶收益降低時統籌賬戶的收益會增加,反之亦然,二者的組合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的風險對沖機制。通過對有效邊界的比較后發現,混合制的有效邊界在現收現付制和累積制的上方,由此可見,與現收現付制或累積制相比,在風險一定的條件下,混合制的收益更高,或者在收益一定的條件下,混合制的風險更小。因此,從風險-收益的角度講,混合制優于單一養老金制度。
對優化模型進行求解后發現,統籌賬戶的最優占比介于38.6%到44.78%之間,低于現行統籌賬戶66.67%的占比,個人賬戶的最優占比介于55.22%到61.2%之間,高于現行個人賬戶33.33%的占比。可見,從最優組合的角度講,現行制度下的統籌賬戶占比偏高,而個人賬戶占比偏低。
本文的政策含義在于,適當的降低現行統籌賬戶的占比,相應的增加個人賬戶的占比能夠更好的分散養老金面臨的各種風險,增加養老金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