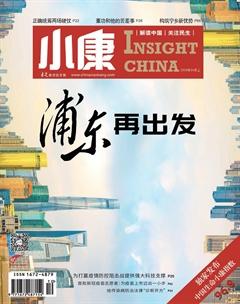浦東開發開放的“制度試驗”
謝國平

先行先試 從1990年起平均每隔5年,中央和上海市政府就會給浦東重大改革開放任務、重大功能性戰略,要求浦東先行先試。
細看浦東開發開放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浦東身上一直有個標簽——試驗。比如,2005年浦東成為全國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3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落戶浦東。這個標簽的內涵正是浦東開發開放30年來堅持不懈的制度試驗,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看,這是一場大試驗。
探索:從功能性政策起步
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而在之前,中國已經有了5個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早期,經濟特區都把優惠的稅收政策作為吸引外資的主要手段,實行優惠政策幾乎和中國的特殊經濟區域劃上了等號。浦東開發啟動后,最初也是以實行財政和稅收優惠政策為核心,以市場準入等功能性政策為輔助。但是浦東建設者發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實施優惠的稅收政策的弊端逐步顯現,如有違公平原則、產生“虹吸效應”、招商中的惡性競爭等等。浦東建設者也意識到,優惠政策早晚要終結,政策傾斜總有歸正之時。為此,浦東開始擺脫對稅收優惠、資金資源等政策的依賴,提出了實施功能性政策,也就是開始了制度試驗。
所謂功能性政策就是針對當時中國對外資進入的領域限制、產業限制、經營限制和其他限制,按照國際慣例和國內現狀允許浦東突破先行先試。比如,改革開放早期中國只是制造業對外商開放,服務業不對外開放。浦東開發開放后,建設者認為浦東不僅僅要在工業領域,更重要的是在金融和商業等第三產業領域實行對外開放,其中包括建立自由貿易區、允許外資進入金融業等。因此在1995年,浦東向中央提出,請求浦東在服務貿易領域對外資先行先試開放。該報告的核心內容是建議中央允許浦東新區在服務貿易等某些領域對外資開放,先行先試,包括允許外資銀行在浦東試營人民幣業務;允許在浦東建立中外合資外貿公司;允許在浦東設立中外合資的保險公司;允許內地其他省份的外貿公司到浦東設立子公司;在外高橋保稅區實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這一請求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并以國務院文件的形式批復。因為這種功能性政策的實施、試驗,使得浦東在中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建立相關的市場體系、規則、環境等方面先行了一步,逐步成為中國對外開放度最高和市場準入度最大的地區。
而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看,這種功能性政策更具有宏觀意義,因為改革開放發展到了深處,依賴稅收優惠政策已經在一些地方顯現出弊端,更需要制度層面的創新。
對于功能性政策,浦東新區管委會首任主任趙啟正有這樣一個形象的解釋:將海邊的一個軍事場所,通過政策安排,改變為海濱游泳場所,這樣改變場所的功能,這樣的政策就是功能性政策。和以前的優惠政策比,其最大的特點是沒有任何稅收上的關系,更沒有來自上級部門的投資。
其實,浦東提出的這種功能性政策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中一項重要戰略——在一個特殊的區域里不斷地進行制度試驗,成功的便加以推廣。而浦東人最先意識到了這一點,并舉起了“先行先試”的旗幟。
進入21世紀,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各地開始走出簡單地依靠優惠政策發展的階段,進入體制創新、制度創新階段。而浦東沿著功能性政策的探索,又進一步爭取國家對外開放和制度創新方面的重大舉措放在浦東先行先試,積極穩妥地推進綜合性制度創新。因為就區域而言,浦東在逐漸失去優惠政策效應的同時,面臨如何在更高的起點上實現快速發展的問題。到2005年,浦東創造了整個上海四分之一的地區生產總值、二分之一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和三分之一的利用外資總額。一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地區怎樣進一步發展?從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層面看,之前的單項式的改革所引發的矛盾已經超越了經濟范疇,必須考慮改革的系統性和配套性,將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等置于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框架中。而浦東一直在進行功能性政策的探索,一向愿意在改革開放中先行先試,因此,浦東的請求又一次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成為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之后一直到2013年,中央一共批準全國12個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可以說,這又是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實施的一項區域發展戰略。
堅持:以擴大開放倒逼制度創新
2013年,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落戶浦東,這又是浦東的一場重大制度試驗。而之前,雖然浦東經過了多年的開發開放,但上海仍沒能完成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任務,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緣于上海能夠自我改革的空間很小,涉及經濟和金融領域的改革都要到各部委審批,進展緩慢。盡管浦東自2005年后進行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點,但這種改革屬于內源性的改革,在浦東一些關鍵領域并不成功,尤其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因此,按照以往的經驗,只有通過外源性改革,也就是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來倒逼改革,實現進一步發展。而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也要求中國必須更深入地改革,這一改革更多是制度層面的。仔細看一下中國自貿區的招牌,就能發現它與全球2000多家自貿區的不同點,其招牌上凸顯“試驗”二字,意味著它不同于多年前實行特殊優惠經濟政策的地區,也不同于國際上傳統意義的自由貿易區,更不同于國內各種形式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名稱不一樣,承擔的歷史使命和作用也不一樣,就是要突破傳統的自由貿易區概念,凸顯其制度試驗的功能,而且這一“試驗”絕非孤立地試驗,是要推廣示范全國的。
再看浦東開發開放史,先后有三個“第一區”:1990年浦東成為第一個國家級新區,2005年浦東成為第一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3年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落戶浦東。
從國家級新區到綜改試驗區,再到自貿區,這一歷史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根紅線:改革開放的大試驗。事實上,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一直堅持的一種做法——不斷地在特定區域內進行改革開放的試驗。從1980年的深圳經濟特區一直到2013年的上海自貿試驗區,從窗戶式開放到門戶式開放;從最初從政治風險的角度考慮選擇了中國南方邊陲小鎮“殺出一條血路”,而后選擇了在中國最大工商業城市建立“試驗田”。中國政府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態度一步一步地在各種特定的區域內進行政策和制度試驗,取得成效后,再向中國的其他地區推廣,讓全國分享成果,以減少政治風險和政策失誤。
這真是一場偉大的試驗。旁觀者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寫道:“由于各級政府(從省市到鄉鎮級別)都在嘗試尋找最適合自身經濟發展的方法,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實驗室,各種不同的經濟試驗遍地開花。”
對浦東來說,因為這場大試驗,從1990年起平均每隔5年,中央和市政府就會給浦東重大的改革開放任務、重大功能性戰略,要求浦東先行先試。如1990年宣布浦東開發開放,1995年實施與國際接軌的先行先試的功能性發展戰略,1999年“聚焦張江”啟動高科技發展戰略,2005年進行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2009年“兩個中心”建設獲批,2013年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落戶浦東,2019年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獲批。這是浦東作為改革開放先鋒者的使命必然,也是浦東一以貫之堅持先行先試所得到的榮幸。
因為這場改革開放的大試驗,浦東在20多年中經歷了歐洲發達地區用兩個世紀才完成的同樣程度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浦東大大跨越了歷史,似乎羅馬一天建成了。也因為這場大試驗,浦東人將“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作為座右銘。
(作者系《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作者,《浦東時報》原副主編,《浦東開發》雜志原主編)